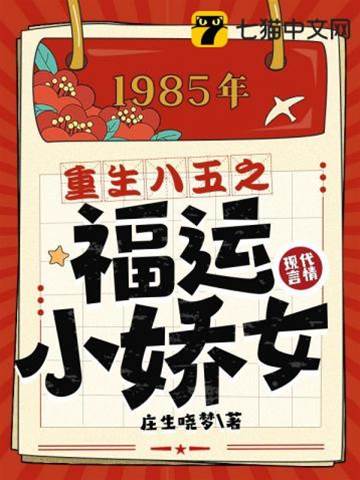《晨昏游戲》 第63章 第63章
鑒于前一天晚上休息不足,今天郁承上床之后,就地抱著睡了。可興許是白天補多了眠,到了半夜里,懷歆突然毫無征兆地醒了過來。
下意識手往旁邊一,是空的。
褶皺的床單還殘存著風吹過的溫度,懷歆睡意消散了些,直起來。
薄被從肩頭落,如同心靈應般,過鵝黃的紗簾幔,看到了孑然倚在臺欄桿上的男人。
半夜兩點鐘,他披著薄外套,在外面打電話。大約是怕吵醒睡覺,聲音得很低。
過了好半晌,他放下手機。
郁承背對著,懷歆看不見他的表。但是卻見幾縷縹緲的煙霧繚繞上浮,接著男人捻住指間那一支猩紅,放在口中深吸,復又緩緩吐出。
火明滅,郁承著遠,影融進幽暗夜中,顯出那麼一點寂寥滋味。
但懷歆這麼看著,卻覺得他此刻其實也是不希任何人去打擾的。
他心事重重,總是想得很多,肩上不知背負了什麼東西。它們沉甸甸的,讓他同其他人的距離很遠。
這一刻懷歆突然清醒了過來,盡數找回理智。
今天一整天他們都黏在一起,熾熱的甜和溫充斥心間,導致有一瞬間產生那種永恒的念頭。
可是現在卻警醒,人一旦貪心,就容易陷萬劫不復的境地。
臺的門沒有關,有些許網的風從隙中溜了進來,吹得懷歆思維愈發冷靜。
因為的親所以覺得心得更近,疊加之前的基礎,會產生錯覺也是很正常的事。
可事實卻是,他們不是熱的,只是兩個互相欣賞并樂意和對方上床的人。也許上有一定程度彼此需要,但若因他一句“和你在一起很開心”就繳械投降,絕對是愚蠢的行為。
Advertisement
還沒有贏,不能夠掉以輕心。
可以樂,但是要有分寸;可以放縱,但是不能沉溺。
懷歆重新躺下來,凝視著天花板上那頂熄滅的吊燈。
揮去心中霾之后,覺自己仿佛愈發輕松。
郁承進來的時候床上的人還在睡,剛和香港打了一通電話,他的眉目很是倦淡。
男人上床的時候作很輕,可才剛剛躺下,就裹著被子翻了,蜷進他的懷里。
“怎麼了?”懷歆的嗓音迷迷糊糊的,郁承輕拍了拍的肩膀,安道,“沒事,睡吧。”
他上的煙草氣息沒有想象中濃厚,淡淡的溫緩,大概是在外面又站了一會兒才進來。是在細節上也很的男人。
懷歆閉著眼微挽了下角,也安地握住他的手指,輕聲道:“晚安。”
一夜好眠。
第二天早上是在鳥兒的啁啾啼鳴中醒來的。
白天他們去了黑沙海灘,趁著線好拍了好多照。郁承帶了他的單反,里面還有當時在稻城牛湖為懷歆拍的那張照片。
其實當時是故意的。
明明自己有相機,非要用他的。
懷歆猜想郁承大概也知道,但他一向縱容這些小心思。
午飯吃了附近最正宗的葡國菜,地道的燒沙甸魚、焗飯,還有馬鈴薯、洋蔥和鱈魚一同油炸的香噴噴的馬介休球。
下午又去了一些其他的景點,玫瑰堂和澳門塔。兩人回到永利酒店,原本商量著晚餐在商場里吃,付庭宥卻忽然找過來,說是自己的一位叔叔來了澳門,讓郁承最好去見一見。
郁承放下電話,很自然地從后擁住懷歆,嗓音低沉道:“抱歉,本來是一起度假,我卻總還有些別的事。”
知道這對他來說很重要。這些人這些事,本就是他生活中不可割舍的一部分。
Advertisement
“沒事兒,付先生不是說晚上還去賭場玩嗎?”懷歆微微一笑,“我等你回來,然后一起去。”
他把轉過來,細細地凝視片刻,而后眸沉靜地點頭:“好。”
前幾天就聽付庭宥說今晚他們那些人會去賭場玩,算著郁承差不多回來的時間,懷歆換上自己帶的一條酒紅復古小禮,坐在鏡子前開始化妝。
約莫八九點的景,外面響起男人沉著平穩的步伐聲。
也許是在外面找了一圈沒找到,所以推測在梳妝室。
懷歆的這條酒紅禮服是吊帶式絨魚尾,同樣是掐腰設計,擺是繁復的歐式宮廷褶皺,如同一朵盛開的薔薇花。同時背部有一小塊是鏤空的,出綢緞一樣的白皙細膩的,十分惹眼。
郁承的腳步聲停在門口。
懷歆繼續畫眼妝,耐心地等了好一會兒,才聽到他出聲。
“今晚準備穿這個?”郁承嗓音微沉,辨不出緒。
這才斜睨了他一眼,揚揚眉,神像只慵懶的小狐貍:“是啊。”
他沒出聲,只是又淡淡地看了一會兒,轉走了出去。
外面很快就響起窸窸窣窣的聲音,接著浴室有水聲,郁承沖完澡,也換了服。
懷歆定完妝走出去的時候,男人正在臥室里慢條斯理地扣著袖扣。他著一雙排扣平駁領馬甲,腰腹間的收束盡顯力量,拔而英俊,如同英倫貴族紳士。
兩人的視線在半空中相,懷歆翹了下角,坐到床沿邊上,慢條斯理地穿高跟鞋。
這是一雙新鞋,還是假期不久前逛街時候買的,所以鞋尾稍,不太好穿。不過懷歆也不著急,踩著鞋站起來轉了轉腳尖,大小剛好合適。
Advertisement
現下大約九十點左右,懷歆問:“他們已經下去了嗎?”
郁承嗯了一聲。
懷歆走到他面前,俏地歪了下頭,撒般的:“我今天不好看?你都沒有夸我。”
郁承深長眸凝視須臾,而后斂著眸笑了。
“好看。”
他微俯下,耳側,“好看到我想把你藏起來,不給別人看到。”
溫熱吐息撥得懷歆頸側微,些許緋紅蔓上來,還沒說什麼,就見郁承漫不經心地將搭在臂彎里的西裝外套拿起來,徑直搭在上。
肩頭和背部出的全部都被遮蔽住,郁承不由分說地攬著出門。
“……”
男人的占有啊,懷歆想笑。
到賭場的時候五六人已經開了桌德州撲克,見郁承攜人來了,連忙讓座。
懷歆不聲掃過一圈,在座有幾個都是之前晚宴上的面孔,與郁承搭過話的,葉鴻也在。
葉鴻看到明顯面微變,付庭宥被簇擁在中間,淡淡朝他使了個眼。
葉鴻神更不好了,視線在懷歆和郁承之間轉圜兩圈,咬了咬牙,當著幾人面遞給郁承一支煙:“承,之前是我對不住,您別放在心上。”
大家的注意力都吸引過來,籌碼也不下了,都饒有興致地看戲。
“怎麼了這是?”
郁承雙疊,并不理會葉鴻,對方的手僵在空中,難堪解釋道:“我……得罪了承。”
郁承這才抬眼,眸不含什麼溫度:“你該道歉的人不是我。”
周圍響起些許竊竊私語,葉鴻深吸了兩口氣,又轉向懷歆。
“Lisa小姐。”他略顯艱難地開口,“先前是葉某不對,開罪了你。葉某向你賠不是。”
龍亨集團的三公子,平時有多傲氣是可以想見的,這現下謹小慎微的,讓人不得不嘆世道諷刺。
Advertisement
懷歆支著下頜看了他片刻,平和道:“沒關系。”
郁承這才淡淡勾了下,接過葉鴻手中的煙。
葉鴻見狀,趕傾過來為他點火。
懷歆看出葉鴻明顯松了口氣,低著眼卻難藏翳,而旁幾位都不聲,或沉思或看戲。淡淡的煙草味道從側彌漫過來,懷歆瞇了瞇眼,也垂下了眸,假裝不知曉這一桌子的暗洶涌。
郁承吸了幾口煙就掐了,重開一局德撲,他攬了懷歆的肩,附在耳邊說:“你替我下注。”
一手四千,輒大幾萬,懷歆詫異:“我?”
郁承低笑,下的眸略顯慵懶:“嗯,你。”
懷歆想了想,也微側過來,同他私語:“萬一我輸了很多怎麼辦?”
不是不會玩,可是在學校里和同學玩都是虛擬籌碼,從來沒過真格的,想想就苦了臉。
郁承抬了抬眉,散漫問:“你怕輸?”
這話似是有些興味,不知在暗指什麼,懷歆的勝負驀地被激起,沉默地將郁承面前的籌碼挪到了自己跟前。
男人笑了,嗓音重新溫低緩下來:“盡管出手,無論賠賺我都擔著。”
這事兒就是算概率,但是懷歆沒鉆研過那些,風險偏好適中,既不過激也不太保守,幾局下來輸贏幾乎相抵。
這個結果比懷歆設想中要好很多,得了趣,膽子漸漸大起來,開始出一些不同尋常的招數。
連續輸了兩把之后,懷歆最終贏了一次。不僅把前兩次虧空賺回來,還多贏了許多。
換錢數一算,大概得有個大幾萬。
付庭宥笑而不語,他邊坐著的孟先生也挑眉道:“Lisa小姐看著年輕,沒想厲害著呢。”
葉鴻聞言頓了一下,低著頭沒說話。
懷歆看向幾人,謙虛道:“都是運氣。”
正說話間卻覺到的手忽然被某人握進了掌心里,饒有興致地把玩。
郁承的手指修長漂亮,溫熱指腹淺淺蹭過的腕心,似有若無的撥。
懷歆心里一,想回來,卻被他抓得更。
也就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任由他去了,只是后面幾局都只把左手放在臺面上。
桌上幾人都點了煙,有些嗆人,看樣子這局是進尾聲的意思,孟先生提議去喝酒,眾人紛紛附和。
懷歆站起了。
郁承的外套還披在上,傾過同他耳語:“我去趟衛生間。”
“嗯。”郁承問,“需要我陪你去麼?”
懷歆搖搖頭,付庭宥幾人正準備換場,郁承便叮囑道:“注意安全,出來之后聯系我。”
到都是熱鬧的景象,紙醉金迷,燈紅酒綠,穿過這片區域,走了一段距離才找到洗手間。
懷歆重新補了妝,對著鏡子靜靜凝視自己片刻,轉走了出去。
循著之前的記憶往回走,很快就來到了賭場門口。
懷歆其實對這里的一切都到新奇,看到周邊有許多餐廳和購小店,也不著急聯系郁承,在附近轉了轉。
倒是過了一會兒,郁承發微信問在哪里,還把他們去的那家酒吧名字發了過來。
懷歆據他給的臺號直接找到了卡座的位置,還沒走近就看到一大幫子人圍一圈,有男也有。
除了剛才的幾位,他們又了好些人。打牌不喜人上桌,但喝酒總要人陪。
郁承就坐在角落里,左邊空了個位置,看樣子是給留的。但讓懷歆多看了兩眼的是他右側,坐著一個妝容致,材姣好的漂亮人。
懷歆正準備過去,就見人了一下郁承的肩,側臉笑著同他說話。
酒吧聲音太過嘈雜,本聽不清,人便向他傾,抹雪輕。
懷歆線平直,提著擺走了過去,在郁承邊坐下。
男人第一時間就發現了,清緩氣息覆過來:“怎麼去了那麼久?以為你迷路了。”
“沒有,就到走一走。”
懷歆把肩頭的西裝外套下來,扔回給他。
郁承怔了一瞬,靠近:“怎麼?”
懷歆拿了一杯shot一飲而盡,朝他笑笑:“太熱了。”
兩人只講了幾句話,可卻吸引了不人的注意力。
他們昨晚是見過懷歆的,年輕麗的容總是讓人印象深刻。今日又穿著一襲紅,比昨天還要明艷三分,實在得張揚。
猜你喜歡
-
完結437 章

禁愛冷婚:噬心總裁請走開
十歲那年,她被帶回顧家,從此成了他的專屬標籤.性子頑劣的他習慣了每天欺負她,想盡各種辦法試圖把她趕出這個家.在她眼中,他是惡魔,長大後想盡辦法逃離…孰不知,傲嬌的他的背後是他滿滿的深情!在他眼中,她是自己的,只能被他欺負…
79.8萬字8 51621 -
連載1508 章
媽咪爹地要抱抱
豪門陸家走失18年的女兒找回來了,眾人都以為流落在外的陸細辛會住在平民窟,冇有良好的教養,是一個土包子。結果驚呆眾人眼球,陸細辛不僅手握國際品牌妍媚大量股份,居然還是沈家那個千億萌寶的親生母親!
127.1萬字8 107896 -
完結518 章

六歲妹妹包郵包甜
【團寵、高甜、前世今生】農村小野丫頭樂萱,靠吃百家飯續命,家家戶戶嫌棄她。 某天城里來了個謫仙似的小哥哥沈易,把她領了回家。 噩夢中驚醒,覺醒了萱寶某項技能,六歲女娃琴棋書畫樣樣精通,徹底虜獲了沈家長輩們和哥哥們的心,她被寵成了金貴的小寶貝。 每天爺爺奶奶、爸爸媽媽、叔叔嬸嬸、還有哥哥們爭著搶著寵,鄉下野生親戚也突然多了起來,自此萱寶每天都很忙,忙著長大,忙著可愛,忙著被寵、忙著虐渣…… 標簽:現代言情 團寵 甜寵 豪門總裁
109.9萬字8 94533 -
完結872 章

婚華正茂
蘇念恩被查出不孕,婆婆立馬張羅,四處宣揚她有病。丈夫出軌,婆婆惡毒,當蘇念恩看清一切,凈身出戶時,丈夫和婆婆雙雙跪求她留下。她瀟灑走人:“我有病,別惹我。”愛轉角某個牛逼轟轟的大佬張開雙臂說:“你有病,我有藥,天生一對。”
138.1萬字8 70063 -
完結38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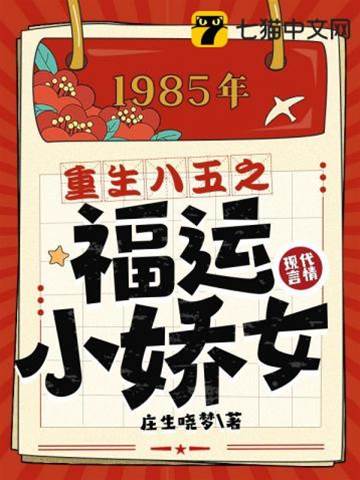
重生八五之福運小嬌女
前世,喬金靈臨死前才知道爸爸死在閨蜜王曉嬌之手! 玉石俱焚,她一朝重生在85年,那年她6歲,還來得及救爸爸...... 這一次,她不再輕信,該打的打,該懟的懟。 福星錦鯉體質,接觸她的人都幸運起來。 而且一個不留神,她就幫著全家走向人生巔峰,當富二代不香嘛? 只是小時候認識的小男孩,長大后老是纏著她。 清泠儒雅的外交官宋益善,指著額頭的疤,輕聲對她說道:“你小時候打的,毀容了,你得負責。 ”
70.5萬字8 19167 -
連載285 章
相親對象是富豪總裁
她著急把自己嫁了,不求此人大富大貴,只要沒有不良嗜好,工作穩定,愿意與她結婚就成。沒想到教授變總裁,還是首富謝氏家的總裁。……當身份被揭穿,他差點追妻火葬場。老婆,我不想離婚,我在家帶孩子,你去做總裁,謝氏千億都是你的,你想怎麼霍霍就怎麼霍霍。其實,她也是富豪。
50.8萬字8 1449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