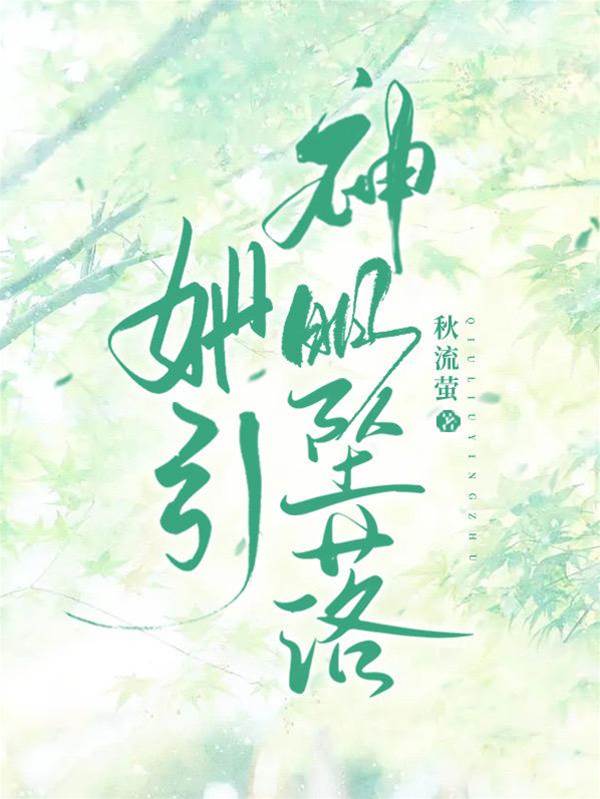《予你熱戀》 第35章 跑操
“不是因為你。是家里的原因。”
舒茗愣了一下。其實的話還沒說完, 那后半句是‘你明明是為了夏知予’,但是許京珩本沒給這個機會。
“家里原因?”
“你不也說了嗎?我爸媽是閃婚,生了我之后又火速離婚, 誰也沒有要我。現在我那丟下我的媽回來了,外婆了刺激, 又不認得人了。”他轉著筆, 眼神仍在掃題目, 只是面無表地陳述事實:“我要去京江的前一天, 走丟過一回。最后是找到了,但緒并不穩定, 我放心不下, 所以沒去。”
聽著有些牽強, 但也親眼目睹過他外婆的況。聽說老人家患有阿茲海默癥, 時常記不起事,這幾年況更嚴重。很多時候,一個人坐在院子里, 總是在想些什麼, 自以為想起來的時候開心得像個孩子。
結果一開口, 還是沒記對。
那些親近的、重要的人,在生命中逐漸丟走了。
所以能理解許京珩的這樣的想法。但又意識到, 許京珩從來不跟解釋這些的。他這人經常端得一副‘關你屁事’的姿態,就算解釋, ‘家里原因’這四個字也已經足以打發人, 沒必要解釋得這麼詳細。
正疑,許京珩又說:“被流言困擾的滋味, 并不好。我現在跟你解釋清楚了, 如果有必要, 我日后都會是這個說辭。所以,你別多想,也別傳。”
說到‘別傳’這三個字的時候,他終于抬眼,看向舒茗。
那一刻,舒茗好像明白了什麼,卻也沒覺得難過。因為不覺得難過,這才意識到自己好像確實如許京珩所說的那樣,沒那麼喜歡他。
Advertisement
多年后,回想起這段過往,甚至還有些竊喜。在高中這個半封閉式的環境下,大多數人格的養無法跳于家庭而獨立存在。并且在自我暗示下,任由格缺憾的長。諸如在單親家庭中長大,理所當然地認為自己就是需要從別人上獲取安全,所以會錯把安全當做喜歡。而大學后,封閉的圈子出一個,接面廣了,才知道,格不過某個特定時期、特定偏好的證明,或許很難徹底扭轉,但它絕不是固附在你上的標簽。
一點一點地把寄托在別人上的安全取了回來,牢牢地攥在掌心。而這一切,對那個時候的舒茗來說,似乎都不算太晚。
-
次日,學校吧突然多了條帖子。樓主是黎川,他最終還是當了許京珩的水軍,以好兄弟的份,幫忙解釋了許京珩沒去參加競賽的原因。
當然,那套說辭,是許京珩一個字一個字打給他的,他只是個復制粘的工人。雖然不知道他的好兄弟為什麼要搞這一出,但不得不說,許京珩在控制輿論這方面還有天賦,帖子發出后,再也沒人編排他棄賽的事。
夏知予是從程岐手機上看到那條帖子的,看到帖子的那刻,原些堆積的歉疚慢慢消散了一些。心里一直覺得許京珩是通過的電話找過來,這才有棄賽打架一事。本來想找個時間問問清楚,但最近幾天一直沒找著合適的機會。
卻不想在帖子發出后的第二天,許京珩就在跑的時候找上了。
市一中的跑,不單單是繞著場跑,而是需要沿著跑道,跑出場北門,靠近北門的是高三(11)班,由他們班領隊,一直往后到高一(1)班,繞著整個教學樓跑上一圈,再回來場。所以按照班級順序,高三(1)班和高一(3)班之間隔了整整十九個班級。
Advertisement
通常來說,高三整個年級段跑了大半路程的時候,高一才跑出場。然而他就像算準了時間一樣,在高一(3)班快要跑到教學樓背后夾竹桃的時候,挑散了鞋帶,隨后慢條斯理地蹲下來,修長的手指有一下沒一下地捻著鞋帶玩。
直到抬頭看見夏知予的影,才站起來,小跑著跟在的旁邊,出言提醒:“學妹,你踩到我鞋帶了。”
聽到悉的聲音,夏知予扭頭過去,一下子撞進許京珩盛笑的眼里,跑的速度也沒多快,不過是慢跑,心臟就開始猛烈跳。
兩人齊齊掉隊,最后也跟不上了,索慢下步子。夏知予去看他的鞋帶。鞋帶雖然散了,但是洗得發白,毫沒有灰痕跡,也就不存在他所說的踩到鞋帶。
“現在騙子訛人的手段都這麼低級嗎?”
“奧,我變騙子了?那我還沒訛你什麼呢。”
夏知予狐疑地看向他,嘀咕了一聲:“你還想訛我...”
他單刀直:“訛你一個聽我道歉的機會行不行?”
果然訛人的騙子在一開始就明確想好了自己想要獲得的東西。
夏知予怔忡。
“你沒事道什麼歉。”
要道歉,也該是道歉。雖然吧上說許京珩棄賽是因為家里原因,與夏知予打得那通電話無關。棄賽的事興許與無關,但是打架的事擺在那兒,他確實是因為自己跟那群人手并且了輕傷,事后還和家里人鬧得不歡。
“我收了胡編造第一名的圍巾,但是沒拿第一回來。這條圍巾,算是預付行不行?”
“預付?”
“嗯。預付。”
夏知予的兩側都是刺眼的白,只有前被寬大的影籠罩,看見許京珩眼皮微微下垂,像在看。
Advertisement
后時不時有別的班級跑過,廣播聲、腳步聲、談聲,很熱鬧。
可繞是這樣,也清楚聽到許京珩倨傲又張揚的聲音:“預付半年后,就算沒有保送,我也照樣在高考時給你拿個第一回來。”
-
回教室的時候,距離跑結束已經有一段時間了。陳閔見回來晚,忍不住問:“剛剛那個,是高三的許京珩嗎?”
大概是前段時間許京珩頻頻往高一跑,班級里的人都眼他了,也難怪陳閔看出來。
夏知予沒有否認。
“你們很嗎?”
“還可以。”
陳閔拿著筆,拔了筆帽又合上,重復了幾回相同的作:“平時還有別的聯系?”
在同班同學看來,二人除了傳話遞作業之間的流外,似乎沒有其他的集,非要定義二人的關系,充其量也只是認識而已。夏知予說‘還可以’,或許正是說明他倆之間的聯系不止這些。
夏知予不知道怎麼回答,程岐合時宜地轉過頭:“班長,咱們迎新晚會的節目定了嗎?”
“這事不是文藝委員在管嗎?”
“聽說你要上臺唱歌啊?哪種類型的?我覺得你適合唱民謠,抱著吉他,安安靜靜的那種。”程岐非常真誠地給他建議。
“可是我打算唱搖滾。”
“...”
四人小組盯著他那張文儒的臉安靜了一分鐘。
夏知予打圓場:“搖滾...搖滾也好的。也有那種溫抒的搖滾。”
“聲嘶力竭的那種不行嗎?”
程岐抿了抿,想起于左行的每次都想背越式過桿裝個,每次都摔在墊上的場面:“不是...你那麼叛逆干嘛呢?”
“我唱搖滾就是叛逆了?那許京珩是什麼?”
程岐沒想到自己一句話,把陳閔的脾氣點著了:“我只是覺得你的聲線適合唱抒歌。”囁嚅了一聲:“而且好端端的,你說人許京珩干嘛?”
Advertisement
“他這樣。不照樣討你們生喜歡?”
“什麼?”程岐以為自己聽錯了,但很快捕捉到了他話外之意:“聽你的意思,你是要學他啊?”
‘學’這個詞,又踩在了陳閔的雷區上:“我就是喜歡搖滾,想唱搖滾不行嗎?你怎麼這麼多話。”
“我只是給你建議!說都說不得了?”
程岐要跟他吵,被夏知予拉住了。氣吁吁地轉頭過,拿筆草稿紙:“不稚?莫名其妙的。”
-
高三(1)班那頭,文藝委員疲累地在講臺上做《高三最后的迎新晚會》的員,他講得繪聲繪,然而底下沒幾個容的。
“這不為難我們班嗎?像去年那樣,直接不參與不行嗎?”
不是他們不想參與,是班里總共五十幾個人,四分之三都是男生。另外的四分之一不是去藝考集訓,就是嗓門比音箱還大的直。
“不報名了唄。報了也丟人。況且高三節奏這麼快,別的學校都取消文娛活了,怎麼到了我們這兒還強制參與呢?”
文藝委員也去集訓了,臨時被一個男生頂上:“兄弟,別為難我了。我哪知道咱們校領導一天一個想法啊。說好每個班都報一個節目,咱們隨便出一個,讓我差行不行?拜托了。”
他掃了一圈,最后把視線落在末排的許京珩上:“哥。許哥。救一下行嗎?”
黎川坐他左前方,聽到文藝委員指名讓他上,笑得前仰后翻。
許京珩正刷題呢,被他一晃,拋線像飛機尾跡,直沖而上失了控。他一腳踹在黎川的凳上,踹得他給桌面磕了個響頭。
“干嘛啊你!他讓你救場,這難道不好笑嗎?”
許京珩長了一張德智勞全面發展的臉,在別人看來,他似乎樣樣能來,沒一個拉的。也就黎川從小跟他玩到大,知道他這人什麼都行,唯獨缺了點音。
這點缺失從兒園開始就端倪可察。每次到他們小太班合唱,他離調就離得特別突兀。有人說他是音樂鬼才,還真不是夸他,畢竟沒幾個間人能唱出他那間調。
偏他還不是個懂尷尬的人,每次唱歌都能唱出一種,只要我不尷尬,折磨的就是別人,并且還樂于其中。也就后來長大有了包袱,這才不輕易開口唱歌了。
“你們讓許京珩上去唱歌,不如讓他表演默劇。拿臉湊上啊。這也不至于太丟人吧。”
文藝委員不太相信黎川的話:“可是他明明長了一張很會唱歌的臉啊。”
“你沒看他高中兩年都不參加文藝活的嗎?他這是行好積德,看你們沒買保險保護你們耳朵呢。”
他瞥了黎川一眼,見沒反駁他:“嗯。所以,不救。”
作者有話說:
作收一百啦,發個紅包!
陳閔:我就要對標許京珩
許哥:不好意思,沒打算參加。我只想考第一。
任何人格測試都只應被看作是人們在其一生的某個特定時期的特定偏好的證明——菲利浦·津多
猜你喜歡
-
完結428 章

年代甜炸了:寡婦她男人回來啦
(全文架空)【空間+年代+甜爽】一覺醒來,白玖穿越到了爺爺奶奶小時候講的那個缺衣少食,物資稀缺的年代。好在白玖在穿越前得了一個空間,她雖不知空間為何而來,但得到空間的第一時間她就開始囤貨,手有余糧心不慌嘛,空間里她可沒少往里囤放東西。穿越后…
97.7萬字8 28516 -
完結10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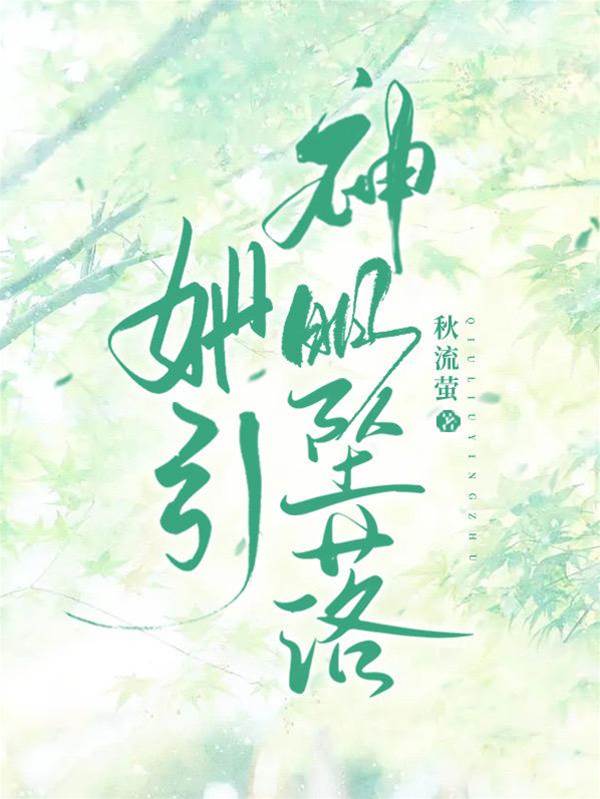
她引神明墜落
沈黛怡出身京北醫學世家,這年,低調的母親生日突然舉辦宴席,各大名門紛紛前來祝福,她喜提相親。相親那天,下著紛飛小雪。年少時曾喜歡過的人就坐在她相親對象隔壁宛若高山白雪,天上神子的男人,一如當年,矜貴脫俗,高不可攀,叫人不敢染指。沈黛怡想起當年纏著他的英勇事蹟,恨不得扭頭就走。“你這些年性情變化挺大的。”“有沒有可能是我們現在不熟。”宋清衍想起沈黛怡當年追在自己身邊,聲音嬌嗲慣會撒嬌,宛若妖女,勾他纏他。小妖女不告而別,時隔多年再相遇,對他疏離避而不及。不管如何,神子要收妖,豈是她能跑得掉。某天,宋清衍手上多出一枚婚戒,他結婚了。眾人驚呼,詫異不已。他們都以為,宋清衍結婚,不過只是為了家族傳宗接代,那位宋太太,名副其實工具人。直到有人看見,高貴在上的男人摟著一個女人親的難以自控。視頻一發出去,薄情寡欲的神子人設崩了!眾人皆說宋清衍高不可攀,無人能染指,可沈黛怡一笑,便潦倒萬物眾生,引他墜落。誰說神明不入凡塵,在沈黛怡面前,他不過一介凡夫俗 子。
20.2萬字8 45509 -
完結221 章

春意入我懷
【大學校園 男二上位 浪子回頭 男追女 單向救贖】【痞壞浪拽vs倔強清冷】虞惜從中學開始就是遠近聞名的冰美人,向來孤僻,沒什麼朋友,對前仆後繼的追求者更是不屑一顧。直到大學,她碰上個硬茬,一個花名在外的紈絝公子哥———靳灼霄。靳灼霄這人,家世好、長得帥,唯二的缺點就是性格極壞和浪得沒邊。兩人在一起如同冰火,勢必馴服一方。*“寶貝,按照現在的遊戲規則,進來的人可得先親我一口。”男人眉眼桀驁,聲音跟長相一樣,帶著濃重的荷爾蒙和侵略性,讓人無法忽視。初見,虞惜便知道靳灼霄是個什麼樣的男人,魅力十足又危險,像個玩弄人心的惡魔,躲不過隻能妥協。*兩廂情願的曖昧無關愛情,隻有各取所需,可關係如履薄冰,一觸就碎。放假後,虞惜單方麵斷絕所有聯係,消失的無影無蹤。再次碰麵,靳灼霄把她抵在牆邊,低沉的嗓音像在醞釀一場風暴:“看見我就跑?”*虞惜是凜冬的獨行客,她在等有人破寒而來,對她說:“虞惜,春天來了。”
39.6萬字8.18 627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