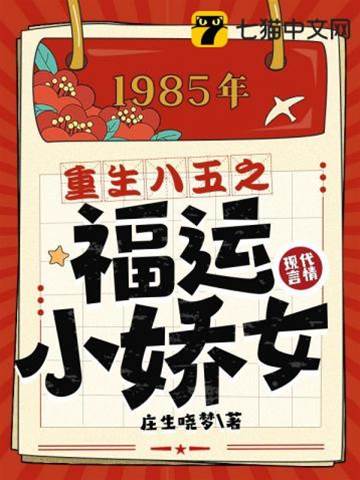《我的天鵝》 第39章 第三個愿望
余葵畫畫作很快。
課間在草稿本上打了底稿,最后一堂班會課開工,從料調到勾線上,只花了不到四十分鐘就搞定了。
功退,剩余的板塊只需要兩位生往里填充文字。
在洗手間把胳膊上的料都沖干凈,離放學還有四五分鐘。
這個時間,再專門回教室好像又沒必要,干脆活幾下僵的肩頸,在長廊放慢步子,涼風從發梢和臉頰掠過,等待放學鈴聲響起。
就站了那麼一會兒,樓上有一串略微倉促的腳步傳來。
接著,余葵聽見樓梯間響起陌生孩稍顯繃的喊聲。
“……時景!”
“你稍等,我、我能不能問你一件事?”
乍聽見這名字,余葵頓住了。
下意識往后退后兩步,躲進樓梯間的視線盲區。
倚在立柱上,余葵的心臟忐忑地怦怦狂跳起來,很清楚,禮貌的做法自己應該現在立刻走開,但腳下像灌了鉛,重得本挪不步子。
太好奇了。
生的聲音落下幾秒,男生的回答才姍姍傳來。
“我要去球場,你想問什麼?”
他的聲音很淡,萬事不經心般隨意散漫。
生頓了頓,像是在蓄積勇氣,余葵細聽,才聞見小聲開口問。
“我可以喜歡你嗎?”
“我對你沒有興趣。”
年的回答一針見且利落干脆。
他說罷繼續沿臺階下行。
生瞬間帶上了哭腔,淚流滿面,卻還是對著他的背影喊道:“我知道!”
“時景,我知道你可能從來沒有注意過隔壁班有我這麼一個人,但我還是喜歡你,喜歡你一年多了,我從來沒奢過能當你朋友,只是想把這份心意告訴你。明天就底考了,我準備了很久,就是為了考進一班,你能為我加油嗎?”
Advertisement
那樣真摯純粹的告白,連余葵聽了都忍不住容,然而年的腳步未曾停留,聲音依舊平靜毫無波瀾。
“與我無關。”
生站在原地啜泣。
哭聲隔著一層樓板約約傳來。
余葵也順著立柱蹲在地面,掌心冰冷,心生出一種兔死狐悲的悵然。
跟這生,何嘗不是一類人呢?
區別大概只在于,生本就在離他很近的4樓,而自己在吊車尾的15班,生有勇氣向他討要一句加油,而自己甚至連將喜歡宣之于口的勇氣都沒有。
也幸而,早就習慣了生命里的求而不得,幾次呼吸過后,調整好心起,余葵從墻后走出來。
一步、兩步。
沮喪盯著地面朝前走,視線猝不及防多了雙白球鞋。
形猛然頓住。
余葵大腦怔怔空白一片,不敢抬頭。
呼吸停滯幾秒,視線緩緩順著頎長的校服管上移——
年抄手兜,平靜漆黑的眼睛與對上。
這瞬間,余葵只恨不能化大魔法師,揮舞魔杖憑空消失在空氣里!
聽喜歡的人墻角被逮了個正著,誰能告訴,一個早該去球場的人,為什麼竟然還留在原地啊!
場那邊的彤云晚霞燒紅了半邊天空,一金圓日往地平線移,風吹得余葵短發嘩啦作響,下意識退兩步,想轉走開,年卻抓住的校服針織馬甲。
口型了,他聲線低沉,音量放得極輕。
“跑什麼?”
樓上的生還在哭,余葵反應過來,時景并不想讓對方知道他還留在這兒。
立刻擺手,跟著低聲,眼神真摯愧疚否認:“對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什麼也沒聽見。”
時景挑眉,顯然不信。
Advertisement
還要再說什麼,卻聽生的哭聲停了。
四周安靜下來,擤了下鼻涕,開始下臺階。
樓板上傳來拖沓悶重的腳步,昭示著主人此刻的心沮喪而沉重。
撞見人家那麼難堪的場面,余葵下意識想再閃躲起來。偏偏這次作晚了一步,剛藏的那柱子已經被時景霸占了,立柱的寬度僅夠擋住一個人的形。
“你!”
余葵氣得六神無主。
正打算要不直接出去,裝出若無其事的樣子跟生肩而過,手腕猝不及防被人掐住,一把帶了回去。
重重撞進時景的懷里,鼻梁差點斷在他肋上。
強行將痛呼咽進肚子,余葵仰頭,淚盈在睫上,睜大眼睛控訴。
年舉手,食指抵在瓣噓了一聲,而后,垂下天鵝般冷白的脖頸,俊朗的眉目微斂,隨手替了鼻子。
那作自然極了,像是在哄自家的小狗。
然而余葵心只剩一個念頭——
那是他剛剛還抵在瓣上的手指!
男生干凈的荷爾蒙氣息直沖腦門,帶著電流,余葵不知所措,整個心尖都在發麻震,手腳癱。
這…四舍五算接吻嗎?
一下一下,他骨節清晰的手指冰涼,指腹不算,帶著一點兒常打球磨起的薄繭,打圈的鼻尖時,像羽劃過般帶著舒服的意。
手下的力道不輕不重,卻仿佛被什麼到一般,整個形往后掉。
告白的生腳步聲已近在咫尺。
怕余葵出形,時景收臂彎,攬著腰肢將人帶回幾寸,相的瞬間,他整個人的影將孩籠罩,影子在夕下合一團。
世上就是有人擁有著致命的吸引力,像行星的重力一樣無法更改。
Advertisement
遠離時景那麼久,余葵原以為自己能修煉出一點兒自控力,但只是這麼鼻息相撲的一瞬間,便被本能重新俘獲,五里只剩他的存在。
過去大半年,兩人在學校說話的次數,扳著手指都能數得過來,就是再普通不過的同學關系,連中午拍合照那會兒,兩人也鮮有互。
但這一刻,時景的作,卻令重新生出,他們的關系較別人更親的錯覺。
人漸行漸遠。
余葵趕退后兩步,遠離他的懷抱,像剛從水里上岸的魚,不著痕跡使勁吸了幾口空氣,才問,“你干嘛搶我位置?”
“還說沒聽。”
年角微翹,凌冽的眉眼傾笑意。
余葵訕訕,小聲道:“我就是路過,怕你們尷尬。”
時景坦然。
“那我更應該躲起來,或者你想看滿臉鼻涕眼淚,下來撞見我,再尷尬一次?”
余葵瞬間熄火。
“好吧,你怎麼說都有道理。”
放學的鈴聲響起。
危機遠去,和時景相的張也重新漫上心頭。
學生們陸續從教室里出來,怕人多眼雜,余葵提前往下走。
看時景還是和并肩,沒有要分道揚鑣的樣子,努力平復呼吸,試著開口,“你剛留在這兒聽哭,是怕做出什麼不理智的事嗎?”
“不啊。”
年聳肩,“我就想看看,你打算躲到什麼時候出來。”
余葵大驚,“你什麼時候發現我的?”
“我等一下那會兒。”
時景指了指樓梯間墻壁上的倒影,風拂過時,將迎風飄起的短發拓印得分明。
竟然從一開始就被發現了!
余葵肩膀一塌。
表面勉力維持鎮定,心底的小人差點沒投湖自盡。
以為自己機靈,結果在別人眼里跟個一傻子似的。
Advertisement
到架空層,后頭下來的學生越來越多。
余葵加快腳步,離開前,時景站定,揚聲喚住。
“余葵。”
時景上次念名字是什麼時候?
再次聽到男生聽而低沉的嗓音字正腔圓吐出這兩個字,余葵只覺得整顆心都迷瞪瞪地,分不清東南西北,失神轉頭。
夕給年披上一層和的金芒。
他校服敞開,形拔漂亮,沉靜的目仿佛宇宙里令人沉溺的黑,在拖拽著往下跳。
“你……沒有什麼想跟我說嗎?”
四面八方的視線投來。
學生們或許聽不清兩人談容,但像時景這樣的風云人,會在校園行道上,主住生,跟說話,無需任何親舉,便足以發旁人想象。
有學妹甚至放慢腳步,駐足,余朝這邊瞥來。
他想聽說什麼?
不是都道過歉了嗎?余葵不解。
從448分到620分,每一個挑燈夜讀、掐點做題,快要撐不下去的日子里,余葵都曾想象,假如有一天,能明正大與時景并肩同行,該說點什麼。
只是現在,遠不到那時候。
時景幾分鐘前冷漠拒絕旁人的樣子還歷歷在目,余葵不敢賭,也賭不起。
垂眸,又掀起眼皮。
歪頭輕松地笑了笑,“其實,我也想進你們一班,就是分數差蠻多的。”
“差多?”
時景沒有嘲笑的夢想,偏頭沉片刻,仿佛真的在思考能考進一班的可能,然后道。
“如果你今晚有空看,我可以把純附歷年高三的實驗班選拔套題借你。”
“你們一班還有這種東西?”
余葵驚喜得差點沒控制好音量。
瓣緋紅,細白的臉頰在下閃耀著彩。
去年穿還稍大的百褶,如今已短過膝蓋。
長高了,長且細白,校服襯衫外面套著針織馬甲,勾勒出纖細的腰圍。
亭亭立在那兒,像是一株從未過風吹雨打的鮮玫瑰,萬事從未真正在上留下痕跡,有令人想要占有的堅韌稚拙,本真爛漫。
時景費很大勁才錯過目,平靜道:“老師發的,我用不上。”
猜你喜歡
-
完結73 章

霍先生的妄想癥
薛小顰通過相親嫁給了霍梁。 這個從骨子里就透出高冷與禁欲的男人英俊且多金,是前途無量的外科醫生。 薛小顰以為自己嫁給了男神,卻沒想到婚后才發現,這男神級的人物竟然有著極為嚴重的妄想癥。
24.6萬字8 9098 -
完結38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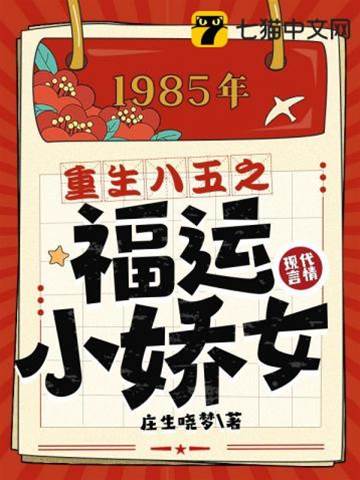
重生八五之福運小嬌女
前世,喬金靈臨死前才知道爸爸死在閨蜜王曉嬌之手! 玉石俱焚,她一朝重生在85年,那年她6歲,還來得及救爸爸...... 這一次,她不再輕信,該打的打,該懟的懟。 福星錦鯉體質,接觸她的人都幸運起來。 而且一個不留神,她就幫著全家走向人生巔峰,當富二代不香嘛? 只是小時候認識的小男孩,長大后老是纏著她。 清泠儒雅的外交官宋益善,指著額頭的疤,輕聲對她說道:“你小時候打的,毀容了,你得負責。 ”
70.5萬字8 19144 -
連載940 章

替嫁新婚夜,植物人老公要離婚
甜寵1v1+虐渣蘇爽+強強聯合訂婚前夜,林婳被男友與繼妹連手設計送上陌生男人的床。一夜廝磨,醒來時男人不翼而飛,死渣男卻帶著繼妹大方官宣,親爹還一口咬定是她出軌,威脅她代替繼妹嫁給植物人做沖喜新娘。林婳???林婳來,互相傷害吧~林妙音愛搶男人?她反手黑進電腦,曝光白蓮花丑聞教做人。勢力爹想躋身豪門?她一個電話,林氏一夜之間負債上百億。打白蓮,虐渣男,從人人喊打的林氏棄女搖身一變成為帝國首富,林婳眼睛都沒眨一下。等一切塵埃落定,林婳準備帶著老媽歸隱田園好好過日子。那撿來的便宜老公卻冷笑撕碎離婚協議書,連夜堵到機場。“好聚好散哈。”林婳悻悻推開男人的手臂。某冷面帝王卻一把將她擁進懷中,“撩動我的心,就要對我負責啊……”
112.4萬字8.18 3132 -
連載833 章

人潮洶涌
周稚京終于如愿以償找到了最合適的金龜,成功擠進了海荊市的上流圈。然,訂婚第二天,她做了個噩夢。夢里陳宗辭坐在黑色皮質沙發上,低眸無聲睥睨著她。驟然驚醒的那一瞬,噩夢成真。陳宗辭出現在她廉價的出租房內,俯視著她,“想嫁?來求我。”……他許她利用,算計,借由他拿到好處;許她在他面前作怪,賣弄,無法無天。唯獨不許她,對除他以外的人,動任何心思。……讓神明作惡只需要兩步掏出真心,狠狠丟棄。
149.8萬字8.18 259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