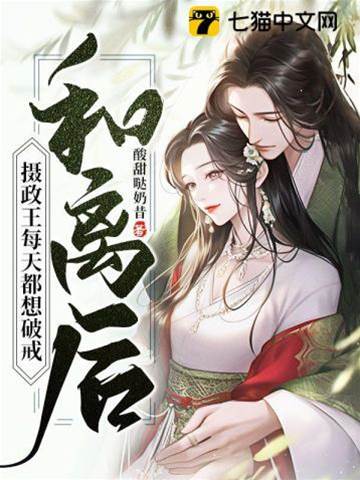《云鬢楚腰》 第186章 第 186 章
186
傍晚下了點淅淅瀝瀝的雨,下雨天的夜里,一貫是最好眠的。惠娘快步進來他們的時候,江晚芙才從睡夢中醒來,人還不是很清醒,聽到惠娘有些焦急地道,“方才紅蕖過來說,姚小郎君發熱了,燒得說胡話了。”
聽了惠娘的話,睡在外側的陸則二話沒說,已經坐起來穿靴了,起把外袍披上。江晚芙也催促惠娘去取的來。
屋燈火尚朦朦朧朧的,陸則系上腰帶,才轉過來與說話,聲音倒是一如既往的不疾不徐,他道,“我過去看看。”
江晚芙心里也著急,小孩子有個頭疼腦熱,是很尋常的事,但姚晗這孩子不大生病,這還是第一回。點頭,“我同你一起去……”說著,看見惠娘抱了過來,便要掀了被褥下來。
卻被陸則抬手攔住了,他眼神里明顯流出些不贊同,但說話卻很溫和,他不大對說什麼重話,“我去就行了。”
惠娘過來,正好聽見夫妻二人的話,也跟著勸道,“外面還下著雨,娘子還是不要過去了,免得了寒。您現下又吃不得藥……”
惠娘苦口婆心,江晚芙也知道,自己現在在他們眼里,跟易碎的花瓶也沒什麼差別,也沒有再堅持,反正有陸則過去,比自己過去還覺得安心些,便點了點頭,答應下來,“好。”
陸則見仰臉著他,脂未施,顯得乖順而,他心中也不由得發,俯抱了抱,起后,從丫鬟手里接過大氅,穿上就出去了。婆子拎了燈籠走在前面,穿過廡廊,很快就到了。
屋里蠟燭都點上了,陸則踏進去,去床邊看姚晗,蠟燭昏黃的照著,小孩兒臉慘白,額上、鼻尖冒著冷汗,陸則了他的額頭,果然是滾燙。
Advertisement
紅蕖端了水盆進來,眼睛還有點紅,擰干帕子,敷在小主子額頭上。然后就退到一邊站著了。
陸則在床邊坐著,問紅蕖話,“什麼時候病的?”
紅蕖并不敢推責任,跪下去回話,“……中午從您那里回來后,小郎君就沒什麼胃口,晚膳也用的不多。奴婢以為小郎君只是讀書累了,便勸他早些睡下。半夜守夜婆子進屋蓋被子的時候,才發現的。請世子責罰。”
小孩子食不振,那很可能就是生病了,一般有經驗的婆子都知道。紅蕖雖是大丫鬟,但到底沒養過孩子,難免有些疏,不知道小孩子是很容易病的,不注意吹了冷風,或是了驚嚇,都會這樣。
從他書房回去就病了?陸則皺了下眉,沒有再問,冷淡道,“先起來,其他事明日再說。”
棣棠院里本來就有大夫,趕過來也很快,退燒的藥丸子用熱水喂下去,退燒還沒那麼快,但姚晗已經沒有不安地翻來覆去,甚至說些胡話了,整個人安靜下來了,乖乖地平躺著。陸則看了眼,起到門口,了個婆子,“去跟夫人說一聲,沒什麼大礙了,我今晚在這里守著,讓不必等。”
婆子躬應下,一路小跑去傳話了。
陸則轉回屋,下人泡了濃茶進來,他不睡,一屋子的丫鬟婆子也不敢撤下去,俱膽戰心驚在屋里門外干站著,陸則也沒有發話讓他們下去,在他看來,阿芙下的手段,總還是太和了些,讓做點殺儆猴的事,又下不了這個狠心,索他替來做吧。
時間慢慢地過去,茶已經涼了,下人重新進來,把冷了的茶換熱茶,已經過了兩更天了。紅蕖匆匆從間出來,“世子爺,小郎君醒了……”
Advertisement
這話一出,里里外外伺候的丫鬟婆子,都松了口氣。陸則這才開了口,“留幾個伺候的,其他人散了吧。”
換了一貫寬容的主母如此折騰下人,他們大概還會私下抱怨幾句,可換了一貫嚴厲的世子爺,就沒人敢說這話了,個個恨不得恩戴德,覺得自己逃過了一陣罰。
陸則進屋去看姚晗,丫鬟正在旁小心問他,“郎君不?想不想吃點什麼?”
姚晗搖搖頭,看見走進來的陸則,一下子有些張起來,后背一下子離開了枕,小聲地了句,“叔父。”
陸則點頭,直接替他拿了主意,“去一份小米粥,再蒸碗蛋羹來。”
丫鬟聽了后便下去了。陸則手,了小孩兒的額頭,還有點燙,但比起剛剛要好些。紅蕖端了一盅梨子水上來,陸則看了小孩兒一眼,多問了句,“自己能喝麽?”
姚晗忙點頭,他可不敢讓陸則喂他,梨子水很甜,但姚晗基本沒喝出什麼味道來,胡地喝完了。紅蕖端了空了的白瓷小盅,退了出去。
陸則其實不大會照顧小孩兒,但也知道生病了要多休息,等他吃了小米粥和蛋羹,便他躺下去,將被褥好,了他的額頭,聲音不算很溫,“睡吧,我今晚不走。”
姚晗閉上眼,不敢直視陸則,覺得鼻子酸酸的,像是被什麼堵住一樣。在他為數不多的記憶里,生病都是很難熬的,娘親沒有錢給他買藥,只能抱著他,乞求長生天的保佑。哪怕給牲畜看病的蒙醫,也不會給“漢人小雜種”看病。
也不會有甜甜的梨子水和溫熱的小米粥。
陸則在床邊坐了會兒,看見小孩兒不知道什麼時候睜開了眼,臉上還有點紅,不知道是不是被子里太熱了,他問,“怎麼了?”
Advertisement
姚晗抿抿,有點難以啟齒地道,“我想小解。”
方才喝了一盅梨子水,小米粥和蛋羹也是湯湯水水的,也難怪他睡不著了。陸則嗯了聲,姚晗得了允許,便掀了被子,穿了鞋,正準備爬下床,便被陸則一把抱起來,扯過一旁大氅裹上,姚晗紅著臉,也不敢掙扎。
陸則在門口把他放下,陸則的大氅對小孩兒來說太長了,拖在了地上。陸則倒不在意,“自己進去吧。”
他覺得對男孩子,總是不能太溺,還是要教養得嚴格點。生了病可略放寬些,但也不能太寬容。
過了會兒,姚晗便出來了,陸則照樣抱他回去,姚晗趴在他寬闊的肩頭,到了床邊,陸則俯要將懷中的小孩兒放下,卻察覺到一陣拉扯,小孩兒攀住了他的肩膀,害怕似的了句,“叔叔。”
生了病,略氣幾分,陸則能夠理解,也并沒有嚴厲對待他,拍了拍小孩兒的后背,“病好了就不難了。”
他這一句安,卻沒有什麼效果,姚晗忽然哭出了聲音,小小的子一一的,他哭得很厲害,哭得陸則都覺得莫名其妙,這麼小的小孩兒,哪里這麼大的委屈了?此時,卻見姚晗松開了手,掉了眼淚,仰頭看著他,像豁出去了一樣,表很堅決地說,“叔叔,我有話要和你說”
陸則還以為他了什麼委屈,點了頭,“嗯,說吧。”
姚晗用袖子掉眼淚,作太用力,眼睛邊上都被他紅了,有點刺痛,但他也沒有在意,咬咬牙,小聲地道,“今天中午在書房,那個東西,你和嬸娘不要……那是害人的東西。”
陸則聽得微愣,姚晗卻以為他不信他的話,他只是個小孩子,說出來的話,很多大人都不會當一回事,他怕陸則也是如此,忙著急地拉住大人的袖子,急急地道,“是真的,我親眼見過!吃的時候會很舒服,但沒有的時候就會發瘋,跪在地上,跟狗一樣求別人給……叔叔,你不要吃,也不要讓嬸娘吃!”
Advertisement
陸則沒有說自己信或不信,只道,“我不會吃,也不會給你嬸娘吃。不過,”他的聲音頓了頓,語氣并沒有變,這說明他尚沒有用對敵人的方法,對待姚晗,“你一個孩子,怎麼會知道這些?”
如果像姚晗說的,這東西這麼危險,那他怎麼會知道?他一個孩子,有什麼機會接這些東西?如果不弄清楚,他不可能把他留在阿芙邊。
姚晗沉默了會兒,并沒有孩子似的哭鬧,良久才說,“……我娘是蒙古人。”
姚晗沒有抬頭看陸則的眼神,慢慢地把一直藏在心底最大的說出來。
他母親是蒙古人。娘告訴他,他有好幾個舅舅,都被強行征丁伍,一個也沒有回來。后來家里沒有男丁了,外祖父也被帶走了,再無消息。家里只剩下人,那些強盜一樣的騎兵搶走了家里的牛羊,在那種沒有什麼禮義廉恥的地方,人不是人,只是牛羊。
……
被□□□□的時候,被收兵回程路過的將軍救下。將軍下披風,裹住的軀,和襤褸衫下的痕跡。然后,將軍將帶回了家。激將軍的恩,留在了他邊,心甘愿為他洗做飯,只是生了一張蒙古人的臉,甚至連漢話也是磕磕的,在邊關那些城鎮,任何一家都可能有兒子死在蒙古人手上,反之亦然,敵對和仇恨沒有一刻停止。
不能踏出這間不大的院子,但甘之如飴,把這一方小天地視作自己的家,在廣闊的草原,卻心甘愿畫地為牢。
上了將軍。將軍亦不嫌棄的出和過往,兩人以夫妻相稱。
將軍很忙,總是要打仗,總是要打仗,好像打不完一樣,守著小院子,將軍來的時候,便很高興。可是有一天,再也沒有等到他了。
足足有一個月。
踏出那間從未踏出的屋子,遮住臉,用不大練的漢話,打聽著將軍的消息,終于從一個小兵得到他的下落。
“姚副將沒了……野狐嶺一站,打得太慘烈了。只可惜姚副將年紀輕輕,尚未家,連子嗣也未留下。”
陸家軍厚恤家眷,只要去軍營,隨意找一個人,告訴他自己的份,就可以拿到田地和銀票。但沒有去,的人是保家衛國的大英雄,哪怕他保的國,并非的國,也要守住他的后名。一個保家衛國的大英雄,怎麼能勾結蒙賊?
離開了,不能在漢人的地盤謀生,便一路北上,想出關。走得很艱難,暈在路上,被一家農戶救下,主人是個心善的大娘,長子死在一次戰役里,唯一的兒子就不再被要求伍,大娘恨蒙古人,但還是了惻之心,告訴,“你懷了孩子,四個月了。你太瘦了,所以這個月份都看不出來。”
留下了,直到生下一個孩子,是個男孩兒,和將軍的孩子。
將軍教漢字時,曾說過,晗,是天快要亮的意思,也是希。給孩子取名為晗,告別了大娘一家,回到了蒙古。孤的婦人,帶著孩子,只能做些活,替一戶人家漿洗。這家的爺是個游手好閑的公子哥兒,無需伍,整日出賭場青樓,服用一種金毒的東西。
……
姚晗至今還記得那一幕,瘦骨嶙峋的男人手中拿著金毒,剛買來還貞烈求死的漢人奴,像牲畜一樣跪在地上,赤//,在一群馬奴瞇瞇的眼神里,手掉裳,雪白的、帶著青紫傷痕的/在外,撕心裂肺地哀求著男人。
娘親捂住他的眼睛,不許他多看,并告誡他,“那個東西,一輩子都不能。你要是了,娘一定打死你!”
他嚇得直點頭,后來眾人散去,那個漢人奴赤昏倒在馬圈邊,娘親將背進屋子里照顧。
但那個漢人奴并沒有活很久。清醒的時候越來越,發瘋的時候越來越多,醒著的時候,會教他說漢話,說了幾句,就會掉眼淚,哭著說,“我想我爹,我想我娘,我想回家……”
瘋的時候,又回咬牙切齒地掐住他的脖子,惡狠狠地說,“我要殺你們這些蒙古人!我要殺了你們!”
后來,奴死了,曾經雪白的軀已經瘦骨嶙峋,上沒有一點,眼睛深深凹陷下去,像一活著的骷髏。的尸首,也被丟棄了出去。
后來,娘也病了,臨死前,拉著他的手,要他跪在的床前發誓,一輩子也不要說出自己上流著蒙古人的。他對著長生天發誓后,母親的神和下來,抱著他說,“你父親是大將軍,是大英雄。晗兒長大了,也要做明磊落的大英雄。還記得娘跟你說過的恩人麽?等你長大了,有本事了,一定要替娘報答他們一家。”
他哭著點頭。奄奄一息的母親就一遍遍地乞求長生天、乞求父親,“讓我的孩子,一輩子平平安安的……平平安安……歲歲平安、年年平安。平平安安……”
娘死了,他聽母親的叮囑,把銀子藏在服夾層著的袋子里,吃很的飯,盡可能幫大人的忙,馬圈的男人會打他踹他發泄,但他們默許了他留下,過了那個難熬且漫長的冬天,他離開了那里,去找母親口中的“和父親一樣也是大英雄的人”。
他找到了,很幸運,他長得像父親,高大的男人抱著他,他的腦袋,“小家伙,你很像你父親小時候。”
后來,他帶他回到京城,把他帶到了嬸娘邊。
猜你喜歡
-
完結476 章

公主能有什麼壞心思
鐵血女將軍中黑箭戰死沙場,穿越成鄰國嫡出的公主蘇卿卿。一道和親圣旨讓蘇卿卿重回故土。捏捏拳,抖抖肩,我倒要看看到底是哪個王八蛋害死的我!(一年前)某男主:認清你自己,我們只是彼此利用而已。(一年后)某男主:我錯了!!!
87萬字8 76210 -
完結511 章

神醫嫡女:寵妃她風華絕代
京城人只知道丞相府有個嫡女顧傾城是第一美人,卻不知道顧錦歌才是丞相府的嫡長女。 丞相顧承恩出身寒門,高中狀元之后迎娶了一品驃騎大將軍的妹妹陸筠清,眾人都道是天作之合,金童玉女,兩人婚后生下長女顧傾城,次子顧淳風。 卻沒人知道,顧承恩在入京考取狀元之前已經迎娶了妻子,在他離開故鄉的時候,妻子已經懷孕,生下了嫡長女顧錦歌。
90.5萬字8 36170 -
完結567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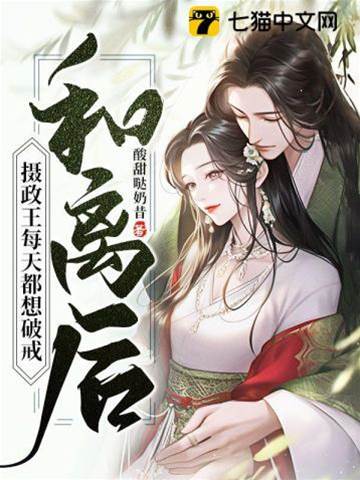
和離後攝政王每天都想破戒
葉芳一朝穿越,竟然穿成了一個醜得不能再醜的小可憐?無才,無貌,無權,無勢。新婚之夜,更是被夫君聯合郡主逼著喝下絕子藥,自降為妾?笑話,她葉芳菲是什麼都沒有,可是偏偏有錢,你能奈我如何?渣男貪圖她嫁妝,不肯和離,那她不介意讓渣男身敗名裂!郡主仗著身份欺辱她,高高在上,那她就把她拉下神壇!眾人恥笑她麵容醜陋,然而等她再次露麵的時候,眾人皆驚!開醫館,揚美名,葉芳菲活的風生水起,隻是再回頭的時候,身邊竟然不知道何時多了一個拉著她手非要娶她的攝政王。
99.6萬字8 9206 -
完結422 章
我養成了未來殘疾暴君
生在聲名煊赫的姜家,眉眼嫵媚動人,姜嬈天生有財有顏有靠山,一生本該順遂安逸,偏偏得罪了九皇子。 九皇子雙腿殘疾,纏綿病榻多年,性情扭曲,眾人眼中陰毒薄情的怪物。 奪嫡成功后,將之前得罪過他的人通通收拾了個遍,手段狠戾絕情—— 包括姜嬈。
63.4萬字8 2107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