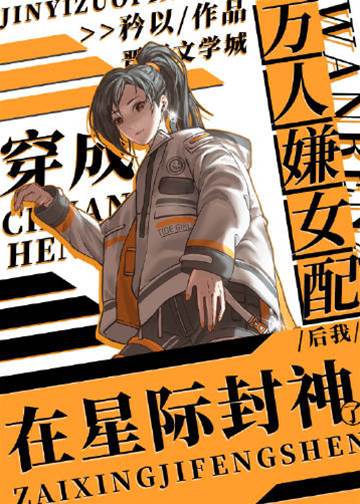《快穿之我養的崽全是炮灰》 穿越女判我女兒有罪19
這個家分了三天才掰扯明白,這還是三房四房什麼都不爭的況下,即便如此,周氏還是一病不起。
要不是知道又多恨兩個庶子,還以為江黎和江順是的心頭呢,這麼舍不得。
分家之后,一家人住到了城郊的莊子里,這是原主姜氏的陪嫁,嫁妝都給拿回來,歲禾覺得神清氣爽。
最開心的莫過于江聽雨了,分家之后覺的天都特別藍,每天起床不用給祖母請安,不用看的臉,也不需要再和江家人虛以委蛇,這日子自在得像是在夢里,本以為只有嫁人才能實現的,現在爹娘就給辦到了。
這莊子離江黎的工坊很近,兩父天就泡在那里,回來吃飯都不。
歲禾在準備著搬家到京都的一切事宜,現在就等著江黎的科考績下來之后,就可以舉家搬遷了。
江家的態歲禾一直關注著,多事的,周氏病得越來越重了,江觀雨又一次自殺被救下了,江然見一心求死,死咬著是兒江聞雨害了,江然也不打算在追究給他下毒的事兒了。
因為以前他不信自己的兒會做出這種事,但現在嘛,誰知道呢?江聞雨確實是一個狠心腸的孩子,就連他這個做爹的都這麼認為。
先前有對江府不滿的家丁在外面傳了一些下三濫的流言,他本想找出傳謠之人置了,但江聞雨先他一步,置好幾個人,那家丁的一家人,甚至是關系好的,都給賣了,還賣到了那種不正規的人衙子里,下場可想而知。
也不能說這麼做是錯的,畢竟殺一儆百,這是最干脆也最有效的做法,但是才十四歲,這個心腸著實狠了一些。
一樁樁一件件事,都讓大房三人之間的隔閡越來越大。
Advertisement
分家了齊氏也是高興的,本來是想早點搬出去的,但江然這個孝子不忍將父母獨自留在宅院,畢竟現在他們倆都不好,三房四房都搬出去了,江恒還在牢里,現在就剩他一個兒子在了,當然要留在家里照顧啊。
江聞雨心梗得想吐,這個封建迂腐的父親,果然有著儒家男人傳統的,深骨髓,刻進了dna里的病。
說照顧父母,他照顧個錘子,每天看幾眼,都是丫鬟仆婦在伺候,要照顧也是齊氏照顧,而且瞧不上行醫,現在又要用醫來治療兩個老不死的……呵呵。
科考績是在會試之后的一個月出來的,放榜的地方幾乎被堵得水泄不通,但歲禾和江聞雨還是早早起來,拉著江黎一起去看榜了。
儀式還是要有的嘛!
江黎不懂這兩個人的什麼儀式,他自信自己名列前茅,府肯定會派人敲鑼打鼓通報,何苦來這個罪?
歲禾一手牽著江聽雨,一手牽著江黎,功到了榜前,但老早就看到了最上面,解元旁邊的‘江黎’二字。
江聽雨也看見了,一瞬間就熱淚盈眶,有些不敢相信,但一想到這段時間和江黎相時,他展現的學識,又覺得沒有什麼不可能。
大伯都能是經元,爹是解元怎麼了?
而江府那邊,江州錄早就提前收到了江黎是解元的消息,畢竟南洋府會試第一名出自織隴縣,還是他的兒子,他自然是第一個收到消息的。
知道這個消息的時候,江州錄呆坐在書桌上呆了半晚,直到累的熬不住了才去睡覺,第二天去衙門的時候,腳步都在打飄,吃什麼都沒有味道,因為什麼東西都沒有他心里的滋味復雜難言。
Advertisement
不僅如此,他作為縣令還要例行公事,派兵去江黎的府邸報喜,按理說他這個縣令也要見解元一面,對他表示嘉獎,然后給他戴紅花的。
但是,這個儀式得省了,他寄予厚的江然,是個經元,那時候啊他高興得拍派了好些兵到江府賀喜,即使是儀式也要走完,當時他是什麼心呢?恨不能向全世界宣告經元就是他的兒子……
江州錄閉起了眼睛……如果…如果他沒有耽誤江黎,他會不會已經是狀元了?
江黎不像江然和江恒從小就拜讀在大儒門下的,還是在讀書者的朝圣之地江南書院。他一直以來都是自學啊,不僅如此,他在讀書的時候還學會了那麼多格技藝,那是何等奇才啊!
江家人其實都很關注江黎的績,但他們都知道,要是江黎真的考得很好的話,他們心里不會好過。
可該知道還得知道,左右隔壁的鄰居都上江家來道喜了,畢竟江家出了個解元,而且他們也不知道江家人關系已經鬧了這樣。
喜是沒有報到,因為這對江家很多人來說都是噩耗,周氏剛在江聞雨的治療下好一點,就又臥床不起了。
而江然,他的心應該是最復雜的,他凄涼地自嘲一下。
原來……原來他真的不如三弟啊,一直以來他是江家的驕傲,但原來這一份驕傲是他母親給他搶奪而來的。
江然丟了魂的樣子讓江聞雨眉頭一皺,若往常定會覺得心疼,現在只覺得煩躁。
南洋府的解元而已,代表的了什麼?外面有那麼廣闊的天空,眼何不放長遠一點?何況江然不是在江南都才名顯赫嗎?何需妄自菲薄,這麼脆弱以后在場要怎麼混得下去?
Advertisement
江聞雨蹙眉沉思,不能再窩在織隴縣這個彈丸之地了,有什麼辦法能讓爹同意一起去京都呢?還不能讓兩個老不死的反對?
山江氏。
放榜之后,舞弊案終于也要審理了,江恒被搜出了他和題販子的來信,還有他付定金的時候摁下的手印,還有犯罪團伙的指認,他跑不了了。
被剝奪了終考試的資格,他的直系三代之都沒得考,除此之外,還要坐五年牢。
江恒廢了,這是所有人的共識,小周氏當場就暈倒了,二房六個孩子哭一片,最小的五歲的江賞雨,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但哥哥姐姐都哭了,娘親還暈過去啊,也跟著放聲大哭。
此起彼伏的哭聲就像是哀歌一樣,讓人心里不適。
江聞雨厭煩地回了自己的院落,屋偏逢連夜雨,鹽商家來退親了,江觀雨倒覺得這是個喜訊,至不用和那樣齷齪的人攪和一生。
江觀雨現在也是看了男人的臉了,整個江家最自私的就是江州錄,造如今的局面大半原因都是因為他,再則就是的父親,呵呵,真是可笑。
或許,不嫁人,絞了頭發當姑子就是最好的歸宿了。
江觀雨向小周氏提出了要出家,小周氏還躺在床上呆呆地看著天花板,半晌點點頭答應了。
鹽商家也不是好糊弄的,退親畢竟是因為江恒犯了法,正常人家不會娶一個舞弊犯的兒,江家理虧那自然是要退還聘禮的。
剛分完家的江家哪來那麼多錢?
于是,所有的人都盯上了最有銀子的江聞雨。
禍不單行,作為縣令,出了一個舞弊犯的兒子,他的烏紗帽還保得住嗎?當然不可能。
不出十日,江州錄就卸任了織隴縣縣長一職,讓他主卸任,已經是留給他最大的面了。
Advertisement
歲禾嘆了一口氣,回顧江州錄的前半生,時在山江氏的族學讀書,被洗腦被pua,一生都想得到宗族的認可,但他也只在年過四旬的時候考中了同進士,天賦平平的他,在山江氏的幫助下進了翰林院當編修,到也算清貴,但山江氏也之幫他到此了。
于是江州錄在翰林院呆了十年,一直修書,職是一寸都沒過,畢竟翰林院都是一些有家世有背景的人鍍金的地方,本不到他。
好不容易有個下放升的名額,他想從縣開始一展宏圖,結果就八年都沒有升,夢想還沒起航他就老得牙都掉了。
寄希于兒子吧,如今又是這般景,真好,希他有事,歲禾心里如是想。
啟程去京都的這一天,歲禾一家人還是去江家拜別了,畢竟古人重孝道,還是要做做樣子的。
周氏病得都沒有力氣起床膈應人了,江州錄倒是強打起神來見了江黎一面,得知江黎說是要去京都拜訪大儒,他點了點頭,半晌才說了一句:“好好讀書。”
去京都的路上,三人都不著急,可以說是游山玩水去的,江聽雨高興壞了,舟車勞頓都不覺得累,像籠中鳥被放出來一般,恨不能到哪兒都撲騰著翅膀,想飛到更高的地方去俯瞰天空。
到了京都,已經是兩個月之后,一家三口先是住到客棧里,好在歲禾早就了解過了京都的住房境況,解決起來比較快。
當一家人住進了三進的院子時,江聽雨都驚呆了,他們家這是傾家產買房子了嗎?京都寸土寸金,陪上娘的嫁妝外加上爹爹賺的銀子應該也不夠吧?
而且這個地段的宅府不是誰想買就買的,這里幾乎是都是高門大戶,是畫本子里最常出現的華街。
“娘親,咱們家哪里來的錢啊?”
歲禾心想,當然是詐騙了江家再加上錢生錢攢下來的,但這話不好說,“你爹這些年也不是全干傻事的,借著給人雕刻攢了不銀子。”
話題就這麼岔過去了,搬家真是一件很繁瑣的事兒,但三人都沒有到很麻煩,畢竟布置新家也是一件值得興的事,這里是他們重新開始一段新的人生的起點。
宅府太大,他們帶來的江家的兩個丫鬟和一個小廝已經不夠用了,雖然依舊覺得奴隸制很殘忍很變態,但也沒有辦法,鄉隨俗,歲禾得去買人了。
讓沒想到的是,在街上撞到了秦隨風和謝遇青,另外還有一個與他們同齡的男子,一看就是高門貴公子,三人談甚歡,看著關系不錯。
歲禾注意到,那秦隨風稱呼那個貴公子為“江兄”。
歲禾挑眉,那這人大概率就是山江氏這一代掌權人的嫡系后代了,現在山江氏在朝最大的就是江閣老了。
這也僅僅是表面上的,堂下朝臣不知有多員拐著彎和江家有關系,更別說地方了,流水的皇朝鐵打的氏族可不是說說而已。
但是現在嘛,皇帝是早就看世家門閥不順眼了,而且正一步步開始中央集權,大力培養天子門生就是一個信號。
舊識堂前謝家燕,是終要飛尋常百姓家的,歷史的洪流無法抵擋。
山江氏的嫡系子弟都出現了,魂不散的江聞還遠嗎?
歲禾知道穿越不會輕易放棄折騰,但也沒有想到能那麼快就帶著江然和齊氏殺來了京都。
布設宅子,外加修建宅子里的小工坊,和城郊外的大工坊,買商鋪等等一系列事宜,已經過去了兩個月,梅花都開了。
工部尚書家的梁夫人舉辦了賞梅宴,的第一個孫子也出生了,想要請大家沾沾喜氣。
本這也與歲禾一家無關,畢竟他們只是初來乍到的庶民,這種場合那肯定是不進去的,但是歲禾和江聽雨都收到了請柬,還是張老太君親自送過來的。
“梁夫人怎麼就邀請起我們母倆呢?”歲禾問道。
張老夫人笑道:“舉辦宴會的可是工部尚書家啊,你們家江黎的名聲那可是響徹整個工部啊,江黎提供的資料對工部研究鐵很有幫助,那高低是個功臣啊!”
歲禾點頭,那就不奇怪了,總歸以后也要是融的,邀請了那就去參加。
而站在歲禾后的江聽雨,默默又在心里給自己打了一把氣,又一次堅定了自己一定要為大晉第一格大家的心,就是要備矚目和禮遇,要人再不敢輕視,要千百年之后,后人連皇子公主都不記得,也要記住江聽雨的名字。
猜你喜歡
-
完結133 章
元帥他不同意離婚
林敬知和元帥自結婚後就從未見過面。 得知元帥有了心上人,在後者苦口婆心的勸說下,林敬知選擇了離婚。 因一年沒有同房記錄,系統判定離婚協議通過。 協議通過的下一秒,敵星的大本營就被炸爛了 協議通過的第九個小時,元帥站在了林敬知的面前 低情商禁慾研究院士受x腹黑狼狗戲精元帥攻 哨向cp 不虐,狗血甜餅文~~ 1v1 ps:強調一次,本文未來架空架空架空架空!任何設定請不要以現代標準代入謝謝!鞠躬了!
44.7萬字8 8759 -
完結17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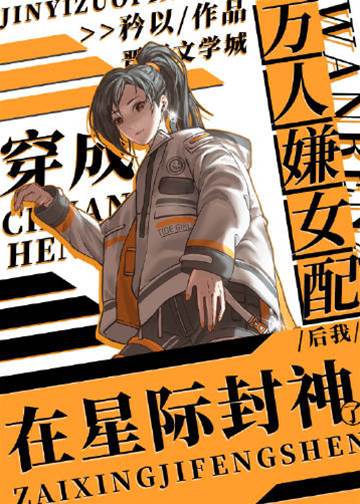
廢物機甲師是星際最強
別名:萬人嫌女配在星際封神了 時蘊從航天局首席研究員穿成了星際萬人嫌女配,還是個廢物機甲師。軍校排名賽中,東青軍校御用機甲師被集火淘汰,時蘊候補上場,星網集體唱衰。“東青這要不掉出四大頂級軍校了,我直播倒立吃鍵盤!”“押隔壁贏了。”“現在軍校排名賽已經淪落為關系戶表演賽…
106.6萬字8 6984 -
完結1011 章

我在異界當倒爺
我只想安安穩穩送個外賣,哪想到有一天居然真的黃袍加身! 還是在異界!! 送外買送到異界的恐怕僅自己一個了吧? 看著滿目荒涼的異界,楊一暖苦笑一聲,開始了異界探險之旅... 外賣是不會再送了,星際貿易才是我的主業! 玻璃球換黃金,香水換翡翠,一個黑心倒爺就此誕生... 異界投資建工廠,尋寶探礦搞開發,從今天開始,我就是楊總! 新世界首富,異世界征服者,就此誕生!!
184.1萬字8 2606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