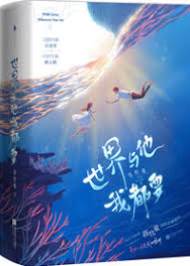《前妻難哄:教授追妻請排隊》 第80章 征服起來有難度
機票,是江暖提前買好的。
反正拽上姜予念就回宣城了,說回來也行,但是不能告訴江敘。
江暖知道在想什麼,于是就跟著回來了。
姜予念其實也知道,要是繼續待在寧城,怕是所有人都知道和江敘的那些事兒了。
雖然,也差不多所有人都知道了。
但為了最后那一點點面子,姜予念勉為其難地回來了。
當天晚上就被拉到酒吧里面來蹦迪。
要是姜予念知道江暖拉回來,是為了來蹦迪的,尋思著還不如在寧城待著呢!
一來魅,江暖就跟服務生打聽他們老板的事兒,服務生哪兒知道老板的事兒,給們下了單就走了。
姜予念直覺有什麼事兒,問道:“你打聽人家老板干嘛啊?又看上人家老板了?你們家非池哥哥呢,這麼快就被你拋棄了?”
江暖靠在卡座沙發里面獨自郁悶,“我先前不是跟你說了麼,那天去謝非池家里遇到一個人,我打聽過了,那個人就是魅的老板容鳶。”
Advertisement
“打聽得夠仔細的啊?”姜予念調侃一句,一點沒有回來的張,“你還想跟容鳶來個正面PK?”
“那我總覺得夜店老板的份和謝非池格格不啊?要麼,容鳶
為了謝非池放棄手頭上那些灰產業,要麼,謝非池下他一警服。”江暖已經將事分析得明明白白,“巨大的份懸殊,注定他們兩得分道揚鑣。”
“知彼知己,百戰不殆。”姜予念給江暖豎了大拇指,尋思著自己當初要是有江暖這樣的頭腦,說不定能讓江敘對自己死心塌地也說不定。
說著,姜予念瞥見了不遠一個周旋在男人堆里的尤。
“小暖,說實話,我覺得那個人說不定是謝非池的菜。你這樣的,太素了。”姜予念用下指了指斜右方的位置。
江暖轉過去看的時候,瞬間就怔住了。
Advertisement
那人不就是容鳶麼。
見江暖非常糟糕的表,姜予念似乎猜到了什麼,“是啊?”
江暖點點頭。
姜予念用非常挽尊的表看著江暖,小姑娘那還有什麼勝算啊?
人家那一個風萬種,深大波浪嫵地披在肩頭,港風復古大紅配上一襲小黑,香肩半。
手里端著一只高腳杯,修長白皙的手指上一抹紅指甲油與相呼應。
容鳶輕笑著,但那笑不達眼底,說是涼薄也不過分。
這般游走在男人叢中的人,本不需要用什麼手段,連手指頭都不用勾
,估計就有一堆男的上趕著過去示好。
姜予念覺得像謝非池那種渾荷爾蒙棚的男人,大概率會喜歡像容鳶這樣的人。
漂亮,野,征服起來很有難度。
江暖有點絕,問道:“我一點機會都沒有了嗎?”
Advertisement
“那也不是一點機會都沒有。”姜予念道,“要是謝非池不喜歡那掛的,再漂亮再都沒用。他要是喜歡你,你就算是再素,材再沒料,他還是喜歡你。”
所謂對另一半的條條框框,其實是設置給那些不喜歡的人上的。
一旦那個喜歡的人出現,所謂的條件,理想型,會在那一瞬間全部被打破。
江暖有些頹喪,拿起桌上的氣泡酒,“關鍵,人家不喜歡我啊……連我今年畢業都不知道。”
“既然他不喜歡,你也不要喜歡他了。男人千千萬,何必在謝非池一棵樹上吊死?”姜予念勸人的時候,才發現這些道理一套一套地從里蹦出來。
但到了自己這里,好像那些道理就行不通了。
道理都明白,可一旦發生在自己上,那些就全部都變了廢話。
猜你喜歡
-
完結199 章

惹不起的趙律師
遭遇家暴,我從手術室裡出來,拿到了他給的名片。 從此,我聽到最多的話就是: “記住,你是有律師的人。”
51.2萬字8 27139 -
完結548 章

沈先生大腿我抱定了
在小說的莽荒時代,她,喬家的大小姐,重生了。 上一世掩蓋鋒芒,不求進取,只想戀愛腦的她死於非命,未婚夫和她的好閨蜜攪合在了一起,遠在國外的爸媽給自己填了個弟弟她都一點兒不知情。 一場車禍,她,帶著腹中不知父親的孩子一同喪命,一切就像命中註定...... 對此,重生後的喬寶兒表示,這一世,她誰也不會相信! 左手一個銀鐲綠毛龜坐擁空間,右手......沈先生的大腿湊過來,喬寶兒傲氣叉腰,她就是不想抱,怎麼破? ......
99.3萬字8 28232 -
完結340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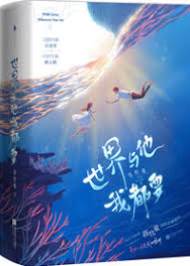
這世界與他,我都要
溫牧寒是葉颯小舅舅的朋友,讓她喊自己叔叔時,她死活不張嘴。 偶爾高興才軟軟地喊一聲哥哥。 聽到這個稱呼,溫牧寒眉梢輕挑透着一絲似笑非笑:“你是不是想幫你舅舅佔我便宜啊?” 葉颯繃着一張小臉就是不說話。 直到許多年後,她單手托腮坐在男人旁邊,眼神直勾勾地望着他說:“其實,是我想佔你便宜。” ——只叫哥哥,是因爲她對他見色起意了。 聚會裏面有人好奇溫牧寒和葉颯的關係,他坐在吧檯邊上,手指間轉着盛着酒的玻璃杯,透着一股兒冷淡慵懶 的勁兒:“能有什麼關係,她啊,小孩一個。” 誰知過了會兒外面泳池傳來落水聲。 溫牧寒跳進去撈人的時候,本來佯裝抽筋的小姑娘一下子攀住他。 小姑娘身體緊貼着他的胸膛,等兩人從水裏出來的時候,葉颯貼着他耳邊,輕輕吹氣:“哥哥,我還是小孩嗎?” 溫牧寒:“……” _ 許久之後,溫牧寒萬年不更新的朋友圈,突然放出一張打着點滴的照片。 溫牧寒:你們嫂子親自給我打的針。 衆人:?? 於是一向穩重的老男人親自在評論裏@葉颯,表示:介紹一下,這就是我媳婦。 這是一個一時拒絕一時爽,最後追妻火葬場的故事,連秀恩愛的方式都如此硬核的男人
52.7萬字8.18 7880 -
完結566 章

滿級熱戀:傅少嗜妻如命
【甜虐 偏執霸寵 追妻火葬場】“傅延聿,現在隻能救一個,你選誰?”懸崖之上,她和季晚晚被綁匪掛在崖邊。而她丈夫傅延聿,華城最尊貴的男人沒有絲毫猶豫:“放了晚晚。”聞姝笑了,她一顆棋子,如何能抵過他的白月光。笑著笑著,她決然躍入冰冷的大海……後來,沒人敢在傅延聿麵前再提“亡妻”……某日,傅延聿不顧場合將一女子堵在角落,如困獸般壓抑的看她:“阿姝,你回來了。”女人冷笑著推開:“傅少,你妻子早死了。”傅延聿隻是紅了眼,死死的拽住她……
98.2萬字8.18 4395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