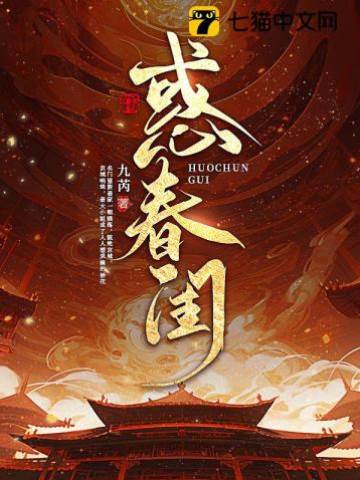《懷嬌》 第88章 第88章
琴聲停了,魏玠不聲地整理好袖,蓋住那些略顯可怖的傷痕,而后輕輕抬眼看向薛鸝,語氣疏離道:“魏玠不過無關要之人,不勞薛娘子費心。”
薛鸝還從未聽過魏玠這樣說話,語氣涼颼颼的,看似云淡風輕,實則夾雜著尖刺,倘若當真順著魏玠的意思不理會他了,只怕他還要暗自生悶氣。
簡直想要質問魏玠,既然故意彈琴引前來,何必還要強撐著一副冷臉不愿與說話。
薛鸝也有些惱火,早該與魏玠斷干凈了,如今還掛念著他做什麼。何況前一回不過是喚了一聲表哥,便引得趙郢拈酸吃醋害慘了他。倘若藕斷連,只怕是彼此都不好過。
想到此,薛鸝猶豫了一番,起便要走,卻聽到嗡的一聲,魏玠的手掌重重地覆在琴弦上,含怒的目朝投過來,仿佛看出了的意圖。
“薛鸝,你從來都是如此,想來便來,想走便走,我于你而言,便如此不值一提,是不是?”
魏玠的語氣有幾分不穩,薛鸝甚至能聽出他強著的怒火下還有幾分委屈。
想了想,還是下語氣,說道:“我怕連累你,趙郢若是知曉,你在軍中不會好過。”
聽到這句話,魏玠的面才稍稍緩和了些。
“我已命人截開了他的耳目,此不會有旁人。”他淡聲說完,薛鸝忍不住輕笑一聲。
分明心中想前來,如愿來了,又賭氣不肯好好說話。
魏玠知道心中在想什麼,也沒有心思再計較了。
自從醒來后,幾次見魏玠都是匆匆一眼,一直沒能好好與他說上幾句話,其實還有很多話想問,堵在心里日夜不能安穩。可如今真的有了機會,卻又不知道該如何開口了。
Advertisement
薛鸝思緒萬千,話到了邊,卻化為一聲悵然輕嘆。
“你的傷如何了?”
“并無大礙。”
聽著魏玠平靜的語氣,不知為何眼前有些泛酸,低聲道:“你莫要傷心難過,度過了如今的坎坷,日后你定能重回云霄。”
魏恒與平遠侯都不約而同地選擇了梁晏,以至于援兵趕來太遲,魏玠心中應當是有恨的。
“若我再回往日的風,你可愿與我婚?”魏玠的眼眸中躍著火的倒影,讓他的眼神都變得明亮灼人。
薛鸝沒有立即回答他的話,猶豫片刻后,問道:“你明知我活下來,定會轉投趙郢,甚至會借此機會報復你,為何還要留我命。你分明……”
分明沒有這樣的好心……
魏玠的目落在那略深的琴弦上,也不知是想到了什麼,面上出了些和的笑意。“我仍是不大甘心,想知曉你心里是否有我。讓你就此死去,我竟也不愿了。”
看到薛鸝奄奄一息地躺在床榻上,他竟生出了一種從未有過的恐慌,甚至覺著倘若平安無事,讓他放手也好。如此想了,他便如此做了。
比起眼睜睜地看著凋零,如今仍鮮活地站在他眼前,即使心中有怨,他亦能忍。
薛鸝悶聲不答話,便聽魏玠繼續說:“你心中有我。”
終于忍不住了,惱地扭過頭去,正要反駁,卻對上魏玠一雙亮盈盈眼眸。尖銳的話當即便說不出來了,于是只能悶悶道:“那又能如何。”
心中有魏玠又如何,些許真在此刻本是無關要。
“已經夠了。”
薛鸝沒有否認,魏玠因此而愉悅了許多,面上總算浮現了幾分笑意。
他傾靠近,抓著薛鸝的手腕,啟去吻。薛鸝知道再這樣下去只會害了彼此,卻沒有立即推開魏玠,仍是縱容了他的作。
Advertisement
魏玠似乎要用這個吻發泄幾日來的怨憤,吻得又深又狠,薛鸝幾乎窒息。不知不覺著,襟也松散了,夜風拂過,到衫中的涼意,扶著魏玠的肩,說道:“我要回去了。”
“我不許。”他強道,而后繼續上前吻。
薛鸝總覺著這是彼此最后一次如此親,趙統不如趙郢一般是輕易可以應付的人,北上與趙統會和后,自然要謹言慎行,不能與魏玠再有往來。
想到此,也沒有了阻止的心思。
魏玠將抱在懷里,扣著的腰,火照在上驅散了些涼意。
綢緞似的發散落,又如湖面的水波一般起伏搖。
薛鸝背對著魏玠,看不清他面上的表,卻能清晰地到他的一呼一吸。
“表哥……”薛鸝的嗓音不由地發,近乎甜膩,語氣也略顯不穩,仍是強撐著開口道:“今日之后,你我便莫要……”
的話被魏玠打斷,悶哼一聲后便沒了下文。魏玠伏在肩頭,輕聲道:“你方才想說什麼?”
他語氣溫,卻又十足的狠。
薛鸝眼角噙著淚,咬牙道:“我與趙郢遲早要婚,你若甘愿做夫,我自是沒有異議……”
的話甚至有商量的意味,能到魏玠在聽到這句話后作有過片刻凝滯,而后他氣極反笑,手指掐著的下頜,毫不掩飾憤怒的語氣。
“薛鸝,有些時候,我是當真想要掐死你。”
薛鸝說完也后悔了,只怕要讓魏玠這樣高傲的人與通,比讓他降城來的屈辱還要大。
然而此刻再想收回也是無用,惹火了魏玠,他便再沒了憐惜,怒火化為狂風驟雨似摧折。
事畢后,魏玠將帕子放下,替仔細系好帶,還要再替整理發髻。薛鸝卻忍不住了,紅著臉瞥了眼他的擺,說道:“你先顧好自己,莫要管我了。”
Advertisement
魏玠掃了一眼,不以為意地湊上前親了親的角,低聲道:“與人親的事,你想都不必想,待我尋到時機便送你離開,會有人幫你。”
魏玠這番話最后說的似是而非,薛鸝沒有明白他的意思。
低頭瞥見魏玠的手背,又問了一次。“你這傷是怎麼一回事?”
魏玠垂下眼,無奈地笑了笑,說道:“我怕你聽了心中厭惡,還是莫要知曉的好。”
薛鸝更覺疑,追問道:“你不說我又怎會知曉,何況你了傷,我厭惡做什麼?”
見堅持要問,魏玠也不再掩飾,說道:“當日你我被關牢獄,你病中要飲水,獄中無人理會,我不忍心見你,才有了當日的無奈之舉。”
他說的委婉,薛鸝卻立刻明白了。何時嘗過人的滋味,想到自己飲了人定是惡心作嘔。然而見到魏玠未愈的傷疤,心中不酸,低著頭不知該說些什麼好。
“何必如此待我?”薛鸝眨了眨眼,眼前的火變得模糊了起來。“你喜我,待我好,本是得不償失,不值得……”
“值得。”魏玠打斷了的話。他明知薛鸝謊話連篇,冷漠勢利,卻還是無法了。
薛鸝心上一,低笑一聲,說道:“那你也要有法子與趙統抗衡才是,否則只能與我死后同葬了。”
魏玠毫不猶豫道:“你不會有事。”
北上的一路上,軍中的夷狄士兵與其他士兵不合,時常有打架爭斗,而寒門出的將領又被士族所輕視,彼此間不合也是常有。趙郢年紀尚輕,又是出宗室,不知該如何理好這些,往往需要讓老將與手下的謀士去替他擺平。然而做這種事吃力不討好,沒有幾人愿意接手。
Advertisement
魏玠當初寫過一篇討伐鈞山王的檄文,可謂是振聾發聵,警世懲惡的傳世名篇,幾乎是天下皆知。趙郢對此耿耿于懷,于是便將此事都推到了魏玠上。
夷狄殺了不齊國的百姓,軍中有人不滿也是平常。庶民起義是為了溫飽,也是為了建功立業,好跳寒庶之別的打。
魏玠潛移默化中,收攬了幾個寒門將領為自己所用,在軍中頗有聲。
不算太久,他們便北上與鈞山王會和。齊軍元氣大傷,名門族能站出來的名將非死即傷,剩下不多的大半是空有家世的無能紈绔。士族把控朝堂太久,寒素清□□如泥,高第良將怯如,一朝一夕已經無法更改。
若是此戰大捷,鈞山王的兵馬秋末便可直奔著去。
薛鸝再一次見到趙統,仍是忍不住心上發虛。趙郢拉著下了馬車,將帶到趙統前,還極為歡喜道:“父王,你看我將誰帶回來了。”
強裝鎮定,恭敬道:“義父。”
趙統打量了一番,嗓音低沉地應了一聲,而后點點頭,說道:“這段時日你苦了,子可還好?”
“一切都好,勞義父費心了。”溫聲道。
猜你喜歡
-
完結869 章
重生之妖嬈毒後
這個是一個被渣男和渣女算計之後,奮起反擊,報復過後,卻意外重生,活出錦繡人生,收穫真愛的故事。蕭家嫡女,風華絕代,妖嬈嫵媚,癡戀太子。二人郎才女貌,乃是天作之合。十年夫妻,蕭紫語殫精極慮,傾盡蕭家一切,輔佐夫君,清除了一切障礙,終於登上了皇位。卻不料十年夫妻,十年恩愛,只是一場笑話。只是寧負天下人
407萬字8 84134 -
完結141 章

替嫁以后
瑩月出嫁了。 哦,錯了,是替嫁。 圍繞著她的替嫁,心計與心機開始輪番登場, 作為一群聰明人里唯一的一只小白兔, 瑩月安坐在宅斗界的底層,略捉急。
43.2萬字8.09 33001 -
完結816 章

回眸醫笑,朕的皇后惹不起
原本是現代一名好好的外科醫生,怎料穿到了一本古言書中,還好死不死的成了女主!哼哼,我可不是書里那個有受虐傾向的無能傻白甜,既然成了主角,那就掀他個天翻地覆吧!只是……這個帝王貌似對我有些別樣的“寵”啊!…
146.8萬字8 9032 -
完結17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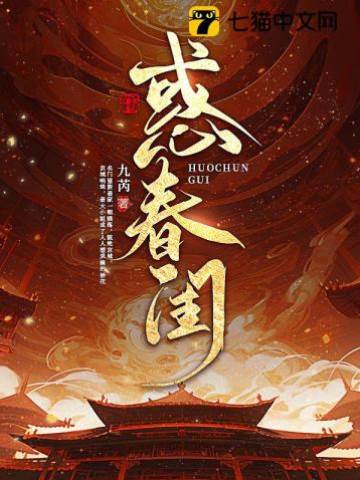
惑春閨
名門望族薑家一朝隕落,貌絕京城,京城明珠,薑大小姐成了人人想采摘的嬌花。麵對四麵楚歌,豺狼虎豹,薑梨滿果斷爬上了昔日未婚夫的馬車。退親的時候沒有想過,他會成為主宰的上位者,她卻淪為了掌中雀。以為他冷心無情是天生,直到看到他可以無條件對別人溫柔寵溺,薑梨滿才明白,他有溫情,隻是不再給她。既然再回去,那何必強求?薑梨滿心灰意冷打算離開,樓棄卻慌了……
31.5萬字8.18 8576 -
完結256 章

誘妻為寵/溺寵為妻
蘇語凝成親那日,鑼鼓喧天。 謝予安目送着大紅花轎擡着她進了大哥的院子,他竭力忽視着心口的窒悶,一遍遍地告訴自己——解脫了。 那個連他名字都叫不清楚的傻子,以後再也不會糾纏於他了。 直到有一日,他看到小傻子依偎在他大哥懷裏,羞赧細語道:“喜歡夫君。” 謝予安徹底繃斷了理智,她怎麼會懂什麼叫喜歡!她只是個傻子! 他終於後悔了,懷着卑劣、萬劫不復的心思,小心翼翼幾近哀求地喚她,妄想她能再如從前一般對他。 然而,從前那個時時追着他身後的小傻子,卻再也不肯施捨他一眼。 **** 人人都道蘇語凝是癡兒,可在謝蘊清眼中,她只是純稚的如同一張白紙。 而這張紙上該有什麼,皆由他說了算。 謝蘊清:“乖,叫夫君。” 蘇語凝懵懂的看着他,甜甜開口:“夫君。”
40.4萬字8.18 44669 -
連載2247 章

乖,叫皇叔
【重生】【高度甜寵】【男強女強】【雙向暗戀】重生后的虞清歡覺得,埋頭苦干不如抱人大腿,第一次見到長孫燾,她就擲地有聲地宣誓:“我要做你心尖尖上的人。” 大秦最有權勢的王不屑:“做本王的女人,要配得上本王才行。” 結果,虞清歡還沒勾勾小指頭,某人就把她寵成京城里最囂張的王妃,連皇后都要忌憚三分。 虞清歡:夫君,虞家的人欺負我。 長孫燾:虞相,我們談談。 虞清歡:夫君,皇后娘娘兇我。 長孫燾:皇嫂,你放肆了。 虞清歡:夫君,有人覬覦你的美色。 長孫燾:小歡歡乖,讓本王進屋給你跪釘子。
358.4萬字8 580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