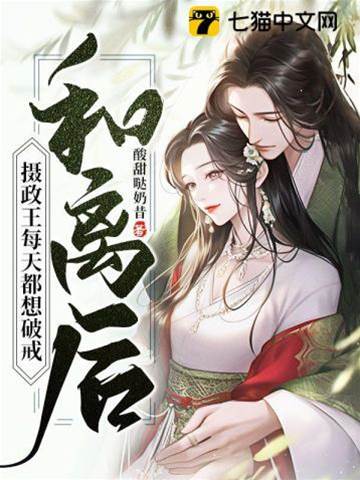《懷嬌》 第32章 第32章
薛鸝回到桃綺院的時候還早,往日里這個時辰,姚靈慧應當還未起。只是不想這次,一進院門便看見了姚靈慧在院子里來回踱步,上披著一件外衫,手里還拿著柄團扇,面沉到能滴出水來。
聽到薛鸝回來的靜,立刻抬起頭來,面帶慍地朝走來,直接拿著團扇打在薛鸝頭頂,低聲斥責道:“你個沒規矩的!昨夜究竟跑哪兒去廝混了,休要與我裝模作樣,還以為我不知道你的品不?倒是好手段,魏蘊也甘愿護著你……”
姚靈慧雖然被薛鸝氣得不輕,指責中卻也帶了幾分關切。“我同你說過多次了,此可不是吳郡,權貴都不是好欺瞞的,你若得罪他們了,沒人能護著你。魏氏長房的人并非善類,你往后離他們遠些,越遠越好,休要自以為是,仗著自己有幾分貌和手段,便忘了自己的斤兩。”
薛鸝到底是年紀小,年時總人欺負,習慣了如何討人歡心換取自己想要的東西,卻從未有人教過該如何做,只有到教訓才知道進退取舍。如今眼看著連魏玠都能為的下臣,難免會生出點驕傲自滿來。今早所見所聞,加上姚靈慧突然說出這樣一番話,像是給潑了一頭冷水,讓囂張的氣焰熄滅了不,也漸漸地冷靜了下來。
“阿娘是否知道些什麼?”
姚靈慧對與魏玠往來的事表現得格外不滿,即便是當真覺得與魏玠有云泥之別,也不至于要如此辱責罵才是。
姚靈慧瞪了薛鸝一眼,拉著快步朝屋里走去,而后將門仔細關上,著坐到榻邊,低聲詢問:“我問你,昨夜你究竟宿在何?”
Advertisement
薛鸝知道已經猜到了,索不再瞞。“在玉衡居。”
得到答案,姚靈慧深吸一口氣,強下怒火又問:“你們可有逾矩……”
“阿娘且放心,兒還不至于如此蠢笨。”只是哄男子歡心,說上幾句好聽話便是,讓他了子可就不值當了。
姚靈慧松了一口氣,而后悶悶道:“我當真是管不住你了,與你說了這麼些話,你竟死不改,還要與魏恒的兒子糾纏。魏氏長房規矩重重,禮法太過森嚴,且不說你與魏玠云泥之別,便說日后以你的子,要如何在此立足,魏氏大夫人,不過是聽著風,你以為是什麼好事不。”
見阿娘沒有說下去的意思,薛鸝回答道:“有所得必有所失,想要榮華富貴,循規蹈矩些也沒什麼。”
姚靈慧聽到的話,眼神像是冒著火,咬牙切齒道:“我看你是睡昏了頭,魏恒在王氏繁盛之時與大夫人結了姻親。不過三年的景,王氏卷宗室爭斗,魏恒立刻與王氏撇清干系,任由王氏沒落,沒有毫幫襯的意思。現如今呢,你來魏氏這般久,可還有見過什麼大夫人。什麼禮法規矩,倒是半點沒誤了男子的薄寡義,與你那混賬父親又有何異?何況……”
說到此,又猛地沒了下文。
“何況什麼?”薛鸝追問。
姚靈慧抿了抿,終究是沒忍住說道:“你且給我記清楚了,他們魏氏長房明面上高潔正派,背地里的齟齬不比薛氏,你若不想攪進這趟渾水,日后便離魏玠越遠越好,否則日后莫怪我當娘的不曾勸過你。”
姚靈慧顯然知道些其中,卻不愿意說出口,薛鸝見此也不好繼續問下去。倘若是從前姚靈慧說了這話,只怕會在心中懷疑是否又是捕風捉影,用不知從何聽來的謠傳告誡。然而今早窺見的那一幕,卻讓不得不信了。
Advertisement
如今梁晏已經知曉了魏玠對的意,便不必要再繼續費力討好魏玠,是時候該慢慢,將心思放在梁晏上了。魏氏長房如何,與實在沒有多干系。
滿不在乎道:“阿娘的話我記在心里了,兒不會對魏玠再有意。”
翌日清早,梁晏醒來后呆呆地著帳頂,夢里的畫面已經變得模糊不清,只是子的笑依舊清晰,他想忘都忘不掉。
好端端的,他竟夢到了薛鸝。
還是昨天那羅,低下頭,小心翼翼地避開腳下荊棘,憂心地問他:“山里會不會有蛇?”
問完后便扭到了腳,險些摔倒在地,好在被他手扶住了。
薛鸝迅速地推開了他,紅著臉往后退了一步,赧到不敢與他說話。
梁晏心中并無多,只是覺著薛鸝這般文雅怯弱,如何會鼓起勇氣接近魏玠這樣目空一切的人,豈不是時常到冷落。不知怎得,他想到了魏玠上的傷口,腦子里便不浮現了魏玠與薛鸝親吻的模樣,臉上迅速地開始發燙,心中更是說不出的古怪。
這個想法一旦冒出來便久久揮散不去,一直到與薛鸝分別后,他仍是會忍不住去想這個畫面,以至于夜里的夢也七八糟。
他本意是想安薛鸝,卻不想經此一夜,心中竟莫名有了幾分心虛。
魏翎與魏弛鬧出了這樣大的事,魏府上下卻沒有毫靜,好似在玉衡居的那場鬧劇,不過是一粒石子落深潭,只驚起了一片微弱的波瀾,很快便沉寂了下去,連一痕跡也不曾留下。
薛鸝仍記得清楚,魏恒的暴怒并非是從進門便開始的,而是在聽到魏翎的胡言語后,才忽然暴戾地打斷了。連一個外人都忍不住為此好奇,魏玠為被指著鼻子罵的那個人,卻表現得這般淡然,實在是古怪至極。
Advertisement
魏玠仍在足中,姚靈慧也對薛鸝看得更了,正好這幾日也不想去見魏玠,便留在府中好好看書。只是往日里魏縉總是尋了機會便來找,這兩日卻罕見地沒有來過。
薛鸝見窗臺的瓷瓶中逐漸泛黃的的梔子,才忽地想到了魏縉,搖著扇的手也漸漸慢了下來。魏蘊問道:“你在想什麼?”
“這幾日似乎不曾見過魏縉。”
魏蘊愣了一下,說道:“你不說我都要忘了,三日前魏縉被送回了廣陵,聽聞是堂兄的意思,廣陵有一位大儒與堂兄結識,似是有意教養魏縉,堂兄將此事轉告給了魏縉的父親,他們便急著將魏縉帶了回去。”
“帶回去了?”薛鸝有些驚訝,魏縉走的這般匆忙,連來見一面也來不及,多半是魏玠刻意為之,不想讓與魏縉有什麼干系。
薛鸝的心忽地一沉,緩緩生出一不耐來。倘若到最后也不能讓梁晏甘心為退了與周氏的婚約,魏縉便是給自己留的另一條后路。從前以為魏玠只是品正直,為人疏離不與人往來,如今卻覺得他未免太過冷冷,將魏縉送走的事上也實在算不得寬厚。
魏蘊睨了薛鸝一眼,心底也有種不清不楚的煩躁。
“莫怪我不曾告訴過你,以堂兄的份,便是你與他兩相悅,叔父與族中幾位長輩也必不會允許你們有什麼結果。”并不厭惡薛鸝,甚至有些喜的俏,喜笑盈盈的喚姐姐。然而一想到一心想著魏玠,便令心中生出些說不出的惱火。
薛鸝若無其事地笑笑,說道:“能好上一日便算一日,往后的事誰又說的準呢?”
魏蘊不想理會這番話,又聽問:“我還想同姐姐打聽一個人。”
Advertisement
不耐道:“什麼人?”
“前幾日我在府中見到了一位扮人模樣的郎君,看著實在是怪異,聽他話里的意思是要去找表哥,姐姐可知曉他是何人?”
魏蘊聽到薛鸝的描述,也不知想起了什麼,面上浮現出一的嫌棄。
“你可有得罪他?”
薛鸝想了想,搖頭道:“應當不曾。”
“他是宮里的皇上,瘋癲不似常人,旁的便也算了,只是他的那位皇后夏侯婧,實在是暴戾殘酷,殺了不知多妃嬪,招攬面首做盡惡事。前兩月王氏的一個庶,不過在宮宴上被皇上撞見,說了幾句話。此事被知曉了,竟將那王氏以醉骨的極刑。你若與皇上多說幾句話,傳到夏侯婧耳中必定會惹出禍事。”魏蘊說著便面厭惡。“夏侯婧也算名門出,自習得圣賢書,一朝得勢便狠毒至此,當真不給自己留半點后路。”
齊國上下都知曉夏侯氏野心,妄圖拉攏幾大族,除去宗室幾位封王后獨攬大權。以他們這半點不留后路的殘暴作風,一旦夏侯氏敗了,自有千萬人等著將他們食寢皮。
魏蘊的表上既是對夏侯氏的憎惡,也有對齊國朝政的無奈,這樣的神,薛鸝前不久在梁晏的臉上看到過。
再次來到玉衡居,梁晏的心卻大不如從前。一見到魏玠,腦子里便冒出與薛鸝有關的事。
他對薛鸝并未有任何逾矩的舉,卻遲遲不愿將他與薛鸝出行的事說與魏玠聽。甚至地希薛鸝也將此事藏在心中,當做他們二人之間的保守。
那一夜流螢飛散如星火,涼風習習吹得梁晏衫飄。他站在小丘上,笑道:“鸝娘日后倘若傷心難過,不妨來此看看。”
“世子若是心煩也會來此嗎?”
“流螢不算常有,心中的憂慮卻怎麼也消解不完。”梁晏的嗓音比起魏玠,要多了幾分年的稚氣。魏玠即便是笑著,也始終像是尊冷冰冰的石像,有著揮之不去的漠然。
“世子在憂心什麼?”薛鸝忍不住問他。
或許是風景太好,薛鸝的語氣也溫,他便下意識回答了的話。
“社稷已是危如累卵,可惜我并無韓王之才,卻妄圖如他一般建伊呂之業,弘不世之功。如今連三公曹都無法勝任,若換做蘭璋,定能功載國史。”梁晏說完后才覺得自己的話無異于是自取其辱,薛鸝如此喜魏玠,定會在心譏諷他的不自量力。他不別過臉,不去看臉上的表。
然而許久后,他才聽到薛鸝說:“世子正值年,何必妄自菲薄。”
薛鸝后是漫天飛舞的流螢,月映照在衫上,讓連發都蒙了一層清輝,襯得如同神一般。
“往后如何又有幾人說的準,世子但求無愧于心,是非敗不必過問。”
這種話梁晏聽得著實不,只是從魏玠的心上人口中說出,總歸是多了幾分不同的意味。
他嗓子莫名有些發堵,艱地開口道:“你不認為我與蘭璋相差甚遠嗎?”
“燭火有燭火的,流螢卻也有流螢的,彼此都無法比擬,至此刻,我認為流螢的更得我心。”
夜風吹得梁晏眼睛干,他眨了眨眼,良久后才說:“多謝。”
梁晏與父親爭執了許久,最終卻是因魏恒舉薦而得了三公曹的差事。此次來見魏玠,是魏恒要他來勸魏玠與薛鸝斷絕往來。
這件事梁晏開不了口,一直在玉衡居拖到了天黑,也沒能說出幾句薛鸝的不好來。
他坐在廊前納涼,碟子里盛著切好的甜瓜,蚊蟲叮咬得他無心去那瓜果,只幽幽地嘆氣。
春獵皇上遇刺一事尚未了結,本是將過錯推給了鈞山王,誰知最后還是讓秦王與河間王知曉了此事,二人憤慨至極,生怕日后會被一個莫須有的罪名給抄家滅族,一氣之下索聯合淮王起兵造反,以清君側為名想要誅殺夏侯氏滿門。魏玠因為頗有威,如今被要求去寫討伐叛軍的檄文。
梁晏想等他寫完了,再問一問他對薛鸝的心思,誰知一等竟等到了天黑。
他正在心中思慮著如何開口,不曾注意到后小心翼翼,輕得像只貓似的腳步聲。
猜你喜歡
-
完結620 章
秀色滿園
成爲地位卑下的掃地丫鬟,錦繡冷靜的接受了現實。她努力學習大宅門的生存技能,從衆多丫鬟中脫穎而出,一步步的升爲一等丫鬟。丫鬟間的明爭暗鬥,小姐們之間的勾心鬥角,少爺們的別有用意,老爺太太的處心積慮,錦繡左右逢源,努力活出自己想要的生活。到了適婚年齡,各種難題紛至沓來。錦繡面臨兩難抉擇……尊嚴和愛情,到底哪個更重要?---------------
157.9萬字8 43123 -
連載886 章

穿越女尊農門妻主不好當
她本是現代女神醫,一手金針起死人肉白骨,卻意外穿越到一個女尊王朝。一貧如洗的家,還有如仇人一般夫郎們,水玲瓏表麵笑嘻嘻,心裡。沒辦法,隻能賺錢養家,順便護夫郎。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82.4萬字8 21764 -
完結2595 章

神醫毒妃腹黑寶寶
穿越當晚,新婚洞房。 雲綰寧被墨曄那狗男人凌虐的死去活來,后被拋之後院,禁足整整四年! 本以為,這四年她過的很艱難。 肯定變成了個又老又丑的黃臉婆! 但看著她身子飽滿勾人、肌膚雪白、揮金如土,身邊還多了個跟他一模一樣的肉圓子……墨曄雙眼一熱,「你哪來的錢! 哪來的娃?」 肉圓子瞪他:「離我娘親遠一點」 當年之事徹查后,墨曄一臉真誠:「媳婦,我錯了! 兒子,爹爹錯了」
470.9萬字8.18 60927 -
完結199 章

癡傻王妃太難追
在丞相府這讓眼里,她就是那個最大污點,丞相府嫡女未婚生下的粱羽寧,從小受盡侮辱,終死在了丞相府,一朝穿越,心理醫生重生,她看盡丞相府的那點把戲,讓她們自相殘殺后笑著退場,大仇得到! 可在小小的丞相府能退場,在感情的漩渦越來越深之時,她能否安然離開? 一場大火,翩翩佳公子,變成了殘忍嗜血的戰神,接連死了八位王妃,當真是自殺,還是人為?
45萬字8 10423 -
完結567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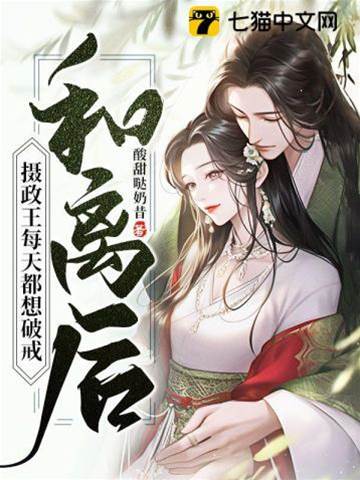
和離後攝政王每天都想破戒
葉芳一朝穿越,竟然穿成了一個醜得不能再醜的小可憐?無才,無貌,無權,無勢。新婚之夜,更是被夫君聯合郡主逼著喝下絕子藥,自降為妾?笑話,她葉芳菲是什麼都沒有,可是偏偏有錢,你能奈我如何?渣男貪圖她嫁妝,不肯和離,那她不介意讓渣男身敗名裂!郡主仗著身份欺辱她,高高在上,那她就把她拉下神壇!眾人恥笑她麵容醜陋,然而等她再次露麵的時候,眾人皆驚!開醫館,揚美名,葉芳菲活的風生水起,隻是再回頭的時候,身邊竟然不知道何時多了一個拉著她手非要娶她的攝政王。
99.6萬字8 948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