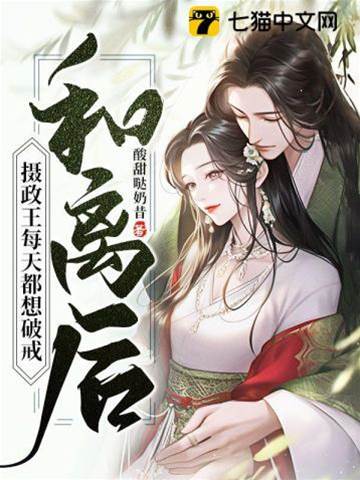《懷嬌》 第18章 第18章
鈞山王是最不想挑起事端的人之一,往日里也鮮與世家族往來。他雖子冷酷,對待親友卻極關,事關河間王與楚王命,又關乎齊國的安定,無論如何他都不會坐視不理。魏植不知如何開口,左右思慮后才托付魏玠一同去與鈞山王商議。
夏侯氏把持朝政,日后遲早要對幾位封王下手。鈞山王深知其中利害,只好暫且應下此事。將刺客的事推到他上,太后一時間不僅不會對他下手,反會找借口為他開。
等說服鈞山王后,酒宴已經快散了。前來拜見魏玠的人如同流水,還有各世家的王孫貴想要同他共飲,魏玠不能失了禮數,只得一一推,待人散后,天已經逐漸昏暗。花樹上掛滿了燈籠,滿樹芳菲映著暈,地上的花影隨風而。
梁晏還想纏著魏玠飲酒,卻被平遠侯從后拍了一掌,只好訕訕地放下酒盞。
“天已晚,蘭璋要回去歇息,你還攔他作甚?若你多學學蘭璋,為父也能些心,整日追逐華而不實之人,何日才能有所作為?”平遠侯自夫人過世,自己又重傷再不能征戰沙場后,便有了極大的變化,意氣風發縱馬過長街的年人,最后竟也了嚴肅冷漠的大家長,以至于連嚴厲著稱的魏恒都要比他和善幾分。
梁晏被幾句話訓得低下頭,再不敢吭聲,擺擺手和魏玠告別。
不等魏玠回到玉衡居,一個侍便從昏黑的小道中躥出來攔住了他的去路。
“你是薛娘子的侍。”晉青看了看,又回頭去看魏玠的表。
魏玠面不改,問:“你找我有何事?”
銀燈覺得此事說出來實在難為,無奈道:“還請大公子去看一眼我們娘子吧,……”
Advertisement
晉青一聽便皺起了眉,先魏玠一步說道:“天已晚,你們娘子又有何事,非要來尋我們大公子?”
魏玠輕飄飄地訓斥了他的無禮,卻沒有多責備的意思,顯然是同晉青一般的想法。
銀燈都想要退了,然而想到薛鸝那不肯罷休的樣子,只好說:“我們娘子喝醉了。”
魏玠溫聲道:“府中有醫師,你回去讓薛娘子好生歇息,再替煎一碗醒酒的湯藥。”
“大公子又不能醒酒,不讓你們娘子去歇著,尋我們大公子又有何用?”晉青見天已晚,說話時便有幾分急切。
銀燈也不知怎得,一見魏玠便渾發僵,腦子里一片混沌,半晌還未將話說清楚,如今見魏玠要走了,才忙不迭地說:“娘子喝醉了一直哭,非說大公子在藏書閣等著,奴婢怎麼勸都不管用,只得任由娘子去,可是……可是天晚了,娘子還是不肯出來,奴婢也進不去藏書閣,一來二去那侍者便不理會奴婢了。”
銀燈說著都要哭出來了,魏玠斂了斂眉,說道:“既如此,我會命人送薛娘子回去,無需擔憂。”
銀燈也聽說魏玠夜里歇息的早,必定是不肯為了薛鸝親自去一趟了,一時間也為薛鸝到失落,悶悶道:“我們娘子是個命苦的人,大公子若對娘子無意,不如早些說清,死了這條心,以免日后愈陷愈深,平白添了苦惱心事。”
一旁提燈的侍者聽了不滿,說道:“對大公子一廂愿的郎如此之多,難不都要去說明一番,薛娘子如此不知禮數,一再糾纏不清,日后豈能怨到旁人上?”
銀燈被說得啞口無言,心中也有了些委屈,苦著臉再不吭聲。
“不可背后議人長短。”魏玠出聲斥責,而后才看向銀燈,淡淡道:“既如此,我會如你所愿,與薛娘子說清。”
Advertisement
或許這侍說的并無不對。
薛鸝這樣的人,不該與他有一一毫的牽扯。世人皆污濁不堪,薛鸝尤其如此,他最不喜變數,更不愿因生出波瀾,與其再被擾,不如早些撇清干系。
藏書閣到了夜里更加昏黑,魏玠拾級而上,忽明忽暗的燭映照他的臉,晉照也在一旁提著燈為他照亮階梯。
藏書閣中安靜到只剩沉悶的腳步聲,一直到了第四層,有冷風從大開的窗口吹進來,將書頁吹得嘩嘩作響。
晉照看到了窗前的影,知趣地停住腳步不再上前。
那個所謂哭著要等魏玠來的人,如今已經趴在窗前的桌案上酣然睡。
今夜正是月中,月亮圓而亮,幽幽月進窗子,落了滿地白霜。薛鸝的玲瓏軀仿佛也罩了層朦朧白紗,連發都泛著瑩瑩的清輝。
魏玠緩步走近,坐在對面的位置,空氣中有淡淡的酒氣。
“薛娘子”,他出聲提醒,“該回去了。”
薛鸝沒有任何反應,他依舊沒有任何不耐。“薛鸝,夜已深,你該回去了。”
這一次桌案上的人終于有了作,迷迷蒙蒙地抬起頭,嗓音還帶著初醒的微啞。
“表哥……”
魏玠黑沉沉的眼如同一汪深潭,明凈的月也照不見底。
薛鸝睜大眼著他,面上的驚喜一閃而過,接著眨了眨眼,淚水便接連滾落。“你怎麼才來……”
見薛鸝哭了,魏玠還是一副從容不迫的模樣,溫和道:“為何而哭?”
噎道:“姚氏的人……還有阿娘,他們要我與人議親……”
魏玠對此有所聽聞,二夫人似乎也知道了些傳聞,今日托叔父旁敲側擊地同他說起了薛鸝,而后又提及了四房的魏縉,應當是有意為他們二人議親。
Advertisement
“魏縉一表人才,父親時常夸贊他聰慧守禮,若是你能與他議親,并不算什麼壞事。”要說起來,薛鸝若能與魏縉定下親事,也算是高攀。
魏玠語氣和緩,薛鸝聽了卻惱火不堪,而后哭得也更傷心,袖上滿是淚漬。“表哥當真不曾……不曾察覺鸝娘的心意嗎?”
薛鸝滿面淚痕,哭得肩膀都在輕,頭上的步搖也晃晃悠悠的撞在一起。
“薛娘子醉了,今日的事,我會當做不曾聽過。”魏玠態度疏離,平靜到讓心冷。
似乎察覺到薛鸝不肯罷休,他終于起,不愿與再有牽扯。“薛娘子還是早些回去的好,我命人送你。”
意識到魏玠是真的要與撇清干系,薛鸝松開掐著掌心的手指,猛地拽住他的袖。
魏玠回頭去看,發現正在去面上的眼淚,而后仰著頭看他。
昏暗之中,他不能將薛鸝的表看得一清二楚,卻聽得出的強歡笑。“能與表哥相識,已是鸝娘一生之幸,不敢奢求更多,我不難過……不該難過”
清輝落在月白上,暗紋如同搖曳的花影。與此同時,窗口的風吹得衫與帶都在舞,朦朧月輝灑落,有如流風回雪。
“表哥……我頭暈。”撐著桌案起,軀微傾,居高臨下地著魏玠。
黑發如墨,紅如,月照著薛鸝的影子也像在輕。好似一只攝人心魄的魅,潤的眼眸直直地盯著魏玠,被風吹起的發時而從他頰邊過。
魏玠察覺到不對,正想起,薛鸝卻猝不及防地晃了晃,子一歪朝地上摔過去。
他下意識手將人扶住,薛鸝卻如同一藤蔓攀附而上,微熱的手臂勾住他的脖頸,而后不等魏玠將推開,便似一只向他示好的,臉頰在微涼的頸側輕輕蹭了蹭,自言自語一般地低喃:“好熱……”
Advertisement
魏玠從未遇到過這種事,也無人敢如此輕浮地對待他,以至于一時間驚愕到渾僵,往日里的理智也在此刻被薛鸝攪得一團糟。
微熱的呼吸,像一羽輕輕掃過他頸間的皮。薛鸝略顯得意地悶笑一聲,溫的瓣在他的臉頰一即離,輕得像是落花拂過,好似一切都是酒醉后的無心之舉。
魏玠像是到了一塊熱炭,瞳孔驟然一,連扶著的手臂都微不可察地抖了一下。
不等魏玠發火,薛鸝裝作若無其事地,小聲地對他道謝,而后嘀咕道:“要回去了……阿娘還在等我。”
薛鸝踉踉蹌蹌地離開,幾次險些摔倒,魏玠沒有前去阻攔。
步的脆響與沉悶的腳步聲漸漸遠了,留在空氣里的幽香與酒氣似乎還揮散不去。魏玠僵站在原地無法彈,驚愕與惱蒸發了他的理智,幾乎他無法呼吸,方才被到的地方莫名發熱,如同被燙傷了一般。
許多古怪而陌生的緒如水般涌上心頭,他從未如此失態,像個傻子一般呆站在此,任由戲弄他的人逃之夭夭。
魏玠薄抿,始終難以平復雜的心緒,好一會兒了才沉著臉看向窗口進來的月。
薛鸝竟敢如此冒犯他。
猜你喜歡
-
完結620 章
秀色滿園
成爲地位卑下的掃地丫鬟,錦繡冷靜的接受了現實。她努力學習大宅門的生存技能,從衆多丫鬟中脫穎而出,一步步的升爲一等丫鬟。丫鬟間的明爭暗鬥,小姐們之間的勾心鬥角,少爺們的別有用意,老爺太太的處心積慮,錦繡左右逢源,努力活出自己想要的生活。到了適婚年齡,各種難題紛至沓來。錦繡面臨兩難抉擇……尊嚴和愛情,到底哪個更重要?---------------
157.9萬字8 43123 -
連載886 章

穿越女尊農門妻主不好當
她本是現代女神醫,一手金針起死人肉白骨,卻意外穿越到一個女尊王朝。一貧如洗的家,還有如仇人一般夫郎們,水玲瓏表麵笑嘻嘻,心裡。沒辦法,隻能賺錢養家,順便護夫郎。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82.4萬字8 21764 -
完結2595 章

神醫毒妃腹黑寶寶
穿越當晚,新婚洞房。 雲綰寧被墨曄那狗男人凌虐的死去活來,后被拋之後院,禁足整整四年! 本以為,這四年她過的很艱難。 肯定變成了個又老又丑的黃臉婆! 但看著她身子飽滿勾人、肌膚雪白、揮金如土,身邊還多了個跟他一模一樣的肉圓子……墨曄雙眼一熱,「你哪來的錢! 哪來的娃?」 肉圓子瞪他:「離我娘親遠一點」 當年之事徹查后,墨曄一臉真誠:「媳婦,我錯了! 兒子,爹爹錯了」
470.9萬字8.18 60927 -
完結199 章

癡傻王妃太難追
在丞相府這讓眼里,她就是那個最大污點,丞相府嫡女未婚生下的粱羽寧,從小受盡侮辱,終死在了丞相府,一朝穿越,心理醫生重生,她看盡丞相府的那點把戲,讓她們自相殘殺后笑著退場,大仇得到! 可在小小的丞相府能退場,在感情的漩渦越來越深之時,她能否安然離開? 一場大火,翩翩佳公子,變成了殘忍嗜血的戰神,接連死了八位王妃,當真是自殺,還是人為?
45萬字8 10423 -
完結567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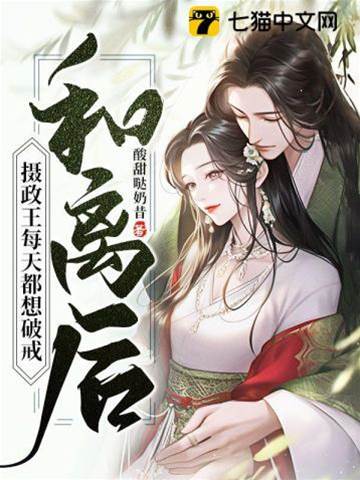
和離後攝政王每天都想破戒
葉芳一朝穿越,竟然穿成了一個醜得不能再醜的小可憐?無才,無貌,無權,無勢。新婚之夜,更是被夫君聯合郡主逼著喝下絕子藥,自降為妾?笑話,她葉芳菲是什麼都沒有,可是偏偏有錢,你能奈我如何?渣男貪圖她嫁妝,不肯和離,那她不介意讓渣男身敗名裂!郡主仗著身份欺辱她,高高在上,那她就把她拉下神壇!眾人恥笑她麵容醜陋,然而等她再次露麵的時候,眾人皆驚!開醫館,揚美名,葉芳菲活的風生水起,隻是再回頭的時候,身邊竟然不知道何時多了一個拉著她手非要娶她的攝政王。
99.6萬字8 948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