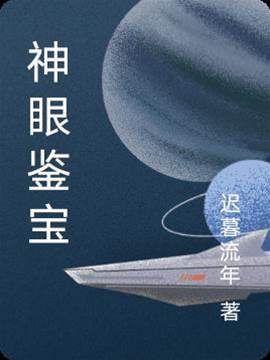《第一序列》 四十七、詭異樹林
任小粟沒理其他人,而是走過去查看徐夏的傷,他把徐夏捂住脖子的手拿開,赫然看到徐夏脖子上有一長長的螫針。任小粟一眼就認出來這是什麼東西……馬蜂!
他背對著后的人悄無聲息的把螫針給拔了下來,因為他不想讓其他人知道這徐夏到底是怎麼死的。隊伍里的氣氛越來越古怪,有時候讓這群人對荒野產生畏懼,反而更有利于他這個“向導”。任小粟從來不認為自己是個好人,他也沒義務把所有事都告知其他人,自己活下去才是最重要的。
不過任小粟倒是松了口氣,只要不是什麼神種襲擊人類就好,其實他剛才也嚇了一跳。
如今按照任小粟的推斷,可能是有馬蜂停留在了皮卡的車斗里,而徐夏爬車的靜驚到了馬蜂,于是馬蜂就給他來了這麼一下。
只是沒想到現在馬蜂蜇人竟然這麼致命,是脖子腫脹導致窒息嗎?不不不,不對,如果是窒息不至于十幾秒直接死亡,起碼還要等一段時間,看來是蜂毒的問題了。
曾經小時候任小粟也被馬蜂蟄過,但也只是半邊臉腫了幾天而已啊,并沒有死。
這荒野,越來越危險了啊。
有時候任小粟心里會有很矛盾的覺,他一方面被這神的荒野吸引著,想要知道這荒野的,而另一方面他有很清楚好奇心太重可能會死。
Advertisement
人都是多面的,思想也從來都是復雜的,這才是人啊。
死亡的影籠罩了整個車隊,而車隊里面現在最輕松的就是任小粟了,許顯楚來查看過傷口但是只能看到脖子上的一個紅點,任小粟觀察著所有人的反應,楊小槿也假裝無意間來觀察了一下徐夏的傷口,結果楊小槿也皺起眉頭。
只有任小粟知道,徐夏其實只是被荒野里進化過的馬蜂給蟄了一下而已……
“徐夏的尸怎麼辦?總不能把他棄尸荒野吧?”有人說道。
“那還能怎麼辦?”劉步愁眉不展,他是打算把徐夏直接扔到這里的,埋了還要花時間,這鬼地方他是一刻都不想多呆。
駱馨雨說道:“給他放到皮卡車斗里吧,先離開這里,到了合適的地方再把他給安葬了。”
作為樂隊的領頭人,要把徐夏拋在這里,其他人怎麼想?以后傳出去都是名聲上的污點了。
劉步對許顯楚說道:“要不咱們還是回去吧?”
“不行,”許顯楚搖搖頭,但他沒說為什麼。
劉步這時候心里很清楚自己是不可能左右私人部隊的,外人看起來他們好像是雇傭了私人部隊,但其實不是。
原本私人部隊就要來到境山執行任務,他們只是蹭車的,了保護費而已。而且私人部隊之所以愿意讓他們蹭車,似乎也是想掩蓋這次行程的目的,拿他們打掩護而已。
Advertisement
所以這一趟前往境山的行程,他們樂隊說了本不算。
劉步見沒法回頭便對任小粟說道:“你一個人坐皮卡車斗去,程東航你去車上,”他冷笑道:“既然你說沒帶錯路,那你就面對危險吧。”
這時候他也顧不上任小粟吃不吃餅干的事了,畢竟誰都不想死啊。而且相比被吃點餅干而言,生死明顯更重要。
任小粟倒是沒意見,一天多沒吃餅干,還想念的呢……
至于跟尸呆在一起他就更沒什麼心理力了,之前狼群襲擊工廠時留下那麼多尸他也沒害怕過。
壁壘里的人對生死有敬畏,但任小粟對生死只有敬,沒有畏。
車隊重新出發,任小粟坐在車斗里面一邊吃餅干、喝瓶裝水,一邊對著徐夏嘟囔道:“你說你們閑著沒事非要跑出來,得,命沒了吧?”
“哎你說你們壁壘里面到底什麼樣啊,我們外面的人很多都快死了,你們竟然還有心聽歌捧明星。”
“豬都給你們運進去了,我們也吃不到……”
任小粟跟“徐夏”有一搭沒一搭的聊著純粹是閑著沒事干,可皮卡駕駛座位和副駕駛的兩個哥們兒就不這麼想了,他們路上忽然約聽到任小粟說話的聲音,司機頭皮都麻了,他問副駕駛的兄弟說道:“他跟誰說話呢?!”
“我……我也不知道啊,可能自言自語呢吧……”
Advertisement
“你說他腦子到底有沒有病啊……”
當天晚上車隊沒能找到特別適合宿營的地方,只能勉強找個小小的空地,大家今天都沒什麼好心去聊天吹牛了,只剩下沉默。
第二天清晨任小粟起了個懶腰, 昨天晚上他倒是沒去找吃的,畢竟吃餅干都快吃到撐了。
原本巧克力也是放在車斗里的,結果劉步那老小子機警的把巧克力抱到了自己的車上,他們那輛車也沒地方放那一箱巧克力,劉步就這麼抱了一下午……
任小粟計劃的很好,早上也不用吃飯了,等車隊上路后他在車斗里想怎麼吃就怎麼吃。
結果就在此時他聽到一聲尖,他豁然轉頭去正是皮卡的方向,一名私人部隊的軍人大喊起來:“那個徐夏的尸呢?你們誰見他尸了?”
所有人頓時愣在當場:“不是在車上嗎?”
“尸不見了!”
這一次,任小粟頭皮都麻了!
什麼況,尸在車斗里面放的好好的,怎麼會不見了呢?
正常年男人的重在140斤到180斤,一個人想要扛著尸是非常費勁的,不可能一點靜都沒有。
在場這麼多人呢,怎麼可能一個聽到響聲的都沒有,是誰挪走了徐夏的尸?
這時候任小粟忽然想起自己之前丟掉的魚骨魚,似乎也是這麼消失的:沒有痕跡,完全無法判斷是什麼東西干的。
Advertisement
當時他猜測是螞蟻,可這次總不能是螞蟻了吧,這螞蟻再怎麼進化也不能一晚上搬走這麼大一個尸啊。
現在,任小粟心中也被一層影籠罩起來,他皺著眉頭思考,這到底是什麼東西干的?
劉步渾抖的看向許顯楚:“長,咱們還是回去吧,這也太詭異了。”
許顯楚端著槍朝外警戒著:“我跟你一樣害怕,但我說必須去境山,自然有我的理由!”
“可這樹林真的太古怪了啊!”劉步都快哭了。
“都給我上車,趕離開這鬼地方!”許顯楚怒吼道。
從這一刻起,任小粟手中始終都握著骨刀,他的大腦徹底活躍起來,時刻防備著任何危險的到來。
猜你喜歡
-
完結2278 章

透視仙醫
平凡小子偶得神鼎,不但可以煉製種種神丹仙藥,無病不治,還造就一雙火眼金睛,能透視,能治病,從此以後,賭石,淘寶,賭博,無往不利,財富唾手可得,桃運接踵而至。
446.2萬字8 144102 -
完結3259 章

都市全能高手
都市全能高手最新章節簡介:親愛的讀者朋友,請靜心閱讀我的小說,用鮮花和收藏支援我吧。
860.1萬字8 61485 -
完結929 章

無雙龍婿
葉玄天,玄寓意神秘、強大,天寓意至高無上的地位。多年以前遭人設計陷害,隱忍埋伏,替龍國清除叛徒,只為自己正名。功成身退的他,為了兌現爺爺的諾言,屈身小家族當上門女婿,換來了的卻是家族的謾罵,指責,隱藏身份他,該如何翻身逆襲?…
131.6萬字8 28582 -
完結4539 章

奶爸!把女兒疼上天
女兒,爸爸的心頭肉! 女兒,爸爸前世的小情人! 女兒,爸爸的貼心小棉襖! 身家萬億的全能奇才劉正陽,一睜眼發現自己居然穿越了! 望著外麵下大雨,裏麵下小雨的“新家”。 劉正陽表示自己腦殼有點痛。 不過當劉正陽看見“自己”那乖巧懂事的女兒之後。 劉正陽心都快化了,當即表示這輩子要...
496.8萬字8 63028 -
完結87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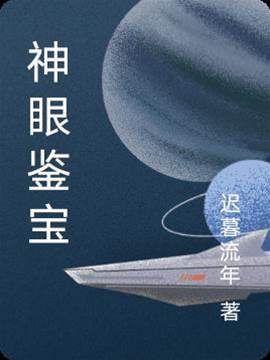
神眼鑒寶
簡介:秦昊因母親高額的醫藥費,同意以離婚為條件換二十萬醫藥費,結果不但沒要到錢,還被二世祖毒打一頓,意外之下激活祖傳玉佩,得到透視能力。
155.2萬字8.18 23272 -
完結1720 章

都市至尊神眼
平凡少年得到了一顆神奇的珠子,融合進入到左眼,左眼發生異變。 透視以及預知未來。 賭石鑒寶,建立商業帝國。 武功高強,拳打惡霸腳踢二代。 風流翩翩,引得一干美女盡折腰。
330.8萬字8 53515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