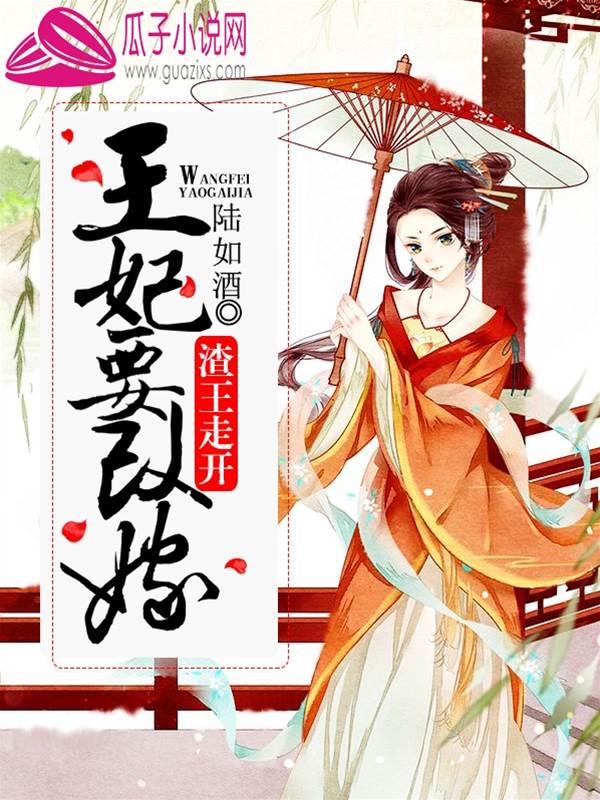《皇后嫵媚動人》 第三十七章
未央宮外的立侍已經抖了篩子,總覺皇後娘娘再這樣鬧下去,他們的腦袋遲早要搬家。
可誰又能管得了皇后?
方才未央宮眾人皆跪地懇求皇後娘娘,但娘娘不知哪裡來的怒意,還說誰敢撤走的牌子,就把誰扔去鱷魚池。
娘娘曾經寬容大度,那眼下的娘娘……一時一個主意,若非娘娘子骨,指不定都上樑揭瓦了。
眾宮人齊齊跪地,有膽小的已經汗流浹背。
李德海的結滾了滾,小心翼翼瞥了一眼側的帝王,見帝王側臉沉,晚風拂起帝王錦袍一角,顯得莫名蕭索。
李德海當初也是跟著蕭昱謹一道去西南鎮國公府,他自是知道蕭昱謹對皇後娘娘是如何看重。
帝王起初份卑微,境艱難,他不亞於是臥薪嘗膽,年時期臉上從未有過笑意,可每回穆溫煙去找他,年總能放下邊一切事,可他終究背負太多,即便見到小糰子甚是開心,他也不會笑出來,多數時候只是默默的看著。
穆溫煙時話多,活潑好。
他就聽著說話,看著調皮。
但也只是聽著、看著。
時的穆溫煙和年的帝王是兩個極端,一個冷,一個熱。
李德海比誰都清楚,帝王親自去西南迎娶穆溫煙,究竟花費了多力氣,單是朝臣反對,以及蘇家的阻力,就讓帝王費了不心神。
可娶回來后,帝王只是供著,甚至每回看見了皇后,還有些畏手畏腳,當然了,帝王表面仍舊是冷無溫,旁人看不出什麼端倪。
自娘娘失了心智后,帝王常年無溫的臉倒是有了些許暖。
帝王不.重.,可這重.的病一直都在。
「皇上息怒,娘娘許是跟您鬧著玩呢。」李德海詞窮了,總不能說娘娘是在練字吧?
Advertisement
蕭昱謹掌中還攥著那隻藍花細頸小瓷瓶,戴著扳指的拇指,有一下沒一下的挲著,發出瓷撞的聲響。
李德海提及了重點,「皇上是不是還得給娘娘……上藥?」
帝王一個眼神掃了過來,李德海當即閉了。
在眾立侍巍巍的凝視下,帝王終於拂袖轉而去,未央宮外隨即癱了一大片。
李德海抬步一路小跑才能跟上,可突然之間帝王止了步,幸好李德海及時剎住了,「皇、皇上?」
蕭昱謹將手中瓷瓶給了李德海。
李德海立刻會意,「奴才這就去辦!」轉之前,他又加了一句,「娘娘會明白皇上一片良苦用心的。」
蕭昱謹不聽這話還好,聞言不由得膛起伏,幾時能明白他了?
「多事!」
丟下一句,蕭昱謹回頭看了一眼未央宮的方向,不知是什麼事又惹怒了他,帝王的俊臉沉的可怖,直接轉離開。
***
穆溫煙蔫了。
人已昏昏沉沉的趴在秋香碩大迎枕上,實在困的厲害,可下還是一陣陣痛,但又難以言表究竟是怎麼個痛法。
張嬤嬤端著李德海所送的瓷瓶過來時,因為過於激,手有些輕。
再見穆溫煙此刻狀況,便不難猜出帝后二人之間已經發生了什麼。
莊嬤嬤對此事尤為在意。
穆溫煙是否得寵,不僅關乎著鎮國公府的安危,同時也關乎著的一輩子。
穆溫煙兩年前嫁皇宮時,莊嬤嬤就知道穆溫煙這輩子都與這座皇城息息相關,只怕是一輩子也不了了。
若是帝王能真心待,那是最好不過。
莊嬤嬤沒急著給穆溫煙藥,試探的問道:「娘娘,皇上他……對你做過什麼了?」
穆溫煙沒甚力氣,的靈魂在暴走,可子宛若被幹了所有力氣,眼皮子都懶得提起來,喃喃道:「他欺負我,嚶……」
Advertisement
真的欺負了麼?
問題是,這回欺負的徹不徹底呀?
莊嬤嬤一生未嫁,男之間的事,也無法張就問。
穆溫煙十六了。
在大楚,子這個歲數婚生育子嗣之人不在數。
若是能一舉誕下皇太子,鎮國公府的形勢立刻就能迴轉。
莊嬤嬤恨不能從穆溫煙肚子里掏一個孩子出來,帝王二十好幾了,至今膝下無子嗣,甭管娘娘生下皇太子,亦或是大公主,都將是意義特殊。
又問,「皇上他怎麼欺負娘娘了?」
這是一個傷心的話題,穆溫煙不想提及,思及此事頓時泫然泣,淚水盈滿眼眶,「翻來又覆去的不停欺負!嚶嚶嚶……」
莊嬤嬤,「……」可能經歷有限,不太明白怎麼個翻來覆去法,但基本已經能夠確定了一樁事,那就是帝后二人極有可能已經圓房了。
「娘娘,老奴伺候您是上藥。」莊嬤嬤道。
穆溫煙趴著未,確切的說半點彈不得,「不了嬤嬤,且讓我自生自滅吧,反正在宮裡也沒甚麼盼頭了。」
莊嬤嬤,「……」
***
宮裡又掀起了一陣流言蜚語,皇後娘娘又病了,比上回病的更重,據說徹徹底底下不了榻,整日昏睡不醒,滴水不進。
除此之外,未央宮外面也發生了一樁事,原本種了花卉的草圃,一夜之間被人填上了青石磚,別說是昨晚..進.去的木牌,就連一棵花木也未能倖免。
國公夫人與穆世子宮探病。
昏睡了一夜,穆溫煙並未好轉,相反的,神獃滯,一慣機靈水汪汪的大眼也沒了氣神,小臉蒼白如紙。
莊嬤嬤稍稍代了幾句,國公夫人便大約明了了,「哎,這世上男子皆一樣,可皇上也太不知節制了,哪能把人折騰這樣?!」
Advertisement
話音剛落,玳瑁瞥見了一抹帝王龍袍角,蕭昱謹不知幾時已經站在殿,嚇的立刻跪地,「皇上!」
莊嬤嬤深深的看了國公夫人一眼,自己則悄然退開稍許。
飯能吃,話不能說。
尤其是在未央宮。
因為你永遠也不會知道,帝王究竟什麼時候會悄然無聲的出現。
國公夫人臨危不,起行了禮,「給皇上請安。」
當年蕭昱謹去西南歷練時,國公夫人已嫁鎮國公府了,故此,他二人早年就認識。
穆溫煙揪著被褥,把自己藏了起來。
國公夫人看著帝王沉的臉,神訕了訕,「皇后打小驕縱,這事皇上比誰都清楚,這不,昨個兒晚上吃了些苦頭,還在鬧著小脾氣呢。」
蕭昱謹,「……」
帝王用他的冷茍住了局面,似乎無論發生了什麼,他始終如一的清冷無溫,就像是幾年前,那時候穆溫煙已經長了亭亭玉立的,開朗,足智多謀,但無論做什麼,亦或是說什麼,蕭昱謹始終是那副漠然。
「夫人可否先迴避?」帝王言簡意賅。
國公夫人常年跟一對傻父子相,還不曾與蕭昱謹這樣的男子「過手」,搵了搵臉上並不存在的淚,惋惜道:「皇后自聰慧,也不知怎的就這樣了,皇上多擔待些,皇后才十六,子骨經不住折騰。」
說著,國公夫人坦坦的離開了殿。
李德海是個很有自知之明的,也隨即退下,他多瞄了一眼國公夫人,他也算是見多識廣,可不知為何,總覺得國公夫人深藏不。
殿再無旁人,穆溫煙聽不見任何靜,被薄衾悶的難,稍稍探出來一些,卻是正好撞見了帝王的凝視。
穆溫煙嚨乾,大約是昨天哭的太狠了,啞聲問,「你來作甚麼?」
Advertisement
蕭昱謹踏足未央宮的一刻起,就知道他自己輸了。
又輸給了這個心智不全的小混蛋。
帝王輕嘆了一聲。
他跟一個孩子計較什麼?
「起來。」他們那樣之後,他還沒跟好好說說話。
穆溫煙哪裡肯?
一想到昨日,無論如何求他,又如何的痛哭裝可憐,蕭昱謹就像是發了瘋一樣,仍舊不管不顧的起伏,現在是想想,就覺得自己委屈的不行。
立刻又哽咽了,啞著嗓子說,「皇、皇上,你難道就不能給我一條活路麼?我給你當了兩年皇后,沒有功勞也有苦勞,我家中還有年事已高的爹爹,和尚未婚的兄長,我……」
「夠了!」帝王了眉心,不曉得又是從哪裡看來這些措辭。
穆溫煙的確頓時停住了,但出薄衾外面的眼睛,卻是怎麼也抑制不住眼淚,「昨晚不是說好了再也不兇我了麼?嚶嚶嚶……」
蕭昱謹噎住。
他一慣不懂如何與相,可這些對那個人而言卻是輕而易舉。
帝王的段高大頎長,他此刻就杵在那裡,又氣又束手無措。
可仍舊是那張冷漠無溫的臉,兩人對視著,誰也沒有讓誰,最終帝王無奈,先啟齒,「突厥使臣月底來朝,你最恨的人也要京,你就打算這樣見他們?」
提及突厥,穆溫煙眼裡的三千委屈頓時化為憤恨。
前一刻還是一隻飽欺.凌.辱.的可憐白兔,但這回已經是渾長滿刺的小刺蝟了。
眼神兇狠,嘗試著爬起來,卻又突然意識到自己還在「虛弱」狀態,以免蕭昱謹又逮著折騰,穆溫煙把自己偽裝小白兔,「嚶嚶嚶……突厥殺我西南將士無數,手上還沾染了我叔伯的,突厥人來了,本宮當然要站起來!」
「本宮」二字都喚出來了。
蕭昱謹看著矯造作之態,薄涼的微微一,帝王走上前把穆溫煙扶了起來,掌下的小板纖細弱,彷彿稍稍一用力,就能擰斷了似的。
再看傻皇后略顯蒼白,宛若被雨水打過的梔子,帝王眉心擰了凝。
昨晚他可能真的下手太重了。
穆溫煙機靈多怪,但不住帝王激將。
蕭昱謹不知與如何相,但他卻是最懂的那一個。
「把葯喝了。」
莊嬤嬤熬了保胎葯,純粹是以備不時之需。
蕭昱謹以為是給穆溫煙的滋補湯藥,以他對的了解,這妖縱使是病死也不會主喝葯。
穆溫煙泣,但眼中仍舊充斥著悲憤。
蕭昱謹知道矯,又說,「不喝葯如何能好?若皇后不康復,又如何給那幫突厥人下馬威?」
穆溫煙眨了眨眼,狗皇帝的話好有道理啊。
安胎藥苦沖鼻,穆溫煙才喝了幾口,就哭出來了,一度哽咽,「都怪突厥人!不是他們,我也不用喝葯!」
帝王端著瓷碗的手一僵。
很想糾正穆溫煙的措辭,這事皆由他而起,跟突厥人沒有關係。
「你還吃不吃飯了?」帝王問。
穆溫煙點頭,此刻甚是配合,這人敢敢恨,突厥與大楚常年戰,位於西南的鎮國公府首當其衝堅守邊陲,這些年也隕落過太多穆家兒。
蕭昱謹知道,穆溫煙打小的夙願,就是上陣殺敵,滅了突厥。
這也了他的夙願。
「我會好好吃飯!我要喝十全大補湯!皇上,那……你看,這一陣子我有要事要辦,皇上就莫要讓.侍.寢.了,跟皇上睡一覺,我會元氣大傷,嚶嚶嚶……」
穆溫煙著帕子,哭的楚楚可憐。
蕭昱謹怔住了,「……」
帝王自我寬,全當穆溫煙是在褒讚他,男人眸暗了暗,有種危險的緒在漫延,但頃皆被他掩飾,「好。」
穆溫煙努了努,眼神直直的看著蕭昱謹,然後又看了看桌案上的藍細頸小瓷瓶,沖著蕭昱謹眨了眨眼,「皇上,你做的事你要負責的,你得幫我……」
蕭昱謹,「……」
——
國公夫人與穆長風在外面吃茶,不多時,帝王踏出了殿,他二人起行禮,卻見帝王俊微紅,蕭的額頭溢出薄汗,一慣冷靜自持的帝王,眼神出現了一刻的遊離,但很快就恢復清明。
帝后的房中事,無論是誰都不便手。
穆長風就是個愣頭青,兩年前還差點在帝后的大婚上對帝王手,不過如今時過境遷,他已經不再是當年的那個穆世子了!他已經了……稍許。
猜你喜歡
-
完結149 章

小庶女
章云驪生于朱門繡戶,雖為庶女,但也是錦衣玉食的千金小姐,本想做個隨分從時的小姐。可這波瀾不驚的湖面下,卻蘊藏著無邊的風險,尤其是隨著隔房堂姐被選為王妃后,頓時洶涌的波濤溢出湖面。…
64.2萬字8 8612 -
完結263 章

一妃動華京
穆長縈沒有想到,“命中克夫”的自己在大婚前夜竟然把自己“克”死了!穆長縈也沒想到,自己再睜開眼睛的時候已經嫁人為妻!穆長縈更沒想到,自己重生后的夫君竟然是自己生前就要嫁卻死都不想嫁的奸臣煦王!穆長縈甚至沒想到,她這一死竟然動了某人的棋局!青梅竹馬是家中的養子。正牌夫君是朝中的奸佞權臣。推心置腹是從小一起長大的生死之交。還有對原主人死心塌地的東宮之主。可是她通通都不想理!她只想知道自己為什麼被指婚?又是怎麼死的?想知道原來這具身體的主人是怎麼死的?想知道為什麼即便重生也有人不放過她?想知道自己到...
103萬字8 8629 -
完結903 章

瘋了!廢后她冷宮養崽要造反
【本文雙潔1V1】+【養娃】+【團寵醫妃】穿越幾世后,寧宜臻重生在冷宮生崽之時。一醒來……“娘娘,是一對龍鳳胎!您總算有出頭之日了,老奴這就去告訴皇上!”出冷宮?寧宜臻頓時雙眸含冰:她全能大佬,一手醫術更能醫死人、肉白骨之人,出冷宮去侍侯那狗男人?——燕鳳煬,上輩子你欠我的,這輩子我自己來討!他以為,他愛的是自己心中的’小珍兒‘,絕對不是眼前這個奸相的外甥女。可是,有一天他發現自己瘋了!
154.7萬字8 254193 -
完結1480 章
將軍夫人嬌寵日常
前世,她驕橫跋扈,受人挑撥,作了一手好死。 一朝重生,她只有一個念頭。 那就是抓緊他,賴住他,死也不放手。 將軍大人看著像無尾熊一樣扒在他身上的她,眸底笑意盎然。 終於,她是他的了。
263萬字8 25319 -
完結501 章

神醫棄妃她每天都想踹翻狗王爺
新婚當夜,她被不愛自己的夫君親手虐死,他冷酷無情,不愿要她。再次醒來,她是21世紀風華絕代的天才神醫千若瑜,不再是那唯唯諾諾任人欺凌的王府棄妃。一朝風云驟起,群雄爭霸,她盛裝出席,一襲紅衣,傾國傾城,虐渣斗白蓮,大殺四方,且看她如何用醫術名揚四海,驚艷天下。只是當初那個虐她千百遍的夜王楚墨白天天不要臉的糾纏她。她眼中只剩下冷戾,“姓楚的,你當初要將我扔到亂葬崗,現在天天黏著我真的好嗎!”某個差點兒被踹翻的狗王爺眼眶猩紅,“王妃,本王錯了,你別跑,快到為夫碗里來!”
91.2萬字8 25340 -
連載52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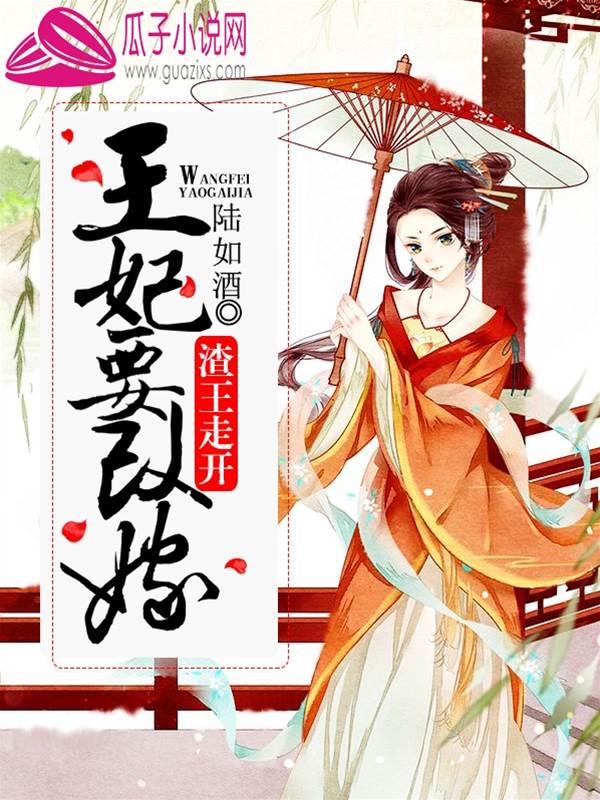
渣王走開:王妃要改嫁蘇妙妗季承翊
蘇妙,世界著名女總裁,好不容易擠出時間度個假,卻遭遇遊輪失事,一朝清醒成為了睿王府不受寵的傻王妃,頭破血流昏倒在地都沒有人管。世人皆知,相府嫡長女蘇妙妗,懦弱狹隘,除了一張臉,簡直是個毫無實處的廢物!蘇妙妗笑了:老娘天下最美!我有顏值我人性!“王妃,王爺今晚又宿在側妃那裏了!”“哦。”某人頭也不抬,清點著自己的小金庫。“王妃,您的庶妹聲稱懷了王爺的骨肉!”“知道了。”某人吹了吹新做的指甲,麵不改色。“王妃,王爺今晚宣您,已經往這邊過來啦!”“什麼!”某人大驚失色:“快,為我梳妝打扮,畫的越醜越好……”某王爺:……
99.7萬字8 1349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