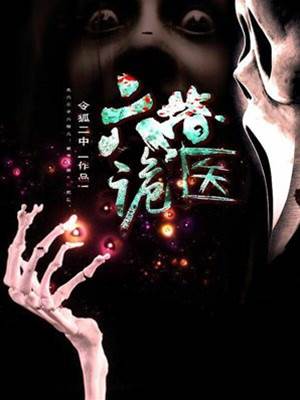《鬼吹燈》 湘西疑陵 第六章 虛塚假穴〔2〕
“這你就不懂了,要是想審咱們,就不會把咱們放在一起。[*爪丶機*書^屋*] wwW.ZhuaJi.oRg我看郭衛國心裡有鬼,不像單純的執行任務。”
“你有什麼證據?”
“覺。”我也不知道這種覺從何而來,總覺得事有哪裡不對勁,可又說不上來哪裡出了問題。
我們有一搭沒一搭地閑扯了半天,還是不見有人來問話。我心想難道是想試探咱們,等我們自己聊出點兒什麼。那這個郭衛國也太傻了點兒。
我繞著帳篷走了好幾圈,發現周圍十分荒涼,除了站崗的士兵之外連只鳥都沒有。我就提議說:“要不咱跑吧,先找到胖子再說。”
shirley楊果斷地否定了這一想法,“把咱們單獨丟在這裡肯定是有原因的,他們不我們也不,看誰沉得住氣。”
我一想也是,要審還不早就辣椒、皮鞭一起上了,幹嗎把咱們撂著乘涼。我掏出一副撲克牌說:“那就娛樂一下,反正咱不急。”
shirley楊不可思議地看著我:“你隨帶著撲克牌進墓室?”
我解釋說:“這是胖子的外套裡的,我也是無聊剛發現的。”shirley楊白了我一眼,我笑著打開盒子,一張折得整整齊齊的”豆腐幹”隨即掉了出來。我打開一看,抬頭寫著:“致親的革命戰友林芳同志……”
**,胖子的書!我沒想到居然有這樣意外的收獲,連忙招呼shirley楊過來看。
“老胡,你這樣做是不是不太道德?”shirley楊湊到我邊上,指著信說,“這是胖子的**,我們是他的朋友,應該尊重他。”
我痛心疾首道:“正因為我與胖子堅定的革命誼,才迫使我不得不高聲朗讀這封飽含與淚的告白書。我這樣做完全是為了能夠更加深徹地了解他,只有更加深地了解了他,我才能幫助他。試想一下,多個夜晚,他躺在床頭看著窗外皎潔的月,心中默念著’芳兒,芳兒’……”
Advertisement
“胡八一,你丫死去!”我還沒來得及抒發完,帳篷外面就傳來了胖子的咆哮聲,“你丫天詆毀老子,看我這次不打死你丫的為民除害。”
我還沒來得及反應過來,胖子就呼嘯著沖到我面前,迎面給了我一肘子。shirley楊忙勸架道:“他還沒看呢,你別急,別手。”
我見胖子一手打著綁帶,一手握著從我手中搶過去的書,紅著臉解釋說:“這不是書,不是書,是流用的,主要是想探討一下今後中關系的走向,是嚴肅認真的外信。”
shirley楊憋著笑點頭說:“你放心,我們都懂,你說什麼是什麼。”胖子扭頭瞪了我一眼,將我從地上拉了起來。我了被撞的口,問他怎麼逃出來的。他指著門口說:“我也不知道怎麼回事,是他帶我來的。”
我抬頭一看,原先守在帳篷門口的門衛已經不見了,章副隊長笑意盎然地走了進來,而跟在他後的正是面鐵青的郭衛國。
章副隊長嬉皮笑臉地向我們打招呼:“各位辛苦了。的況我都了解過了,小郭太沖,委屈各位了,哈哈哈哈!公事公辦,希大家不要放在心上。”
俗話說”無事獻殷勤——非即盜”,要說這麼點兒工夫他就把事的來龍去脈查清楚了,那就是打死我我都不信。這個章副隊長給我的印象一向是猥瑣的,屬於那種凡事不肯吃虧的主兒,現在他親自把胖子送回來,只能說明他必定有求於我們。我故意拿起架子不去接他的話,反問胖子的傷勢如何。胖子說:“還行,骨頭沒傷著,不過傷筋骨一百天,暫時不能有激烈的運。”章副隊長的手懸在半空中,見我沒有與他握手的意思,只好訕笑著將雙手放了下去,在上了一。shirley楊看不過去說我刁鑽,然後就問章副隊長:“況如何,王清正有沒有招供?”
Advertisement
章副隊長見有人肯搭理他,立刻來了神。他掀開帳篷上的簾子說:“帳篷裡空氣不流通,咱們上外邊說去。”
shirley楊二話不說跟著他走了出去,我想跟,可又覺得撂不下面子,結果被胖子一把揪了出去。他說:“面子這東西又不能吃,你要來幹嗎?咱跟上去不為聽他放屁,是為了保護單純的國際友人shirley楊,避免被狡猾的敵人迷。”我一聽他這番自我安法,立刻悻然,不得不承認有些方面胖子就是比我強得多。
我走出帳篷之後才發現外頭已經破曉了,太藏在灰蒙蒙的天空裡,偶爾出那麼一亮,別提有多。郭衛國從始至終沒有離開我們左右,我懶得跟他說話,徑直走到shirley楊面前,想聽聽章副隊長在說些什麼。
“……大況就是這樣,現在全仰仗諸位……”
“老胡你來得正好,副隊長剛才向我了一些營地裡的況,這一夜變化太大,我們低估王浦元了。”
“老王八逃了?”
“不,他把高地給拔了。”
“三十多號人,十幾桿槍,被他給拔了?”我扭頭看了一眼郭衛國,這小子太英雄了,居然被敵人奪了營,難怪見了我跟見了殺父仇人一個表,敢是大營沒守住在遷怒我們。郭衛國見我看他,索走上前來,痛斥道:“土匪!流氓!反分子!他們那是襲!”
我沒空安他的緒,急忙向章副隊長請教事的始末。
“太突然了,太突然了。”章副隊長強笑道,“昨晚隊長跟我講了去找人的事,說他不在的時候讓我注意安隊上人的緒,我就把大夥兒集中到了空地上,開了一場賽歌會。後來,有人提出郭班長他們為考古隊站崗太辛苦了,應該把他們也請過來參加文娛活。我覺得有道理,派了兩個隊員過去,磨泡了好半天才把郭班長請了過來。後半夜的時候,大家都乏了,準備回帳篷休息,就在這個時候,山裡邊突然響起了槍聲。一開始我還以為是山下的獵戶,可轉念一想,封山的公文早就發下去了,怎麼會有獵戶大半夜起來捕獵呢?小郭意識到況不對勁,立刻讓我們向崗哨的位置轉移。我們還沒來得及出空地,就被一大群持槍的迷彩服包圍了。他們武良、手矯捷,頭上都戴著面罩,帶頭的是個壯漢子……”
Advertisement
章副隊長說到後邊,聲音就開始嗚咽了,他停了一會兒,實在說不下去了,就對蹲在一邊悶煙的郭衛國說:“後邊太了,還是你來講吧。”
郭衛國蹲在山頭上,眼神銳利得像一匹孤狼,他將煙屁按在地上,悶聲道:“那人上來二話不說就斃了我一個兵,那小子是新進來的兵,我怕他想家才特意……他媽的這幫狗娘養的畜生。”郭衛國一拳砸在地上,“後來那夥人又說外邊的崗哨已經廢了,想活命就別其他心思。開頭我只當他虛張聲勢,誰知道他們隨即又丟了一袋東西給我,我打開一看全是肩章,這才知道這夥人說的不是玩笑話,他們是認真的。”
章副隊長歎了一口氣,拍了拍郭衛國的肩膀:“郭班長當時一共帶了八個人,佩槍的只有四個。都是氣方剛的小夥,我們隊上也有當兵出的老隊員,沒有一個肯屈服,上來就跟他們打了一團。我們幾個趁逃出了營地,當時我只想著先找到薑隊長,就帶著他們進了工地,跳下了盜。下去之後我急忙封住了口,哪曾想一回頭就遇上了薑隊長,這才知道你們在地底下也遭遇了武裝盜墓者。哎呀,當時郭班長就怒了,帶著僅有的幾個人殺了進去,再後來你們也知道。”
聽完章副隊長的一席話我才知道,原來昨夜我們進墓室之後發生了如此巨大的變故。”那薑隊長呢,他豈不是?”
“這裡是原先我們探測地形時候的小營,已經荒廢很久了。薑隊長的打擊太大,暫時不要打擾他了。我來找你們主要就是商量一下今後的計劃。我們派了兩個人下山求救,可半道上就折回來,說前些日的大暴雨已經把山路沖塌了,暫時沒法下去。封山的通知早就發到鎮上去了,想等別人主來找咱們恐怕不太可能。但我們隊上三十六條人命全都攥在那夥犯罪分子手裡……”
“王清正呢?他不是被你們抓回來了?有沒有問過他況?”
猜你喜歡
-
完結1303 章
渡靈師
在城區的一條深巷裡,有一家小小的毫不起眼的“蘇記香燭紙紮鋪”。店主是一名蒼白的青年,平日這位蘇老闆只是賣一些香燭紙紮,卻很少有人知曉他實際是一名渡靈師,一雙銀眸可以窺見天道,看透鬼神,而他的職責便是專門渡引那些徘徊於人間不肯離去的亡魂……
349.4萬字8 16910 -
完結350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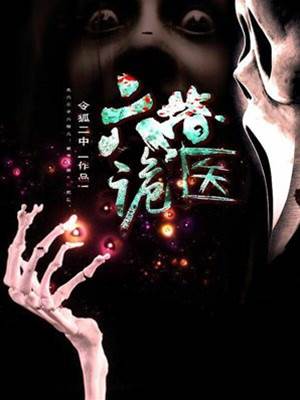
六指詭醫
先天左手六指兒,被親人稱為掃把星。出生時父親去世,從小到大身邊總有厄運出現,備受歧視和白眼。十八歲受第三個半紀劫時,至親的爺爺奶奶也死了,從此主人公走上了流浪之路。一邊繼續茍延殘喘自己的生活,一邊調查謎團背后的真相,在生與死的不斷糾纏中,我…
661.4萬字8 13770 -
完結668 章

靈車
(靈車:運載靈柩或骨灰盒的車輛,你也可以理解為死人專用車。) 我做了四年公交司機, 心中的秘密也整整壓抑了四年, 我來親身講述你所不知道的列車驚悚事件。 靈車改裝成公交車之事, 或許你沒經歷過, 但你所坐過的公交車,不一定只載活人...
151萬字8 698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