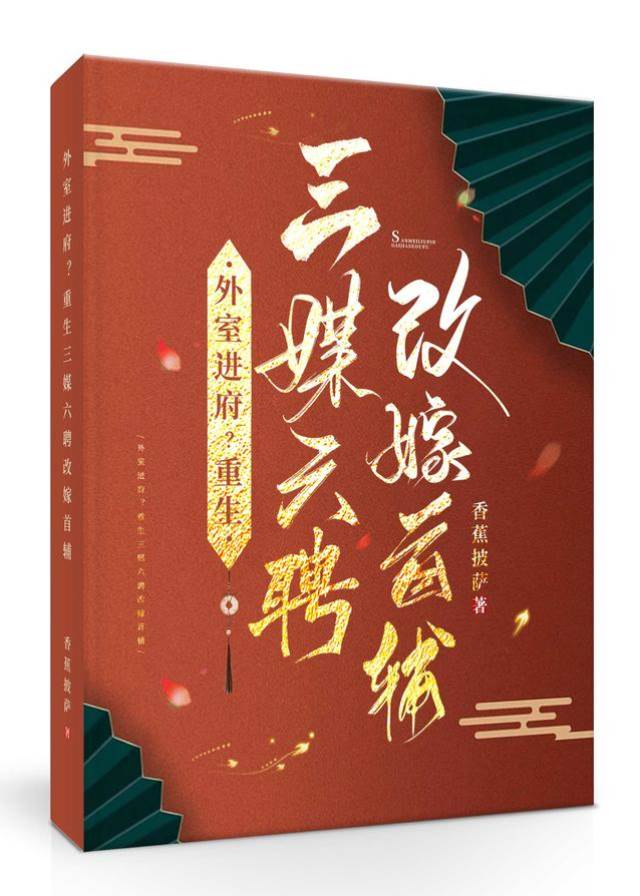《古代小戶女》 第33章 苦盡甘來
正苦思冥想間, 忽然一聲豬哼從塌了的柴房下傳出來。
里正心里正犯堵,抬腳就給了張有金一下:“你自個兒做的事我都沒臉說,你還好意思在這哼哼唧唧的作怪。”
張有金著腦袋沒吱聲兒, 只往草堆里鉆得更深了。
張知魚見他平日里又慫又惡,使三分力打他, 他能嚎出七分的氣勢,這會兒挨這一腳倒一聲不吭, 心里便覺得不對勁, 轉頭就讓爹把茅草房再掀起來。
眾人聽了都默默的沒出聲,只盯著張大郎手看,草棚雖然不比泥磚房重,那也不是隨隨便便一個人能抬起來的。
但張大郎抬起來了, 甚至只用了一只手連氣都沒一下。
張大伯見了不倒一口冷氣,出手指著草棚哆嗦半天沒吐出一個字, 這不是因為這個壯牛似的二房侄兒。
而是一只小豬崽兒正巍巍地打草堆里往外走吶。
且長得跟他家的小豬渾似雙胎。
三房如今是個什麼樣兒大伙兒有目共睹, 若非羅氏子骨還爭氣,母子兩個都不需別人出手,自個兒就死了,哪來的錢買小豬?都不用細想就知是張有金不知打哪兒來的。
這會子看著還不滿一月的樣兒,可見他早早就踩了點兒,專等著人一下崽兒就走。
大桃氣得直接往他上踩了兩腳:“好啊,我就說家里明明九只豬怎麼不見了,我娘還罵我不識數, 讓我打了一旬豬草,原來是被你這壞東西走了。”
張大伯還記得這事兒, 母豬生崽的時候他們都還在地里, 只有幾個孩子在家。大桃說是九個, 其他孩子一時說是三個,一時說是五個,寧氏看著眼前整整齊齊的八只豬,簡直氣不打一來,小的就算了,夫妻倆還當這小子十歲了連數手指頭都不會,一連幾天看著兒子就不上氣。
Advertisement
這會兒見著兩只一樣的小豬崽兒,便覺得這事兒恐怕是真的,三房從前拖家帶口地在他家吃了不飯,張有金對大房的位置記得倒比自個兒家還深,小時候還老錯口管張老大爹,以為張家大房的幾個孩子都是他的親兄弟。
想起這個堂弟也是自己看著長大的,卻變了今天這樣的敗類,張大伯嘆了口氣,看著張有金沉聲問:“你自己說,豬崽兒是不是我家的?”
張有金被張大伯問得眼睛一熱,眼淚就掉了出來,有心想說句實話,他也不知道自己怎麼了今天這個樣子,他只是想過得好點兒而已,這有錯嗎?張大伯家里有九只也不肯分親堂弟一只,眼見著兩家人越來越生份,他可不得為自個兒好好打算?想到這張有金又理直氣壯起來,但他怕被揍,便忍了氣不說話。
大伙兒看他眼神閃躲的樣子誰不知道真相如何?
里正開口就要把豬還給大房,羅氏哪里能肯,只坐在地上一昧地哭老頭子死得早。就讓兩房合伙欺負到頭上來了。
洗刷了冤屈的大桃也很委屈,看著他娘也要哭了。
寧氏卻沒功夫管他,只看著羅氏冷聲問:“嬸子真的不知道?”
賣兒和豬,羅氏都說不知道,三個人在家總有聲兒,豬也不是個死的,哪里就能不知道了。不過是不想知道罷了。
羅氏迎著寧氏冰冷的目,還著心卻虛了,不自在地別開眼。
看著老張家三房人劍弩拔張的樣兒,里正心里就咚咚咚跳個不停,就怕一窩蜂打起來——這不是沒有的事。眼睛便四找張阿公,想讓他做個和事佬。
張阿公已經不當家,把事兒丟給兒子,自個兒拉了魚姐兒看豬。
Advertisement
小豬崽兒一看就沒好好照料,比大房家那只弱了不知多,站都快站不起來了。
豬這東西還很有些野,雜事得很。吃自己同類也吃人,鄉間許多小孩兒都是喂豬喂沒了的。若是大房家那只,張知魚還不敢,但這只站都站不穩了,張知魚便手一翻把豬肚子出來看,然后樂顛顛地跟阿公道:“是個公的,能騸。”
張阿公看著豬習慣地思考起來,他多知道點騸馬的法子,估著豬也差不多,得從兩側割開,把蛋蛋出來,但這樣的傷口太容易發炎了,豬一不小心就會死掉。
張知魚想了想道:“現在是冬日,不容易染發炎,若居住的地兒能干凈整潔,用草木灰裹裹把傷口裹起來也許能行。”
張阿公有些奇怪:“什麼染發炎?”
張知魚就同他解釋:“好比小豬崽兒本來沒病,但他有了傷口,在外邊的臟東西從傷口進去就會讓它不舒服,病也會惡化,這樣就是染。”
張阿公點點頭,這不就是外邪?只是說法不一樣而已,他也不怎麼驚奇,天下醫流派那麼多,很多大夫都有自個兒的習慣,只要能認準病癥,怎麼都不是問題。
里正看著一老一嘀嘀咕咕地討論怎麼騸豬,就想起剛剛來時聽到的幾句話,不由眼前一亮道:“這豬崽兒我看不如讓張有金買下來給大伙兒使,把它給騸了看能不能長,能長以后鄉里也多個發財的路子,不能就也算給了他一個教訓。”
張大伯本來舍不得騸自家豬,但他心里他家豬只有八只,這只多出來的他從沒見過,簡直稱得上意外之喜,用起來也不怎麼心疼,便點點頭同意了。
張有金也知自個兒今日討不了好,只是買只豬兒子,回頭他不給錢張大伯還能怎地,總不能讓三房唯一的獨苗苗去死吧?便也忙不迭應承下來,賭咒發誓自己日后一定悔改。
Advertisement
但張大郎卻不愿意,一頭豬才多錢,他可是想把魚姐兒賣上至三十兩!
里正也沒想過就這麼便宜張有金了,便對張有金道:“既然你也同意,這豬你就拿三十兩來買,一天不就給鄉里干一日活兒。”
張有金雖不打算給這筆錢,聞言也氣得不行,看著里正就罵:“老雜,我看你是糞吃多了燒心,這豬是金子做的不?”
里正道:“你敗壞鄉里名聲,這三十兩里有一兩是大房家的豬錢,你自己想法子還他,如今的豬都能賣到這個價,剩下的二十九兩是罰你為鄉里勞作贖罪,這已經是便宜你了。”
張知魚也冷眼看著他:“你把你三個姐姐賣了三十兩,不到兩月就花個,我還以為你兩個月就能掙這一筆銀子了。”
提起這茬張有金不說話了,他知道鄉里埋怨他害得許多人娶不上媳婦兒。
但這也是白擔心,鄉里沒注意他和魚姐兒這場司,他們也對這三十兩沒什麼興趣,用腳趾頭想張有金也掙不出來。他們更想知道騸豬的事兒,等里正把豬妖的事兒一說,大家就很關心了,在大桃鄉人心里,張阿公說話還是很有分量的,當下仿佛就見著那白花花的朝自己飛來,忍不住扭頭討論起來。
這會兒張有金在他們眼里已經不是個爛人而是一個可供使用的勞力了,張家人看不住他,那一鄉的人呢?他還能懶?
就有人道:“我看不如這樣,算他一日四十文,干滿三十兩再說,到時候豬長了,前九十斤還了張家大房去,多出來的算在大伙兒頭上。”
張大伯想了想也同意,他是半點不指那一兩銀子,若養自己有拿虧不了,不就讓他給家里干活兒,有全鄉監督也不怕他不干。
Advertisement
鄉民一起算了好幾遍都沒算出張有金這樣得干幾年。
張知魚有點看不下去了,便告訴他們:“兩年,兩年就干完了,但這兩年可是他三個姐姐的一輩子!”
人群里寂靜了一陣,鄉里民風淳樸,很有這樣的大惡人,大伙兒看他不起,但他們也沒法子救人,便又往上添了諸多養豬條款。
譬如,若豬活了且長了,多出來的都得算大家的,一塊兒給平分了。若豬長得好,來年大伙兒養了豬都得他來放。他們還規定豬只能長八十七斤,但說實話一般況下張大伯家的還是能有九十多斤的,八十多斤的豬除非災年否則真不好找,但除了張有金自個兒沒人在意這個,他們正盤算著如何鑒定張有金有沒有懶,最后的結論是——張有金不能長得比豬胖,不然肯定是他懶了沒好好喂。
張有金聽得膽寒,這回他才真的怕了,對上張大伯和張大郎,張有金心里其實多有點底,肯定再如何他們也不會真把自個兒怎麼樣。即使分了家,他們也是親,誰也抹不去這層關系。
鄉民就不一樣了,里邊也有不外姓人,還不把他當個豬狗使喚?
羅氏見滿鄉的人都針對自家兒子,眼皮子一翻就昏了過去,咕咚一聲栽在地上。
張有金很有眼力見地抹了淚便倒在娘上大喊:“娘,他們要把咱們母子兩個死啊。”
張知魚見著羅氏臉紅潤,顯見著比兒子還健康,便又拿出針走過去。
這次張阿公給的是最的那,羅氏眼皮子睜了一條兒。并非全然看不見,見著這針便想起兒子那時的慘,便緩緩睜開眼道:“我這是怎麼了?”
張知魚看著這兩人,心下慨真不愧是一窩的,一時看到羅氏手上的佛米串便手往羅氏手腕一按,只道:“我跟阿公學醫呢,如今手藝也不錯了,給你瞧瞧。”
說完魚姐兒便閉了眼聽脈,結果下一秒就臉大變,把個羅氏驚得說話都抖了:“如、如何,我真有事了?”
魚姐兒搖搖頭,問要了兩人大概的八字,想了想便嚴肅道:“這不是病,是被你兒子克的,你不知道,你兒子是孽胎轉世要好好干活改造,才能化解災厄,不然專克至親。”
張有金聽得直罵卑鄙,被張大郎瞪了好幾眼才消停下來。
羅氏本來不信,轉念想起這些年家里接連出事,先是老頭子一跤跌沒了,后來幾個兒也沒了,最近老覺著腰酸背痛,頓時心神就慌了起來,信了一大半兒。
等里正押著兒子去干活兒,羅氏也沒說半句話。甚至第二天一大早就起來苦口婆心地勸兒子上工,語重心長地跟他道:“兒啊,你好好地干滿年數,以后咱娘倆就會苦盡甘來。”
張有金被一群孩子看著刷了一天豬圈,就為著迎接明年冬要住的小豬崽兒,累得渾都疼,這會兒上還有豬糞味兒,哪想起來干活,被子一裹就睡了去。
羅氏見兒子這樣子,扭頭就去找了張大郎。
張家二房為這這事兒在鄉里多待了一天,這會兒人正在吃早食,張大郎聽了拍拍手就往三房走。
張有金還在做夢把張大郎千刀萬剮,卻忽然上一涼,便困地睜眼,正對上一片亮堂堂的天,“我房頂呢!娘!我房頂不見了!”
羅氏在外給豬添了把兒子昨兒割回來的草道:“兒啊,你春生哥說豬晚上睡了冷,掀過去給它蓋上了,你且忍忍,等過了這陣兒,驅了你的衰運,咱家的日子就有救了。”
作者有話說:
下一章要開防盜了哦。
謝在2022-03-21 03:17:21~2022-03-21 18:12:55期間為我投出霸王票或灌溉營養的小天使哦~
謝投出地雷的小天使:水墨丹青 1個;
謝灌溉營養的小天使:阿白、阿白 10瓶;ren、夜雪、柚子醬喵 5瓶;鹿鹿子 2瓶;云卷云舒、二二、明和 1瓶;
非常謝大家對我的支持,我會繼續努力的!
猜你喜歡
-
完結1532 章

神醫娘子手下留針
“夫君,乖一點……” “過了今晚,你可就沒有反悔的餘地。”男人看向醉酒後的小女人,溫柔出聲。 陳夢恬穿成農家媳婦,本想現世安穩,一不小心成了傾世神醫。 一手金針,天下無雙,生死人肉白骨,卻無人得知她醫毒雙絕。 多年以後,她發現一件驚人的事…… 她的夫君竟是日後權傾朝野,就連帝王都要禮讓三分的權臣! 他將她寵壞,慣壞,退無可退,心都亂了。
138.6萬字8 266734 -
連載833 章

王妃又名動京城了
王妃桑氏不守婦道,與人私通,王爺下令即刻封死棺材下葬!”慘死二十一世紀的天才鬼醫桑墨再次睜眼時,卻發現她已經成了京都裡暴虐成性的殘廢王爺正妃。不光被釘入棺材,還要被封棺活葬!她拚死僥倖逃過一劫,更是以驚人的鍼灸醫術為自己爭取到了活命的機會。本以為就此能安穩度過餘生,卻不料被冷虐無情的“殺神”八王爺盯上。“本王給了你半個天下,你這就想走?”“王爺的恩情我早已還清,概不相欠。”八王爺抱著白淨軟糯的小糰子,“那夫君和兒子的你打算怎麼還?”
149.8萬字8 28295 -
完結132 章

廢後將軍
你是君,我是臣,你要忠誠,我給你忠誠。你是君,我是臣,你要我犧牲,我為你犧牲。這輩子隻是君臣……作不了陪你天涯的人。虐文,入者慎!!!!!!!!每天早上900定時更新。由於本文作者一度君華好色貪財、見錢眼開,《廢後將軍》將於2016年2月26日入V。**********************那個叫一度君華的它又在作死了!!*********************《東風惡》渣一最近完結古言,1E。《胭脂債》渣一爆笑古言,那些年沒有猜中的開頭和結局!!《飯票》渣一爆笑末世文,小蘿莉教育落魄總裁!《灰色國度》渣一都市玄幻文,看蠻勇村女進化為呼風喚雨玄術師!《一念執著,一念相思》渣一仙俠言情文,你的執著,我的相思。《情人淚?歲月盡頭》渣一古代仙俠文,陪你到歲月盡頭。《金主,請上當》渣一古代言情女強文,大當家對決腹黑皇子。
51.6萬字8 5621 -
完結506 章

爺快跪下,夫人又來退親了
中醫世家的天才女醫生一朝穿越,成了左相府最不受寵的庶女。 她小娘早逝,嫡母苛待,受盡長姐欺負不說,還要和下人丫鬟同吃同住。 路只有一條,晏梨只能兵來將擋,水來土掩,鬥嫡母踹長姐,只是這個便宜未婚夫卻怎麼甩都甩不掉。 “你不是說我的臉每一處長得都讓你倒胃口?” 某人雲淡風輕,「胃口是會變的」。 “ ”我臉皮比城牆還厚?” 某人面不改色,「其實我說的是我自己,你若不信,不如親自量量? “ ”寧願娶條狗也不娶我?” 某人再也繃不住,將晏梨壓在牆上,湊近她,“當時有眼不識娘子,別記仇了行不行? 晏梨笑著眯眼,一腳踢過去。 抱歉,得罪過她的人,都拿小本記著呢,有仇必報!
90.4萬字8 31102 -
完結71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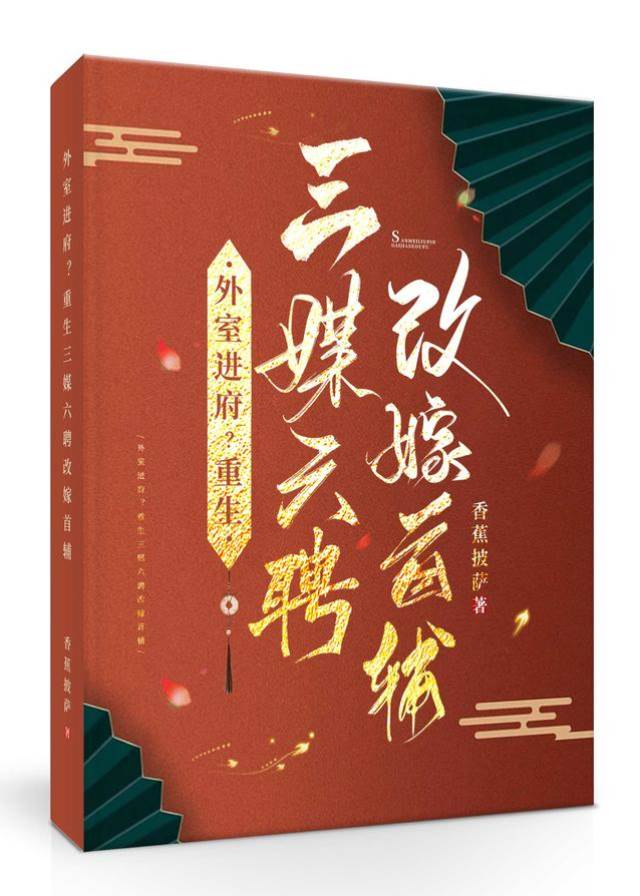
外室進府?重生三媒六聘改嫁首輔
【傳統古言 重生 虐渣 甜寵 雙潔】前世,蘇清妤成婚三年都未圓房。可表妹忽然牽著孩子站到她身前,她才知道那人不是不行,是跟她在一起的時候不行。 表妹剝下她的臉皮,頂替她成了侯府嫡女,沈家當家奶奶。 重生回到兩人議親那日,沈三爺的葬禮上,蘇清妤帶著人捉奸,當場退了婚事。 沈老夫人:清妤啊,慈恩大師說了,你嫁到沈家,能解了咱們兩家的禍事。 蘇清妤:嫁到沈家就行麼?那我嫁給沈三爺,生前守節,死後同葬。 京中都等著看蘇清妤的笑話,看她嫁給一個死人是個什麼下場。隻有蘇清妤偷著笑,嫁給死人多好,不用侍奉婆婆,也不用伺候夫君。 直到沈三爺忽然回京,把蘇清妤摁在角落,“聽說你愛慕我良久?” 蘇清妤縮了縮脖子,“現在退婚還來得及麼?” 沈三爺:“晚了。” 等著看沈三爺退婚另娶的眾人忽然驚奇的發現,這位內閣最年輕的首輔沈閣老,竟然懼內。 婚後,蘇清妤隻想跟夫君相敬如賓,做個合格的沈家三夫人。卻沒想到,沈三爺外冷內騷。 相敬如賓?不可能的,隻能日日耳廝鬢摩。
128.3萬字8.33 5353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