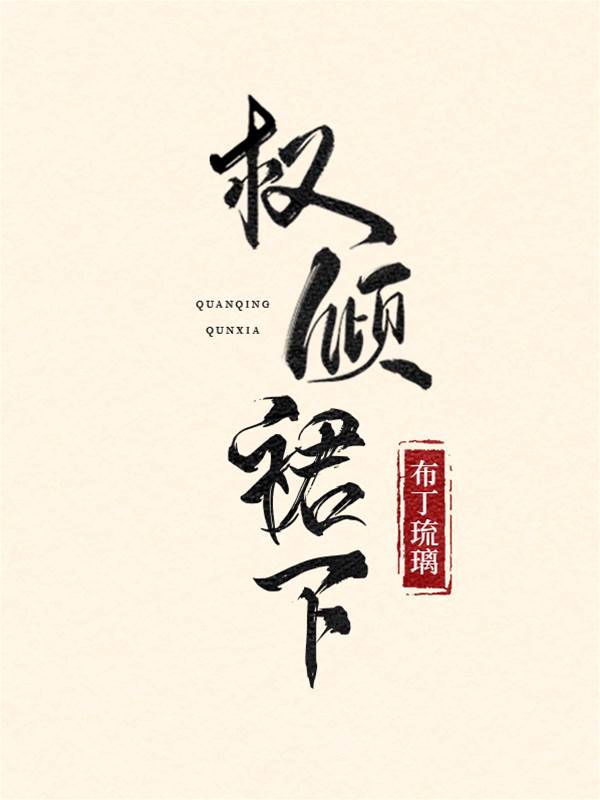《太子的外室(重生)》 58、哄
亥時末刻,阮菱喝了第二遍湯藥后便睡下了。
只點了幾盞夜間引路燈的大殿一片沉寂,窗外不知何時下起了小雨,雨聲過支摘窗滴滴答答敲打著,淅淅瀝瀝。
阮菱眠淺,微微蹙起眉,翻了個。
不多時,一冷風攜著細雨撲面而來,天青的帷幔被吹得呼呼作響。阮菱子瑟了下,突然發現床邊坐著個人。
心一驚,看清來人后這才松了口氣。可松緩過后,卻是直接轉過子。
方才侍奉湯藥的小宮十分有眼力見的,添油加醋的把書房發生的事兒學了一遍。
縱然知道是假的,可阮菱眼下還生著氣,不愿理他。
后猛然一大力,整個人直接被掰過了子,驟然的涼氣和疼痛,“嘶”的喊了聲:“你干什麼?!”
“菱菱。”
男人著的肩膀,大掌因那猛力的藥勁而不住抖,狠道:“看著孤。”
“大晚上你發什麼瘋?”阮菱手想去推開他,可他的力氣大的驚人,驚人到終于發覺到了不對勁。
抬手探上他的額頭,燙得驚人:“你發燒了?”
太子定定看著,著氣,一雙漆黑的眸漸漸變得赤紅。
空氣中,一縷細微的香味悠然攥阮菱鼻間。凝眉,這香味艷俗劣質,是人上的味道。
臉頓時冷了下去:“周萋萋真去了書房?”
聽得終于在意了,太子眼神深了深。
“是啊。”太子著的下,突然調笑道:“孤就像現在這樣,也著的下。”
阮菱抬胳膊打掉了他的手,罵道:“無恥!”
“孤是太子,想怎樣就怎樣。”裴瀾傾覆了上去,大掌鉗著兩條手臂,舉過頭頂,嗓音沙啞:“怎麼?菱菱不是想給孤納妾麼?周萋萋如何?孤即刻封了,奉儀?良娣,還是側妃?”
Advertisement
阮菱冷眼看著他:“裴瀾,你知道自己在說什麼?”
一張一合的朱,像是有一種魔力般,看的太子眸一直,他低頭,狠狠咬上那張嗡的,狠狠吮吸著。
阮菱對他心有抗拒,想到他和周萋萋,便是和他接一寸都覺得惡心。
“你松開!”
裴瀾咬著的鎖骨,狠狠一吸,伴隨著子吃痛的呼,一顆紅莓清晰的烙在白細膩的皮上。
他啞著嗓子,狠聲道:“菱兒為何躲著孤?納妾這事不是你提出來的,怎麼如今又不愿了?”
阮菱朝后躲著,可男人卻著的褪,不讓一一毫。眼前景無限好,男人肆無忌憚的打量著那道幽邃的風。
“瘋子!”阮菱滿臉屈辱,忍無可忍,抬手扇了他一掌。
這是太子殿下兩輩子挨的第一個耳。
藥勁作祟,他覺不到疼,只怔在那兒,像是被打懵了。
藥勁沖了上來,他每一都腫脹的厲害,額頭浮現一層薄汗,脖頸著青筋,太子子晃了晃,最后栽倒在阮菱側,攥著衾的指尖攥到發白。
“裴瀾?”阮菱見他真的昏倒了,眸有一瞬的慌。
搡著他的.口,急切喚:“裴瀾?裴瀾?你醒醒啊!”
“太醫!傳……”阮菱還未喊出去便被下的男人攥住了手。
“菱菱。”裴瀾忽地低低喚。
見他還有靜,阮菱頓時彎下子,趴在他邊聽,聲道:“你說什麼?”
“你為什麼就是不在意我呢。”男人邊嘟囔了一句后,徹底昏了過去。
他聲音小,阮菱沒聽清。不過此刻也顧不得睡覺了,著腳往外面跑,聲音在寂靜的黑夜里顯得格外急促。
“快。”
Advertisement
“傳太醫!”
翌日,東宮一并傳出了兩個消息。
昨日坤寧宮暈倒后,太監診脈的同時,發現太子妃有孕。二是有人意圖勾引太子,致使太子陷昏迷。所幸只是短暫的昏倒,沒什麼大事兒。
從大時思寺祈福回來的福樂公主第一個趕過來,接著各宮宮妃都著前來送禮,看。
敷衍了一上午,阮菱累極了。宮妃散去,只有福樂公主還在把玩著那些送來的禮。
福樂有些奇怪:“嫂子,你懷孕這麼大的事兒,我哥怎麼沒來看你。”
阮菱一怔,笑意在間凝了凝。道:“殿下公務繁忙,這本也不是什麼大事兒。”
不會說,一大早太子就跑來寢殿卻被攆出去的事實。
昨夜他那麼荒唐的行徑,還傷了的心。這事兒可不是輕輕揭過,就能過的。現在才不要見到他。
“這還不是?”福樂唏道:“這是皇長孫啊!我終于要做小姑姑了。”
阮菱抿笑了笑:“都說生下來的孩子誰第一個抱就像誰,皇兒的姑姑這樣貌,定錯不了。”
福樂著那小小的,薄薄的兜,只覺得即將孕育的新生命真是太神奇了。可開心之余也不免傷,放下布料,坐到阮菱側:“再有幾日,我便得回北境了。”
阮菱見難過,心里也跟著沉了沉。
自古和親的公主,那就是潑出去的水。若得夫家尊重,便可一年一次回朝覲見,若無尊重可言,便是此生再難踏上故土一步。
“等皇兒出世,我必給公主寫信告知。”
福樂笑了笑:“那到時候,我求夫君準許我回朝一次。”
從長定殿出來后,福樂心有慨,縱然離開了楚朝,可如今哥哥已經了家,還有了孩子。能讓他放下心氣,甘心娶回家的,必定是他所珍的。至在看來,哥哥也不算那麼孤獨了。
Advertisement
抬首了眼春,眼眸清澈,心底默默道:“母后呀,您看看,玥兒和哥哥都活的很好。您仙靈有知,也可放心啦。”
“顧將軍,您看什麼呢?”一旁的侍衛突然道。
福樂一怔,循著聲音,便瞧見了九曲回廊上的顧忍。
一襲藍,腰持佩劍,還是年時的容貌,只是那臉上的英氣深邃了幾分。
四目相對間,福樂那顆心臟久違的,就跳出心口。
縱然福樂如今已為人婦,可看見顧忍那墨藍的袍,總是能被帶回到年時的暑月。
此次回朝,有過無數次與他見面的時候,都不曾勇敢的說一句你好。如今,要離開國土了,有些人,也該好好道別了。
福樂轉頭對婢道:“你先去那邊等我。”
一襲緋繡著海棠的襦,記憶里公主那張揚明的花容添了幾分沉穩。
顧忍上前幾步,垂頭拱手作揖,聲音有些低有些沉,囫圇不清:“見過福樂公主,公主萬福金安。”
那修長如畫的指節,下意識的抖著,就連齒間涌出來的話,都竭盡全力才沒能發。
“顧忍哥哥,別來無恙啊。”福樂輕輕說著這一句,倏然眼淚便模糊了眼角。
顧忍僵抬起頭,胳膊不控制的抬起來,作勢就去眼角的淚痕,就像小時候一樣。
可手臂抬到一半時卻堪堪愣住了。福樂和他對視了一眼,皆從對方臉上看出了尷尬的神。
顧忍嚨間翻涌著酸楚,原來保護已經了一種本能。
他這樣做,于沈霜不公平,亦是對福樂的侮辱。
“在那邊,都還好嗎?”愣了半晌,他從一片發白的腦海里,匆忙揪出這幾個字。
“都好。”公主淡淡道。這兩個字輕輕揭過了在北境的三年。
Advertisement
在那個民族得過寵,也失過寵。可是不管怎樣,還是楚朝的公主,這些,亦都熬過來了。
福樂問:“顧忍哥哥也快家了吧,那位沈姑娘我聽過,很不錯。”
提到沈霜,顧忍邊舒緩了下來,他輕輕道:“和公主一樣,都很天真活潑。”
“那就好。”福樂又深深看了他一眼,強忍著心間的悸然,后退了一步:“本宮還有事,便先走了。”
在顧忍未反應過來時,福樂又低低道了句:“愿顧將軍比翼連枝,永結為好。”
顧忍怔了怔,隨后僵抬起頭,邊扯開了一抹釋然的笑容,他微笑道:“北境多曲折,公主保重。”
眼前婦人發髻模樣的子,突然變記憶里那個一紅,整日拿著金小鞭同他廝混在一起的。
顧忍了眼睛,持劍朝殿走去。
耳畔里吹來了經年的風,那年意氣風發的狂語猶在耳前。
“你真以為你以后能娶到公主啊!”
“那當然了,長大以后我要為大將軍,然后娶!”
——
東宮,書房。
“諸卿還有事兒嗎?”太子時不時看向窗外,心不在焉道。
討論了一上午,該落實的事宜基本差不多了。詹事府總管起道:“明日,圣人與殿下鑾駕出城,我等再無疑問。”
“跪安吧。”太子了眉心。
聽這群老臣聒噪了一上午,煩得很。
眾位大臣都走后,禮部尚書留了下來。他降了降聲音,肅然道:“殿下,七皇子裴止質子期滿,已從李國出發,不日即可抵達東京城。”
“孤知道。”太子闔眸,臉上似是很疲憊。
禮部尚書辦這些事宜,所以他最先得知的消息,可殿下既然知道,那有些話他不得不進言了:“殿下不可掉以輕心,圣人子嗣凋零,周皇后雖貴為中宮,卻一直無子,定然會把心思放在七皇子上,若中宮有了皇子,朝堂勢必會攪,對殿下的地位肯定也會影響。”
太子腦海里頓時浮現出一個五歲的小男孩,眼眸漆黑明亮,糯糯的喚他四哥。
他手指敲了敲桌案,淡淡道:“裴止他不會。”
禮部尚書焦急道:“怎麼不會?殿下您別忘了,七皇子他的生母是宸妃。宸者,北極星所在,常以指宮殿、王位,更可做帝王之稱啊!圣人的后宮除了已故的朝云皇后,可就是七皇子的母妃最得寵,不然周貴妃也不會一上位就著張羅把七皇子送去李國為質!殿下,您三思吧!”
禮部尚書每說一個字,裴瀾的眉頭便皺得愈深。
當年的事兒,是他沒護住裴止,是他不好。
“退下吧。”太子沉聲道,耐心顯然已經到了極點。
禮部尚書嘆了口氣,退出了書房。
尚書前腳剛走,纮玉后腳就急匆匆進去回稟:“殿下,娘娘要出宮。”
裴瀾抬眉,臉不慍:“怎麼好好的要出宮?”
就是跟他生氣也不至于出宮吧,懷著孩子磕著著了可怎麼辦?
不等纮玉說話,裴瀾匆匆道:“孤親自去看。”
纮玉言又止,嘆氣道:“殿下,娘娘這會兒已經出去了?”
太子眼刀飛過來,纮玉急忙了口氣,飛快答:“屬下早想進來的,可屋里都是議事大臣,屬下就沒敢……”
太子倒吸口冷氣,強著的聲音皆是冰冷:“你覺得在孤心里,這兩個事兒,哪個重要?”
纮玉子都僵了,弱弱道:“太子妃……”
“那還不去備車?!”
——
阮菱換了一常服,帶著清音出了宮。
一早得了信兒,林要回揚州。想著那日在坤寧宮曾幫過自己,便想著去送送。
草長鶯飛的時節,碼頭兩側桃紅杏白,鳥兒清脆,打春的日子,微風都和煦的不得了。
“真決定了嗎?”阮菱看著林心事重重的步伐,聲問。
林笑了笑,抬頭深吸了一口氣:“為什麼不呢?”
也許本不適合京城,還是煙雨蒙蒙的揚州適合。
阮菱握著的手,勸道:“林姑娘,若是為了恒王,那真的不值得。你才多大的年紀啊,往后還有那麼多年呢。”
“阮姐姐,你不必說,我都知道。家中祖母年紀大了,我不在邊總是想我的。等把祖母送走,我再來京城。”
猜你喜歡
-
完結307 章

妃揚跋扈:重生嫡女好妖嬈
上一世鳳命加身,本是榮華一生,不料心愛之人登基之日,卻是自己命喪之時,終是癡心錯付。 重活一世,不再心慈手軟,大權在握,與太子殿下長命百歲,歲歲長相見。 某男:你等我他日半壁江山作聘禮,十裡紅妝,念念……給我生個兒子可好?
56.5萬字8 7103 -
完結201 章

逆天嬌妃:皇上把持不住
宋微景來自二十一世紀,一個偶然的機會,她來到一個在歷史上完全不存在的時代。穿越到丞相府的嫡女身上,可是司徒景的一縷余魂猶在。
52.1萬字8 27669 -
完結148 章

丞相重生后只想擺爛
柳枕清是大周朝歷史上臭名昭著的權臣。傳聞他心狠手辣,禍亂朝綱,拿小皇帝當傀儡,有不臣之心。然老天有眼,最終柳枕清被一箭穿心,慘死龍庭之上。沒人算得清他到底做了多少孽,只知道哪怕死后也有苦主夜半挖開他的墳墓,將其挫骨揚灰。死后,柳枕清反思自己…
57.7萬字8 9491 -
完結13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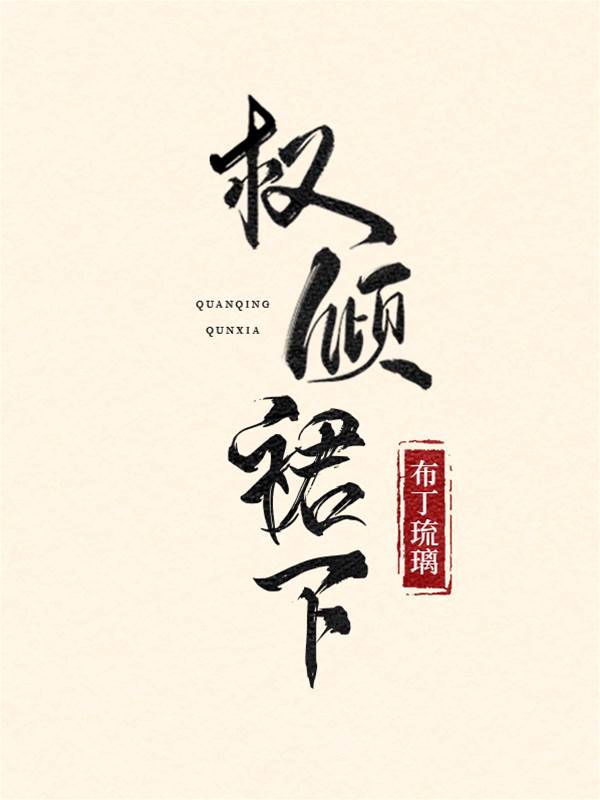
權傾裙下
太子死了,大玄朝絕了後。叛軍兵臨城下。為了穩住局勢,查清孿生兄長的死因,長風公主趙嫣不得不換上男裝,扮起了迎風咯血的東宮太子。入東宮的那夜,皇后萬般叮囑:“肅王身為本朝唯一一位異姓王,把控朝野多年、擁兵自重,其狼子野心,不可不防!”聽得趙嫣將馬甲捂了又捂,日日如履薄冰。直到某日,趙嫣遭人暗算。醒來後一片荒唐,而那位權傾天下的肅王殿下,正披髮散衣在側,俊美微挑的眼睛慵懶而又危險。完了!趙嫣腦子一片空白,轉身就跑。下一刻,衣帶被勾住。肅王嗤了聲,嗓音染上不悅:“這就跑,不好吧?”“小太子”墨髮披散,白著臉磕巴道:“我……我去閱奏摺。”“好啊。”男人不急不緩地勾著她的髮絲,低啞道,“殿下閱奏摺,臣閱殿下。” 世人皆道天生反骨、桀驁不馴的肅王殿下轉了性,不搞事不造反,卻迷上了輔佐太子。日日留宿東宮不說,還與太子同榻抵足而眠。誰料一朝事發,東宮太子竟然是女兒身,女扮男裝為禍朝綱。滿朝嘩然,眾人皆猜想肅王會抓住這個機會,推翻帝權取而代之。卻不料朝堂問審,一身玄黑大氅的肅王當著文武百官的面俯身垂首,伸臂搭住少女纖細的指尖。“別怕,朝前走。”他嗓音肅殺而又可靠,淡淡道,“人若妄議,臣便殺了那人;天若阻攔,臣便反了這天。”
52.5萬字8 2214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