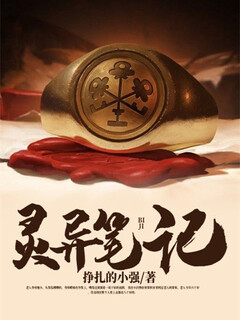《我是千年大棕子》 第十七章鬼殿中
我很豪放地在槍哥面前撂了狠話,也很爽快地看著他沒說什麼默默轉離開了。可是沒過幾天,我就被迫自食惡果了。
原因很簡單。因為某個不知名的原因,紅搖在洗澡的時候一不小心把我房間和房間的水管都給弄了。而這個時候,基地裡會修理水管的人只有槍哥一個……
“他肯定不會修的啦。”我拍脯保證,“那天我才剛讓他圓潤地滾開,現在去讓他幫忙他大概只會讓咱們圓潤地滾回去。”
……然後本來沒有參與破壞水管的我愣是被紅搖拖到了槍哥面前,用道歉作為修理水管的附送禮。
我不不願地被紅搖按著後腦勺站到了槍哥面前,那廝剛剛睡醒,隨便套了條短赤著上站在我臉前,垂著眼簾看我。
“槍兵,阿守來跟你道歉了,”紅搖笑容滿面,然後按著我的頭威脅,“對吧?阿守?”
“……”
“你看阿守都道歉了,所以來幫忙嘛!不修好水管的話今晚上我們都要在船上睡覺了哦!”
“是麼?”槍哥點上煙,閑閑了一口,“可我怎麼看著,這家夥沒什麼誠意呢?”
“你……”我張就想罵他,我敢打賭,以這家夥的心獷程度,肯定早就忘了紅搖說的是什麼事了,只不過不想放過任何一個整我的機會罷了。可我還沒說出口,紅搖就又一次把我的下摁到了口上:“哪裡!阿守很有誠意的,對吧?阿守快說!”
說著,還湊到了我耳朵邊低聲威脅著:“不把他哄高興了,我就把你砸碎九叔花瓶又粘起來的事告訴九叔!”
“……”
我很不願地兩只腳蹭了一下,開口道:“那個……對不起啦,是我的錯,下次我一定不再讓你滾了,所以麻煩你去修一下水管,OK?”
Advertisement
“哦?然後改讓我爬開?”槍哥慢悠悠說道。
恭喜你,答對了。
“罷了,想從你裡聽到真心的道歉,我還不如盼著天上掉妹子。”槍哥把煙掐滅,“哪裡壞了?”
其實,從很多方面來說,槍哥的確是個很不錯的男人。至當他頂著一水從修好的衛生間裡面爬出來的時候,平時最不待見他的我和紅搖還是崇拜地看著他。
槍哥一淋淋的,顯得那更加讓人垂涎。他斜眼看了看一直在瞄他的我們兩個,忽然勾起角笑了笑:“怎麼?想看?”
我和紅搖一起比中指。
“想看也不給你們看。”他很賤地說,“任守,怎麼,和張玄吵架了就想要換人看了?”
“誰說我們吵架了?”我用鼻子出氣,“我們好得不能再好了!一切惡勢力都無法改變我們之間的比金堅!”
槍哥做了個嘔吐的表,剛想說些什麼,卻被一個人打斷了。
“不好意思,請問……任守小姐是嗎?”
我們一起扭過頭去,出乎意料地,一個完全不該出現在這裡的人正站在走廊邊上。蒼離穿著一件米的休閑西裝,冠整齊微笑無懈可擊地看著我。我下意識低頭看了看這邊三個人的睡和衩,頓時覺一定是這家夥跑錯片場了。
他走過來,彬彬有禮地出手:“來天門這麼久,和其他的人都悉了,只是還沒跟你好好聊聊。聽九叔說你是天門的主要戰鬥人員,真是不可思議。這麼小的姑娘居然這樣強大。”
我瞪著那只過來表示友好的手,沒有作。
蒼離也不在意,收回手去笑了笑:“聽說上次在小月氏的祭壇中,那個一切的關鍵——礦石方瞳就是你找到的?真是不簡單,不知道能不能和我聊聊?我對這個巧很興趣,也……”
Advertisement
“不能。”
我本沒張,所以有那麼一會兒我簡直以為自己練了用大腦直接發聲的本領。可是我很快覺得這種金手指不是我的風格,萬一我在心吐槽九叔被聽到的話,開了這玩意兒絕對是賠本生意。我回過頭去,發現張玄站在角落裡,剛才那句話正是他說的。
他大步走了過來,面癱的臉之下有點沉。沒等我們幾個反應過來,張玄抓住我的手腕,一個閃擋到我前面,把蒼離完全擋到了我的視線之外。
“什麼都不能。”他毫不客氣地對蒼離說,“和你沒什麼好說的。”
“這樣嗎?那真是太可惜了。”蒼離的涵養簡直好到讓人驚歎。面對這樣的張玄他依然笑容可掬地說著。張玄皺了皺眉頭,沒有繼續廢話,他拉著我的手,一路踉踉蹌蹌把我拖離了他們的圈子。
“等等,張玄你……你放開我!”被扯到電梯裡的時候,我氣惱地甩開他的手,“你幹什麼?就算我也不喜歡那個人沒錯,可這樣也太沒禮貌了吧!”
張玄眼睛斜視著地面,就是不肯落在我上,當然也不說話。
這種沉默不同於以往他發呆我吐槽的歡樂相模式,低沉的抑、慌的恐懼,我能約到他上散發出的那種不安緒。可無力的是,我連他在想什麼都不知道。
“你不想,和我說什麼嗎?”
我努力平靜著語氣,試圖和他講道理。
張玄了,似乎想說什麼。可是他抬起眼睛對上我的視線之後,又好像被了角的蝸牛,整個人迅速回了殼裡。
張玄小蝸牛,幹得漂亮。
“不說是嗎?那我走。”
我盯了他半天,終於功放棄了。我扭頭就走,結果忘了自己是在電梯上,剛剛轉就結結實實撞到了關著的門上,鼻子上的麻筋被彈了一下,兩行清淚潸然而下。
Advertisement
我捂著鼻子眼睛蹲在地上哼哼的時候,後的人慢慢試探著猶猶豫豫抓住了我的服。
“對不起,你別走。”張玄小聲說。
“對不起有用的話,要扣工資幹嘛啊!”我用力甩,甩,還是沒甩開他的手,“你在鬧什麼別扭?又是不跟我說話又是吃無名飛醋的,我和那個蒼離半句好話都沒說過!你憑什麼一副覺得我在出軌的樣子?還不說話……靠,有本事你晚上別拉著我去小黑屋照向日葵睡覺啊!還嫌棄我,抱你的兔斯基去吧!”
張玄拽得更加用力,幹脆整個人都到了我的後背上。他悶悶說著:“沒有……不要分開睡。沒有不說話,我沒有……”
“閃邊!別著我!不解釋清楚你這段時間怎麼了,就別再拉我上你的床!”
我們兩個在電梯門前的一小塊,推推搡搡挨挨,沒留神,電梯已經到了停靠地點,門悄無聲息地開了,我們兩個疊羅漢狀一起栽到了前面。
日喲……為什麼我們兩個就連吵架都能吵得讓我自己都覺得跌分子!
我尷尬地用力把張玄推到一邊,站起來到看著。他坐在地上不起來,黑眼睛幽幽看著我,一側的臉頰鼓起來,像是裡含了一把松子的松鼠。
“起來!大男人一個,像什麼樣子。”我斥責著,“你到底在想什麼呢?有什麼事不能告訴我?”
張玄慢慢站了起來。他沒有回答我的話,只是緩緩環視著周圍。
剛才進電梯的時候,誰都沒有注意到按了哪一層的鍵。現在看來,應該是誰不小心按了鬼殿的樓層,現在我們所的位置,正是地下室鬼殿。
我不喜歡這個地方。這裡是天門擺放從地底拿出來的各種詭異神奇恐怖危險品的地方,且不說會不會不小心打破了個瓶子就染上古代病毒一命嗚呼,單是那些東西散發出來的死氣,就讓我覺得像是再次回到了被關押在地下的日子,冰冷,寂靜,快要窒息的黑暗氣息,讓人只到無邊的絕。
Advertisement
好幾百平方米的空間,沒有人,沒有生命,牆擺放的玻璃櫃,在冷燈照下的展覽臺,放著寒氣森然的刀劍、半閉雙眼的古、跡斑斑的、綠鏽幽幽的青銅鼎……我知道這裡的每一件東西拿出去都價值連城,可它們也是如此讓人不想接近。它們現了那悠悠幾千年的另外一面,除了博館展出的輝煌燦爛,還有與之相對的、淌滿了鮮和絕尖的曆史。每一段,都慘不忍睹。
張玄向前走了兩步,可也僅僅是兩步而已,他搖搖晃晃停了下來,有些茫然地看了一圈,回過頭來,目又定格在我上。
“諾諾。”他喊我的名字,“你別跑。”
“……我一微米都沒有,親。”
“是啊,你現在沒有跑。”他有些勉強地彎了彎角,似乎是想要笑,可那個表卻比哭還難看。
“你說,你不喜歡地下,不喜歡氣。你討厭沒有的地方……可是,假如我也來自那樣的地方,你會不會討厭我?”
他又往前走了兩步,漸漸踏了離我們最近的一個展覽臺的中。他邊擺放著青銅劍和陪葬的人俑,冷白的線從上面照下來,映得他線條分明的臉恍若一尊石像。和旁邊那些地下的東西沒什麼差別的冰冷石像。
“如果我不是我,要怎麼辦?”張玄一只手握住了腰間的刀,另外一只手在虛空裡抓了一把,“我想起了一些東西……但是也什麼都記不起來。諾諾,要是我也和它們一樣,要是我也屬於地下,要是……我做過傷害你的事,怎麼辦?你會不會討厭我,然後跟蒼離或者槍兵走了?”
聽前一半的時候,我很心疼他。聽後一半的時候,我很想揍他。
我深吸了一口氣,然後大踏步幾步過去,一掌打斷了他正在擺的迷茫憂鬱POSE。
“你腦袋裡裝的什麼?!我在你心目中眼就那麼差嗎?還蒼離或者槍兵……嘔!一個小白臉一個種馬,你覺得他們配得上我嗎!”
我扯著他遠離了那些東西,在他上了,找出手電筒打開來。一邊教訓著他:“早告訴你別想那些七八糟的……什麼做‘你不是你’?你就在這裡!張小玄我警告你,你可是對我媽媽說過要照顧我對我好的,敢食言的話,我就……就算你你的房產在地下又怎麼樣?我們有手電筒!”
我埋怨地用手電筒敲他的頭:“你怎麼這麼傻啊?就算我再討厭那些東西,怎麼會討厭你?我……我還會擔心你嫌棄我太醜太二配不上你這種高富帥呢!笨蛋張小玄,只要你不在外面找個人,不會離開你的啦。”
張玄猶豫抬頭:“真的?”
“呃,男人也不行!”
張玄出手來,認真地看著我:“拉鉤。”
“……好,拉鉤……”
我無力地出手來和他拉了拉,拍了拍他後背:“別扭鬧完了吧?走吧給我上去,就算大話說過了,呃……我還是不喜歡這種地方!”
“還沒有。”
“……啊?”
張玄一只手勾著我的肩膀,低下頭來:“這裡有攝像頭,紅搖說,在攝像頭下面做什麼事很有。槍兵說這樣做很無恥。舒道說最好不要。”
“……所以你到底想說什麼?”
“我們來做一點壞事吧。”
說著,他的臉就湊了過來,沒等我說話,上了我的。
猜你喜歡
-
完結11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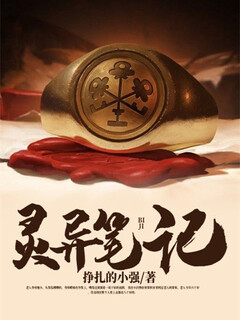
靈異筆記
為什麼自從做了眼角膜移植手術後的眼睛時常會變白?是患上了白內障還是看到了不幹淨的東西?心理諮詢中的離奇故事,多個恐怖詭異的夢,離奇古怪的日常瑣事…… 喂!你認為你現在所看到的、聽到的就是真的嗎?你發現沒有,你身後正有雙眼睛在看著你!
29.6萬字8 7554 -
完結4219 章
玄門遺孤
一把桃木劍,一個羅盤,一把硃砂,鬥惡鬼,捉殭屍,茅山遺孤,修煉傳承道法,在走風雲江湖。
756.9萬字8 64071 -
連載2087 章
天師神婿
符靈天師入贅為婿,卻被小姨子欺負天天捏腳,不料小姨子撿來一頂黃皮子帽,招致惡靈纏身!從此以後,小姨子:姐夫,我錯了,求你不要丟下我......
194.7萬字8 6073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