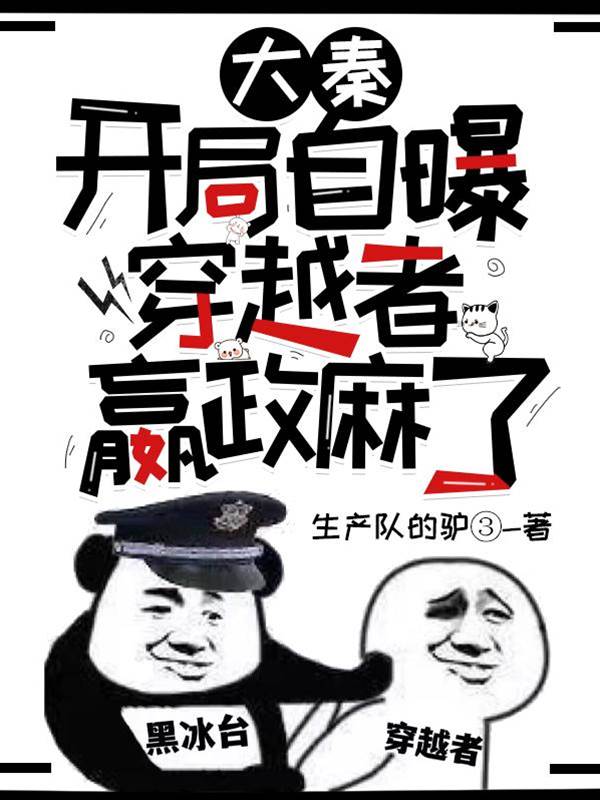《逍遙小閑人》 第51章 受傷了
“啊。”蘇止溪嚇得花容失,尖聲驚。
“啊,小姐。”冬晴和小暖一臉的驚駭絕,也同時嚇得都嚇得尖聲驚了起來。
此時白一弦也不知道自己的反應為何那麽快,幾乎是下意識的就飛撲了過去,一下子就接住了蘇止溪,並穩穩的把護在了懷裏。
但他自己卻重重的摔倒在了地上,疼的他差點眼淚都出來了。
“小姐。”冬晴等人慌張的飛奔過來,扶起蘇止溪就開始上上下下的仔細檢查:“小姐,你沒事吧?有沒有摔倒哪裏?
疼不疼?都怪奴婢,該一直在小姐邊護著的。小姐若是有個什麽事,那奴婢真是萬死都不能贖罪。”
聲音帶著哭腔,眼淚早就嘩的流出來了。
小暖也急忙去扶自家的爺,同樣是急得不行開始檢查。
蘇止溪搖搖頭,說道:“我沒事,到是白爺,為了救我,怕是了傷。”
蘇止溪說著,往白一弦那裏看了過去。此刻的心是非常震撼的,沒有想到白一弦為了救,竟然如此不顧。
因為不止是摔一下那麽簡單,當時們是在車廂前,摔倒之後,那馬帶著馬車一起狂奔,很容易遭到碾。
可他還是不顧一切的撲了上來,救了自己,毫不在意他自己是不是會傷,是不是會死。
蘇止溪在這一刻,心悄悄的變化了。如果說以前嫁給白一弦是無奈不甘,這幾天見他改變了,是自我安,那麽現在,的心中真正接納了白一弦。
一個可以為了自己不顧的男子,難道還不值得自己去嫁嗎?!
Advertisement
蘇止溪關切的問道:“你……你沒事吧?那麽危險,你何必……你就沒想過,你自己可能會死嗎?”
白一弦顧不得蘇止溪的心變化,一擺手,神非常焦急擔心,說道:“我沒事,可元兒還在車上。”
說完,就忍著上的劇痛,開始往馬車的方向追,同時心中不斷念叨著:“元兒可千萬不能有事,他還那麽小。”若是一旦被甩出疾行的馬車外,估計命難保。
其他幾人也想起來此事,臉都白了,急忙跟著白一弦後麵去追。
馬車速度很快,很快不見了蹤跡,好在雖然下著雨,但路上很泥濘,車轍印很深。順著車轍印前進,一路都沒看到元兒被甩出車廂的跡象,這讓眾人心中略安。
天黑路,足足過了半個時辰,他們才終於在路邊看到了停下來的馬車,以及聽到了車廂傳來的哭聲。
白一弦神一振,急忙上前,掀開布簾一看,元兒並沒有事。白一弦放下心來。
元兒年紀雖小,卻很是聰明,馬驚的時候可能摔了一下,可就在他要出車廂的時候,他被那安置在中間的桌子擋住了,於是,他的抱住了桌子。
也好在這桌子安置的十分牢固,這才沒發生什麽危險,實在是萬幸。
元兒摔倒的那一下,也並不嚴重,沒有摔傷,隻不過被嚇得夠嗆。
白一弦鑽車,將元兒抱在了懷裏,輕聲的安著。
元兒嚇得狠了,哭了一陣,也哭累了,在他懷中睡著了。
白一弦徹底放鬆下來,頓時覺得渾上下無一不疼。尤其是後背和右臂,火辣辣的疼,不用看也知道,應該出了。
Advertisement
可他看了看三個,還是沒說出來。這大晚上的沒法理,說出來隻會讓們擔心罷了。
因為這一件事的發生,眾人的服也都了,天已經很晚,索雨小了許多,眼看快停了。
馬車已經偏離了大道,又是晚上,也不知道現在是在哪裏。
眾人找到這裏的時候,在不遠發現了一座破舊的茅草屋,他們便決定在那裏修整一晚。最起碼也得換服,烘幹一下。
來到茅草屋,發現這裏已經很是破敗,並無人居住,屋子裏有一半還是雨的,另外一半倒還好,稍微幹燥些。
比較幸運的是,那幹燥的地方有些相對幹燥的木柴。
但不幸的是,馬車夫隨帶的火折子了,點不著火。而其餘的幾人,都沒帶著火折子。
白一弦原本還想試試能不能鑽木取火,可他現在全疼的厲害,也隻好作罷。
沒有辦法,隻好放棄點火,這種況,還不如在馬車上睡。
雨已經停了,三個在馬車上換好了服,又將白一弦的服拿了下來,讓他去草屋裏換。
眾人將就了一晚,第二天一早,吃了一點隨攜帶的幹糧,找到了回大道上的路,便繼續往前趕路。
此時小暖卻驚了一聲:“爺,您傷了,流了。”
冬晴和蘇止溪聽到靜,急忙看了過去,發現小暖手裏捧著的,正是白一弦昨天換下來的服,在那服的背部,有一片跡,目驚心。
小暖很是疚,昨晚竟然沒有發現,爺一定疼了一個晚上,真是太失職了。
Advertisement
蘇止溪的目裏滿是是擔憂,還有些複雜和心疼,說道:“一定是因為救我的時候的傷。
你,你不疼嗎?怎麽不說呢?竟然忍了一晚上,傷口不理怎麽能行?”
白一弦有些昏昏沉沉的,說道:“昨天那麽晚了,說出來不是平白讓你們擔心嗎?放心吧,我沒事。”
蘇止溪對冬晴說道:“到了下一個城鎮停一下,去給他找個大夫。”冬晴點點頭,急忙出去代馬車夫了。
小暖不住的打量著白一弦,想看看他還有哪傷沒有。這才發現,除了背部之外,手臂也傷了,有跡從服上滲出。
小暖的淚一下子就流了出來,白一弦見狀,隻好安道:“別哭,哭什麽?爺沒事,不過都是些皮外傷,很快就會好。”
蘇止溪疚道:“對不起,都怪我,若不是為了我,你也不會傷。”
白一弦說道:“說什麽傻話呢?難道讓我眼睜睜看著你出事嗎?”
蘇止溪聞言,心中有些。
白一弦見們還是擔心,便說道:“好了,你們別一個個這個表,都說了我沒事,不過是些皮外傷。男子漢大丈夫,流些算什麽?”
可就算他再安,這幾個人還是一副憂心忡忡的擔憂模樣。
好不容易到了一個城鎮,去了醫館,找了大夫幫忙理了一下,親耳聽大夫說沒什麽大礙,隻是皮外傷,們這才放下了心。
白一弦又讓大夫給幾人看了一下,看們有沒有染風寒。還有元兒,小孩子到驚訝,很容易出現問題。
Advertisement
好在一切如常,除了白一弦之外,都沒有事。
隻是因為傷,白一弦有些發熱,大夫開了些藥。
拿好了藥,因為要煎藥,所以又在這裏耽誤了一天。
等白一弦端著那碗黑乎乎的湯藥灌進肚子去的時候,他也在心中不斷的腹誹:這古代的中醫雖然厲害,但隻是簡單清理幹淨了傷口,完全沒消毒啊。
這又是大夏天的,萬一染了可不是鬧著玩的。穿越回來一次,他可不想自己因為染而再死一次。
酒到是可以消毒,但這個年代的酒的度數實在太低,起不到什麽作用。他要不要將酒提純一下,弄點高濃度的酒備用呢?
猜你喜歡
-
完結2811 章
九皇子傳
我本書生郎,錯生帝王家。 讀過許多書,識得萬千字,要是個太平年就教幾個蒙童,得閑聽聽曲,再找幾個狐朋狗友,偷看誰家姑娘好看。 仗劍天涯,太累;紙醉金迷,太吵;推杯回盞,太脹;回首瞧了幾眼,竟然混了個定天之王,大好的一顆頭顱價值萬金,還是太煩。 走的路遠,知道草海深處有一座積雪萬年不化的高山,那十萬山後有一道地龍遮天的天火,天下之大也不過是一張棋盤。有紅顏知己,有諸子百家,難得一刻清靜,那就湊熱鬧下上兩手閑棋,等一個春暖花開的時候,看看年少時埋在海棠樹下的那壇酒熟了沒有。
502.5萬字8 32433 -
完結503 章

回到宋朝當王爺
靈魂重生在原本不存在的宋微宗第四子荊王趙楫身上,想著混吃等死,奈何總有麻煩上門。宋江,方臘造反!六賊亂政!西夏犯境。大遼南下中原!金兵入侵,靖康危在旦夕!不要慌,穩住。
92.2萬字8 14407 -
完結1353 章
官居一品
數風流,論成敗,百年一夢多慷慨.有心要勵精圖治挽天傾,哪怕身後罵名滾滾來.輕生死,重興衰,海雨天風獨往來.誰不想萬里長城永不倒,也難料恨水東逝歸大海.
456.8萬字8 19255 -
連載118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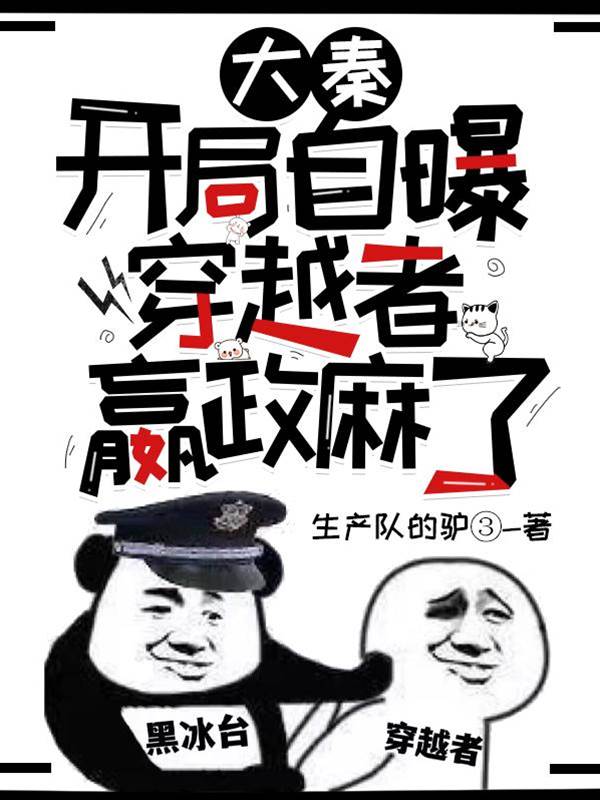
大秦:開局自曝穿越者,嬴政麻了
始皇帝三十二年。 千古一帝秦始皇第四次出巡,途经代郡左近。 闻听有豪强广聚钱粮,私铸刀兵,意图不轨,下令黑冰台派人彻查。 陈庆无奈之下,自曝穿越者身份,被刀剑架在脖子上押赴咸阳宫。 祖龙:寡人横扫六国,威加海内,尓安敢作乱犯上? 陈庆:陛下,我没想造反呀! 祖龙:那你积攒钱粮刀兵是为何? 陈庆:小民起码没想要造您的反。 祖龙:???你是说……不可能!就算没有寡人,还有扶苏! 陈庆:要是扶苏殿下没当皇帝呢? 祖龙:无论谁当这一国之君,大秦内有贤臣,外有良将,江山自然稳如泰山! 陈庆:要是您的贤臣和内侍勾结皇子造反呢? 祖龙:……谁干的?!我不管,只要是寡人的子孙在位,天下始终是大秦的! 陈庆:陛下,您的好大儿三年就把天下丢了。 祖龙:你你你……! 嬴政整个人都麻了!
247.2萬字8 9830 -
完結428 章

嶽父朱棣,迎娶毀容郡主我樂麻了
微風小說網提供嶽父朱棣,迎娶毀容郡主我樂麻了在線閱讀,嶽父朱棣,迎娶毀容郡主我樂麻了由過節長肉肉創作,嶽父朱棣,迎娶毀容郡主我樂麻了最新章節及嶽父朱棣,迎娶毀容郡主我樂麻了目錄在線無彈窗閱讀,看嶽父朱棣,迎娶毀容郡主我樂麻了就上微風小說網。
173.3萬字8.18 902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