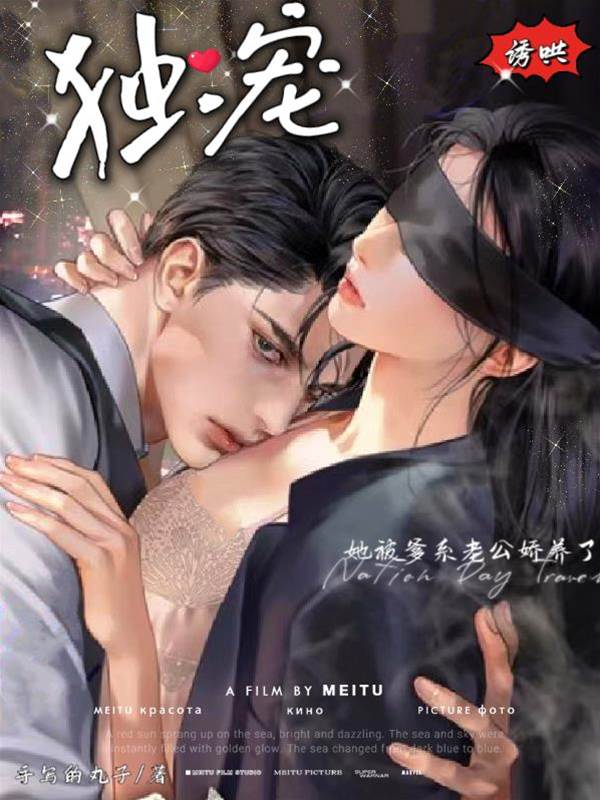《甜婚虐戀:蕭先生,抽空結個婚可好》 第62章 一夜八百
“想都別想,滾遠點。”黎清被氣得又想罵人又覺得好笑,面對這種事還能靜下心來打細算,力求利益最大化,果然不愧是他。
“那你先睡,我去洗個澡。”蕭景逸扯松領帶,又將襯衫上三顆扣子扯開,恰好出致的鎖骨。
“蕭景逸,雖然我是個狗,你長得也很合我心意,但是別以為個服我就會毫無尊嚴底線,對你言聽計從。讓我給你養孩子,想都別想,生孩子更是想都別想。”黎清用力咬著下,好幾次都差點控制不住土撥鼠尖起來,媽蛋,犯規犯規,這腰,這腹,這人魚線,這……上帝造人的時候這家伙到底塞了多錢,才換回來這麼一架讓黃金比例都黯然失的。
“這麼大一筆易,好歹先讓我驗個貨吧。”黎清覺有一只無形的手掐住了自己,連呼吸都急促了起來。
“沒有驗貨服務,最多讓你參觀參觀樣板間。”蕭景逸突然拉起黎清的手,放到了自己長年累月心鍛煉出來的腹上,低沉的語氣huo到讓人抓狂。
“什麼時候房?”黎清的臉刷的一下就紅了,但指尖卻難以自控的一直在流連忘返,手真好。
“裝現房,拎包住。”蕭景逸的呼吸逐漸沉重,低和鼻音織,莫名的,“不滿意無條件退款,今晚簽合同,還能買大送小。”
“蕭景逸,你天就知道假正經,外面人模狗樣,回家臭流氓一個。”黎清狠狠一口咬在了他肩膀上,然后抬手啪的一聲關上了床頭燈,“只要能潛蕭大董事長,這個盤我接了!”
清晨八點,黎清為了督促自己起床設置的連環鬧鐘響了一遍又一遍,簡直吵得人耳子疼。
Advertisement
起關了鬧鐘,剛想開個窗戶氣,就被蕭景逸拉著手臂一把又重新拽回了懷里:“別走,陪我躺一會兒。”
“我今天得去趟隔壁市。”黎清把頭親昵地擱在蕭景逸手臂上,“你也該去上班了。”
“不去。”蕭景逸的聲音有些沙啞,“手機給我,我請個病假。”
“喲,沒想到咱們c市的敬崗業模范也有裝病請假的一天。”黎清慵懶的挑了下眉,“哪兒不舒服啊,腎虛還是腰扭了?”
“我腎虛不虛你不知道?”蕭景逸霸道地把人按在了口上,力度大到恨不得把黎清活生生進里,“這麼看還是我了解你,你是水做的,又又哭。”
黎清臉一紅,嗔地在他膛上落了兩拳:“我以前怎麼沒發現你那麼不要臉?簡直白瞎了這麼一張系的臉。”
“今天別走了。”蕭景逸再一次拉住黎清的胳膊,“請了一天假,吃過午飯帶你去逛街。”
黎清雙眼熠熠生輝:“這算約會嗎?”
“算獎勵。”蕭景逸撐著床坐了起來,拿起昨晚趁黎清睡下后特意準備的錢包,故作高冷地丟到了面前,“給你的,看上什麼隨便買。”
黎清皺了下眉頭,心不僅毫無甜和幸福,甚至還想沖那張帥到天怒人怨的臉重拳出擊:“蕭景逸,你這是干嘛,霸道總裁bao養涉世未深大學生嗎?”
氣死了,這個死直男到底會不會正常談?你就是要給錢也不能這時候給呀。
黎清一個鯉魚打滾兒從床上躍到了地上,掏出錢包隨便了八百現金就往床上丟:“行價一次兩百,拿錢滾蛋,咱們兩清了。”
“你哪兒打聽的行價?”蕭景逸覺自己好像發現了什麼不得了的事,一個床咚把黎清在了下,兩人近在咫尺,鼻尖相,“黎清,你給我解釋清楚。”
Advertisement
臨近中午,宇文鳶和幾個同院的教授一起從行政樓走了出來。
“宇文,你那篇關于東漢西王母壁畫的論文又被院里選中送去參賽了,你自己說這都是這學期的第幾篇了?還給不給我們留活路。”一個年紀比他大些的男教授抱怨道。
“研究遠古歷史和神話系的人,我不過是鉆了個冷門空子而已。”宇文鳶笑得淡淡的,寵辱不驚。
“對了,我聽院長說你下學期不打算來了?怎麼,是覺得咱這小廟裝不下你這尊大佛,準備另謀高就,還是想到了什麼新課題,打算閉個關?”這次問話的是一個老師,長發齊肩,戴著副黑眼鏡,五平平卻充滿了知的。
“家里出了點事兒,我一個人力有限兼顧不過來,只能辭職了。”宇文鳶微微一笑,“這幾年承蒙大家照顧,不過天下沒有不散的宴席,緣分盡了也是沒法子的事兒。”
“你說你現在前途一片大好,怎麼犯得上為家務事兒辭職呢,這也太浪費了。”男教授趕勸道,“依我看,你就是缺個能理事的人,回頭我給你介紹一個,保準明強干,什麼事兒都給你料理得服服帖帖的。”
“噓。”宇文鳶突然打斷了他,“別說話。”
通往停車場的必經之路上,一道人影正倚著籃球場的鐵網,雙手環抱,冷冷地看著他們。
“怎麼現在就來了,記錯時間了嗎?”宇文鳶的聲音很溫,簡直讓人如沐春風,“我下午還有課,先讓人送你回家好不好?”
“不好。”
“那我陪你吃午飯,然后再送你回去好不好,旁邊有家很好吃的披薩,你肯定會喜歡。”
“宇文教授,這位是?”
一起共事四年,這些同事還從未見過宇文鳶如此溫和且耐心的對一個人說話。
Advertisement
作為學院里有名的中央空調,宇文鳶對誰都很溫和,態度彬彬有禮,卻又維持著讓人沒辦法靠太近的距離。
可現在的他竟然溫到像是在哄孩子,整個人由而外出一親和力。
“我學生。”宇文鳶了第五婧的頭,“從小就跟我學習,所以跟我格外的親。”
“難怪我看你對的態度那麼慈父,要不是看起來年紀沒有差太多,我都快以為這是你兒了。”
“舌頭要是不想要,我可以幫你拔了它。”第五婧剜了那個多的男教授一眼,眼神無形,殺氣卻近似實,“還有,你好像很喜歡給他介紹人?”
“小婧,人家是開玩笑的,沒有惡意。”宇文鳶趕擋在了和對方之間,“不好意思啊,我這個學生脾氣有點暴躁,我先帶去旁邊靜一靜,回頭再跟你道歉。”
聽到“小婧”這個名字,旁邊那個知的老師立刻下意識的抬了下眼,目落在第五婧臉上,一刻也不曾離開。
“跟我回家。”第五婧此刻的心簡直糟了,分不清讓自己緒波的原因到底是有人在覬覦自己的東西,還是宇文鳶不肯在外面公布他們的關系。
宇文鳶嘆了口氣:“好,你等一會兒,我現在去請假。”
真是倒霉催的,向來只在停車場接自己放學的小婧今天為什麼會提前走到學校里邊兒來?
“下午的課你現在去請假肯定請不下來的,教務那邊沒辦法幫你調啊。”那個男教授再次展現了自己實力坑隊友的王者水平。
宇文鳶差點被氣得背過氣去,我在這兒待了四年,難道會不知道這個點本沒辦法請假嗎?這麼明顯的緩兵之計能不能不要拆穿我!
Advertisement
“破學校,別干了。”第五婧沒了耐心,突然出手摟住宇文鳶的腰,一把將人扛到了背上,作練得像在扛麻袋,“老子回頭一車鏟了這兒。”
“小婧,放我下來!”宇文鳶一邊用手拍著的后背,一邊滿臉懵,這孩子今天到底是怎麼了,“太高了,我頭暈。”
裝病這招他以往百試百靈,今天卻啞了火。
第五婧充耳不聞,剩下的幾個同事對宇文鳶被當眾抗走的事表示極度懵,要知道對方再怎麼也是個年男,怎麼會一點反抗的余地都沒有?
“宇文這學生有點兒猛啊!看樣子應該是在追他,然后又沒追到。”男教授笑得眉弄眼,“難怪每次給他介紹對象,他都笑著拒絕,是后跟了這麼一尊母老虎。”
“你這張呀真是半點兒也閑不下來,剛才要不是宇文護著你,你現在估計腦袋已經開花了。”知教授扶了下眼鏡架,“宇文是作為特殊人才特聘進的咱們學校,在這之前他供職于安理穆斯大學,是安理穆斯有史以來最年輕的副教授。你們就沒好奇過以他的年紀做講師都勉強,這個副教授的位子到底是怎麼力排眾議評下來的嗎?”
“人家論文發得多唄,而且質量也很好,影響因子特別高。我們學校引進他不就是看中了他的論文數量和一級課題。”男教授滿不在乎地說。
“安理穆斯這樣的學校什麼時候缺過論文和課題了。我讀博期間曾經被換過去一段時間,所以我記得校董會第二執行董事有一個很獨特的名字,第五婧。”
猜你喜歡
-
完結38 章

半是蜜糖半是傷
三年前,他們已經走到了談婚論嫁的地步,但當林曜辰向她求婚時,葉微雨卻一臉不屑,將他手中鑽戒打落在地,“你一個林家的野種,有什麼資格向我求婚?”
3.9萬字8 47140 -
完結2338 章

億萬首席寵甜妻
五年前,她被設計和陌生男人發生關係,珠胎暗結。訂婚宴上被未婚夫淩辱,家人厭棄,成為江城最聲名狼藉的女人。而他是手握權柄,神秘矜貴的財團繼承人,意外闖入她的生活。從此,繼母被虐成渣,渣男跪求原諒,繼妹連番求饒。他狠厲如斯,霸道宣告,“這是我楚亦欽的女人,誰敢動!”“五億買你做楚少夫人!”她的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236.3萬字8.18 95034 -
完結108 章

全世界都以為他暗戀我
盛以沒想到,她高中時的同桌江斂舟現在紅極一時;更沒想到,她一個素人還得和這位頂流一起錄綜藝;最沒想到,她跟江斂舟的CP竟一夜爆紅。一個CP大粉的微博被轉出了圈:“江斂舟成名多年,卻半點緋聞不沾身,我以為他不可能會喜歡別人。…
45.2萬字8 21971 -
完結9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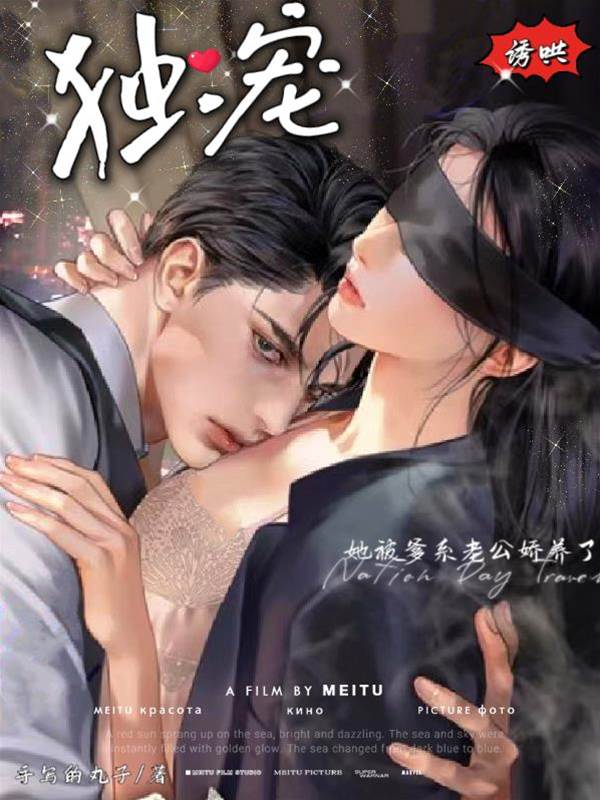
獨寵!誘哄!她被爹係老公嬌養了
1v1雙潔,步步為營的大灰狼爹係老公vs清純乖軟小嬌妻 段硯行惦記那個被他撿回來的小可憐整整十年,他處心積慮,步步為營,設下圈套,善於偽裝人前他是道上陰狠殘暴,千呼萬喚的“段爺”人後他卻是小姑娘隨叫隨到的爹係老公。被揭穿前,他們的日常是——“寶寶,我在。”“乖,一切交給老公。”“寶寶…別哭了,你不願意,老公不會勉強的,好不好。”“乖,一切以寶寶為主。”而實際隱藏在這層麵具下的背後——是男人的隱忍和克製直到本性暴露的那天——“昨晚是誰家小姑娘躲在我懷裏哭著求饒的?嗯?”男人步步逼近,把她摁在角落裏。少女眼眶紅通通的瞪著他:“你…你無恥!你欺騙我。”“寶貝,這怎麼能是騙呢,這明明是勾引…而且是寶貝自己上的勾。”少女氣惱又羞憤:“我,我才沒有!你休想在誘騙我。”“嘖,需要我幫寶寶回憶一下嗎?”說完男人俯首靠在少女的耳邊:“比如……”“嗚嗚嗚嗚……你,你別說了……”再後來——她逃他追,她插翅難飛“老婆…還不想承認嗎?你愛上我了。”“嗚嗚嗚…你、流氓!無恥!大灰狼!”“恩,做你的大灰狼老公,我很樂意。
15.9萬字8 1115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