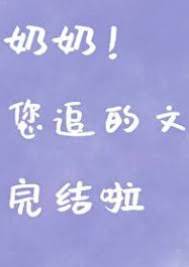《二婚媽咪是團寵》 第30章 穆總的報復
人子那種悉的戰栗,令穆意沉非常滿意。
過后,他角微翹:“你還跟當時一樣赧。”
大致是心非常好,聲音中顯見聽出愉快。
“當時離婚,我也年輕,可能,很多事理方法不當,可我今天講的這些話,字字句句皆有保證。你不必疑心我又在騙你,你有啥值的我騙的?”
這話真特麼直白啊,直白到令人無法坦然接。
就仿佛,對方吃準了必定會點頭同意一樣。
吳清歌惱怒,一把把眼前人推開,出手就要去……
“你但凡敢一下,信不信我會再親兩下?”穆意沉道。
口吻淡淡,好像吃飯睡覺,氣得非常自然。
吳清歌覺的,以前那個冰山男,讓到難以相,可如今這個莫明其妙霸總上的穆先生,好像更令人抓狂。
“先將粥喝了吧,涼了傷胃。”
見人抿,穆意沉眼尾含笑。
就如大姐穆朝歌經常講的那樣,有些話真從中出來了,好像也沒那樣難……
看見人怒而不發的生俏麗的樣子,他心口某個地方,好像正在被漸漸填滿。
……
從醫院出來時,外邊已是萬家燈火。
穆意沉不容回絕的要送回去。
快到碧水江汀時,吳清歌忽然看見唐一菲正牽著林林走在外邊林蔭道上。
“你將車輛開到全福元,我想買點東西。”
穆意沉皺眉:“你才病好,須要什麼我到時人買給你。”
“不須要。”
突然沖他一笑,可那笑容卻不達瞳底。
“穆總是不是有一些,太自命不凡了?不是你講什麼,其它就會答應的,你不是說……要我用心會,用心看麼?我現在就看你的表現哦。”
Advertisement
太懂這個穆意沉了,這個男人可沒那樣好的耐心。
車廂中瞬時一片緘默,吳清歌可以分明的看見,男人瞳底那一縷寒意。
便在還當他就要生氣趕下車時,穆意沉卻一反常態把車輛倒回去開往全福元。
沒停在大門邊,卻是直奔地下停車場。
“你停門邊就可以了。”
這一次到某男角輕勾:“看我表現?我陪著你一塊去,還能幫你提東西,你可要用心看。”
吳清歌心極度暴躁。
……
與此同時,吳家的氛圍卻有些凝重。
客廳中,吳家幾名主人齊聚一堂,曾凱表明來意以后,向吳幸媛,開門見山說:“那蛇,就是吳幸媛吳小姐擱到清歌小姐的禮品盒之中的,卻最終連累穆總,我們這里,已預備走法律程序。”
“不是我!”吳幸媛一口否認,“跟我有啥關系?我一個生怎麼敢那種玩意兒?你不要口噴人!”
曾凱笑意不變:“吳小姐再怎麼狡辯也沒有用,我今兒既然來了,自然手中已有充分證據。穆總被蛇咬,這是大事,我方不達目的,不會罷休。”
“胡說八道!那蛇是撥過牙的寵,你家穆總怎可能被傷到?”
吳幸媛而出,才后知后覺意識到說了!
曾凱滿意起,向吳家可以作主的吳老太太合吳家康:“您二位也聽見了,我可沒冤枉吳小姐。”
說話過猶不及,意思到了即可。
反正,曾凱今天這一趟,是必要吳家給個待才行。
吳家康面沉,吳幸媛本即有些怕他,眼及他冷寒的眼睛,更嚇的著頸子趕快躲到吳老太太背后。
吳老太太不喜吳清歌,自個兒的親孫兒自要護短:“幸媛就是跟開個玩笑罷了,只是這玩笑有點不合時宜,小孩子之間玩得太過,常有的事兒,罵幾句就算了。”
Advertisement
曾凱還沒出口反駁,吳家康卻已毫不猶疑吩咐家中仆人去請家法了。
且不管他打小到大對吳清歌的寵,單就今天穆意沉旁最得力的書親上門,這事也決不唬弄過去。
即使吳老太太有心維護都沒有用。
吳家康冷眼看著吳幸媛:“當時潔瑛小小年齡,便用同樣的方法嚇唬過清歌,你好的不學,倒將這些齷蹉東西學了個遍,今天,我這個作叔叔的,必得要你長記,知道分寸怎麼寫,不然以后遲早出大事!”
“你憑啥管我?你又不是我親生爸媽!”
吳幸媛紅了眼圈。
“你就看他們全都不在,才故意欺負我的!”
吳家康并沒因為的不敬而惱火:“你父親回老家前,特意囑咐過我要好生照料你,我不可以眼的看你走上邪路!”
呵呵,說的倒好聽!不就是想為吳清歌出氣嗎?
吳幸媛驟覺委曲,淚水撲簌直掉。如果吳家如今還是長房當家,哪里會被人這樣欺負?
氛圍一時之間有些低迷,見那仆人杵在原不,吳家康沖一吼:“還不趕快去!”
仆人肩頭一,馬上垂著腦袋倉促上樓。
此時,一直沒張口的韓茵向前,眼卻是落到吳幸媛平坦的小肚子上:“家康,昨天張董夫婦之所以勉強答應下這婚事,說白了,還是想早一些抱上第三代。”
此話說的委婉,可不難聽出在晦提醒吳家康,吳幸媛跟張毅春風一度,如今有可能已經有了小孩,如果冒然家法,說不定會出現意外。
吳氏眼下正于危機關口,可以抱張家大,那是再幸運不過的事。
吳幸媛也迅速會意,止住哭音,眉間浮上一得瑟,乃至故意起自己的肚兒。
Advertisement
有了這個護符在,還怕啥?
吳家康眉間輕蹙,隨即又展開,住已走到樓梯拐彎的仆人:“不必再請家法。”
吳幸媛一喜,可笑容還沒有來的及浮上眉尾,就聽見隨其后的冰涼一聲,“去拿書房屜子里的戒尺!”
比較起家法,板子打在手心兒頭,那疼也是不相上下。
戒尺板子到吳家康手中以后,不管吳幸媛怎樣怒罵,最終還是給倆仆人死死摁住,手心兒接連被狠打十下。
打完以后,腫的像饅頭,略一下就是死痛死痛。
瞅了幾眼倒在吳老太太懷中哭的撕心裂肺的樣子,吳家康面沉靜的,把板子扔一邊,然后從新向曾凱:“這個結果,不知穆總可否滿意?”
曾凱剛才見他親自打下去時,幾近沒有留余地,心中不免驚詫,可臉上卻沒分毫顯,只笑說:“既然吳先生都可以大義滅親,那穆總自然也不會斤斤計較。這事兒,便這樣算了罷!”
一頓,眼轉向吳幸媛。
“只是我還想給幸媛小姐提句醒,某些損人不利己的事兒,往后還是干為妙。到底,都要作新娘的人了,上戾氣太過,好像也不太好啊。”
吳幸媛聽見這話,陡然一戰,對邊人瞳底那一縷告誡,看的一清二楚。
這人便是穆意沉的走狗,他所說所作,全都是穆意沉的意思。
形勢比人強,吳幸媛即使心頭再不滿,此時也只可以先服下。
收住哭音,輕聲說:“我……我知道了。”
目的已達到,曾凱滿意走人。
吳家康把人送走,返回客廳馬上便遭到了吳老太太的譴責。
韓茵帶吳幸媛去上藥,客廳中唯有他們二人,吳老太太便沒再給兒子留臉面,手杖往地下狠狠一拄:“為個外人,如此狠心打自己的親侄兒,你對的起你大哥麼?!”
Advertisement
“媽,我不單單是為清歌。穆意沉既然選擇手,幸媛如不付出代價,他絕對不會善罷甘休,到時遭殃的可不止幸媛一人。”
吳老太太半個字都不相信,真由于穆意沉的關系,大可以作作模樣就是了,可剛才打板子時,每一下都和用足了力氣一樣,不要說幸媛一個小孩,便是大老爺們兒也都不住。
“說實話,你是不是還想著甄如蘭那個賤人?既然已經娶了韓茵,你就和人家安生過日子,等為你生下繼承人,一切就都走上正軌了……千萬別學你哥,鬧的家不是家,人不是人……行了行了,我不管你們了,我這老婆子究竟造了什麼孽,才生下你們這種兒子!”
提起曾一度讓自己滿懷期盼的長子,吳老太太心中久久不能沉靜,又見次子眉角皺,驟覺一陣煩燥,把仆人來,上樓去了。
許是又提到了“甄如蘭”仨字,直至跟前煙缸中煙頭堆小山,吳家康才逐漸舒展開眉角,一想,又取出手機拔了吳清歌的電話。
這時,吳清歌跟穆意沉從商場滿載而歸。
穆意沉一把奪過手提的唯一一個袋子:“我來。”
吳清歌瞅一眼他淺淺的面,才想講什麼,手機鈴音突然傳來。
吳家康電話來問是否還好,年時期,給吳潔瑛那樣一嚇,吳清歌高熱反復,足足七天才退,險些死掉。現在吳幸媛又故技重演,他唯怕有個三長兩短。
吳清歌輕笑,要父親不要擔憂,怕他多想,去了自個兒白天住院的事兒,只說穆意沉擋在跟前,啥都沒有看見。又安幾句,吳家康這才松口氣來。
等叩掉電話,二人不知不覺間已走到高檔小區的大門邊。
穆意沉明顯沒有預備就此打住,眼看往,提示把門卡取出。
齒過,吳清歌遲遲沒作。
“你送到這就可以,小區中有推車,我自個兒推上去就行了。”
“三更半夜,你一的不安全。”
猜你喜歡
-
完結260 章

小可愛你挺野啊
第一次和江澈見麵,男人彎著一雙好看的眼,伸手摸摸她的頭,笑著叫她小喬艾。他天生笑眼,氣質溫雅中帶著些許清冷,給人感覺禮貌親切卻又有幾分疏離。喬艾正是叛逆期的時候,個性還不服管教,但為了恰飯,她在江澈麵前裝得乖巧又懂事。時間一久,跟江澈混熟,喬艾的人設日漸崩塌……她在少女時喜歡上一個男人,長大後,使出渾身解數撩他,撩完消失的無影無蹤。多年後再遇見,男人紅著眼將她圈進臂彎裡,依舊彎著眼睛,似是在笑,嗓音低沉繾綣:“你還挺能野啊?再野,腿都給你打斷。”
44.2萬字8 20042 -
連載2076 章

撿個首富回家寵
送外賣途中,孟靜薇隨手救了一人,沒承想這人竟然是瀾城首富擎牧野。
237.7萬字8 208041 -
完結213 章
生崽痛哭:豪門老男人低聲輕哄
【年齡差11歲+霸總+孤女+甜寵+無底線的疼愛+越寵越作的小可愛】 外界傳言,華都第一豪門世家蘇墨卿喜歡男人,只因他三十歲不曾有過一段感情,連身邊的助理秘書都是男的。 直到某天蘇墨卿堂而皇之的抱著一個女孩來到了公司。從此以后,蘇墨卿墮落凡塵。可以蹲下為她穿鞋,可以抱著她喂她吃飯,就連睡覺也要給她催眠曲。 白遲遲在酒吧誤喝了一杯酒,稀里糊涂找了個順眼的男人一夜春宵。 一個月以后—— 醫生:你懷孕了。 白遲遲:風太大,你說什麼沒有聽見。 醫生:你懷孕了! 蘇墨卿損友發現最近好友怎麼都叫不出家門了,他們氣勢洶洶的找上門質問。 “蘇墨卿,你丫的躲家里干嘛呢?” 老男人蘇墨卿一手拿著切好的蘋果,一手拿著甜滋滋的車厘子追在白遲遲身后大喊,“祖宗!別跑,小心孩子!” 【19歲孩子氣濃郁的白遲遲×30歲爹系老公蘇墨卿】 注意事項:1.女主生完孩子會回去讀書。 2.不合理的安排為劇情服務。 3.絕對不虐,女主哭一聲,讓霸總出來打作者一頓。 4.無底線的寵愛,女主要什麼給什麼。 5.男主一見鐘情,感情加速發展。 無腦甜文,不甜砍我!
39.3萬字8 14199 -
完結18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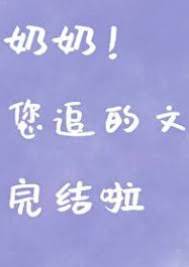
南風知我意
清遠公安裴西洲,警校畢業履歷光鮮,禁慾系禍害臉,追求者衆卻無一近的了身,白瞎了那顏值。 某天裴西洲受傷醫院就醫,醫生是個女孩,緊張兮兮問他:“你沒事吧?” 衆人心道又一個被美色迷了眼的,這點傷貼創可貼就行吧? “有事,”裴西洲睫毛低垂,語氣認真,“很疼。” “那怎樣纔會好一些?” 裴西洲冷冷淡淡看着她,片刻後低聲道:“抱。” - 緊接着,衆人發現輕傷不下火線的裴西洲變乖了—— 頭疼發熱知道去輸液:南風醫生,我感冒了。 受傷流血知道看醫生:南風醫生,我受傷了。 直到同事撞見裴西洲把南風醫生禁錮在懷裏,語氣很兇:“那個人是誰?不準和他說話!” 女孩踮起腳尖親他側臉:“知道啦!你不要吃醋!” 裴西洲耳根瞬間紅透,落荒而逃。 ——破案了。 ——還挺純情。 - 後來,裴西洲受傷生死一線,南風問他疼嗎。 裴西洲笑着伸手擋住她眼睛不讓她看:“不疼。” 南風瞬間紅了眼:“騙人!” 卻聽見他嘆氣,清冷聲線盡是無奈:“見不得你哭。”
36.3萬字8.18 15565 -
完結510 章

改嫁總統后,假千金成團寵了!
【真假千金+團寵+閃婚+萌寶】大婚當天,許栩沒等來新郎,卻等來了未婚夫霍允哲和許雅茹的曖昧視頻。 她滿腹委屈,給遲遲未來婚禮現場的養父母打電話。 養父母卻說:“感情這事兒不能強求,允哲真正喜歡的是雅茹婚禮,趁還沒開始,取消還來得及。” 直到這刻,許栩才知道,得知她和許雅茹是被抱錯的時候,養父母和霍允哲就早已經做好了抉擇! 不甘成為笑話,她不顧流言蜚語,毅然現場征婚。 所有人都以為她臨時找的老公只是個普通工薪族。 就連養父母都嘲諷她嫁的老公是廢物 卻不想海市各方大佬第二天紛紛帶著稀世珍寶登門拜訪! “海市市長,恭賀總統新婚!送吉祥龍鳳玉佩一對!” “海市民政局局長,恭賀總統新婚,送錦緞鴛鴦如意枕一對!” “海市商務部部長,恭賀總統新婚,送古董梅瓶一對!”
59.8萬字8 3582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