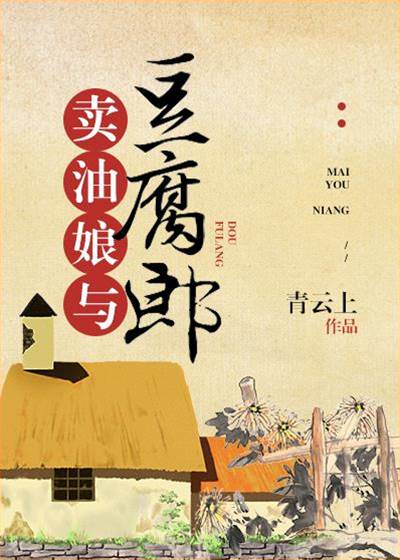《閨寧》 第418章 惹禍
他站在那,居高臨下地看著。
溫雪蘿哭得愈狠,一聲聲幾乎要不上氣來。淚水如同斷了線的珠簾,撲簌簌直往下落。亦不敢手去抹,只睜著眼小心翼翼覷著他的神,服求饒,連番辯解。
箭在弦上不得不發,已走到了這一步,就絕對不能輕易地再失去。肅方帝好,便做出可憐又招人的模樣來,纏上他的,像纏在樹上生長的藤蔓,一點點收攀援,告訴他,自己從沒有過旁的心思,先前的的確確只是不慎踩著了自己的擺,站不穩罷了。言畢,自有不住聲的誇起了肅方帝,贊他英雄氣概,贊他年輕英俊,贊他聖明……
可肅方帝雖然聽著,面上卻沒有太多變化,那張臉上的神舒緩了些許,可並沒有出愉悅用的模樣來。
溫雪蘿暗道不妙,只怕肅方帝已是認定先前那一跌,是有心圖謀,是在算計他。
既如此,眼下不論再如何辯駁,肅方帝也定然是不會相信的。心念電轉,驀地鬆了手,伏在地上哭著磕了兩個頭,弱聲道:「皇上,臣有罪……」
肅方帝聞言,倒覺得有趣了些,問道:「何罪?」
溫雪蘿哽咽著,又俯首磕了一頭,磕得額上紅了一片,輕聲說著:「臣不該膽大妄為,慕於您。」
「慕?」肅方帝眼神微。
溫雪蘿哭聲不止,只漸漸輕了下去,赤著子跪在他跟前,青瀉在後,似水一汪,倒現出人的艷來。
話音堅定地道:「是,臣初次見您,便已傾心於皇上……」
肅方帝聽得一愣,旋即哈哈笑了起來,面上霾終於一掃而,換做了一張笑臉。
這樣的子,他倒也還是頭一回遇見。
肅方帝上上下下打量著的子,終於道:「也罷,那件事便就此掀過不提吧。」
Advertisement
說完,他轉即走,並不多留半刻。
盯著他遠去的背影,溫雪蘿咬著牙哭了兩聲,終是將淚水囫圇咽了下去。
——既已失算,那便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了。
就這麼在宮裡頭留了下來,這一留就是許久。
宮宴已散,黃昏時分,眾人便已各自出了宮門。溫夫人則較眾人稍晚一步,因為還未見到自己的兒。之前在花園中,明明白白聽到宮人說,是惠和公主邀了溫雪蘿一同賞花。本以為過得片刻,二人便會回來。誰知,從這以後,便一直再不曾見到過兒。
甚至於到散了,也沒等到溫雪蘿回來。
溫夫人不起了幾分憂慮,求到了皇貴妃跟前去。
然而並不曾見到皇貴妃的面,坐在偏殿里等了約莫一刻鐘,仍只瞧見皇貴妃邊隨侍的姑姑從門外緩步走進來。見了便說:「溫夫人,娘娘方才吃了兩盞酒,這會不勝酒力,一時半會怕是不便見您。」
溫夫人聽著,不由暗自苦惱,因天漸晚,也不可能再宮裡長留,惠和公主那邊,更是無法打探,只得纏著眼前面目嚴肅的姑姑試探著問:「不知小眼下,可還在公主殿中?」
「自然是的,您且放心,娘娘已打發了人去永安宮問話,不消片刻便能請了溫二小姐來見您。」
溫夫人鬆了一口氣,笑了一笑。
吃著茶候著,過得須臾,外頭果真有了靜。
飛快地抬起頭來,以為是兒已至,然而誰知,來的卻並不是溫雪蘿。
仍是先前那位姑姑,了簾子進來,躬行了一禮,隨即道:「溫夫人可以先行離宮了。」
溫夫人聞言大吃了一驚,急急問:「姑姑此話可解?」明明是來等兒一道離宮的,這會卻可獨自先行離宮了?胡想著,道:「可是公主殿下,留了小說話?」
Advertisement
惠和公主過去便時常留了謝家的那個姑娘留宿,興許這一回同溫雪蘿聊得投趣,便也留了。
可這念頭還沒來得及在心中多停留一刻,站在一步開外說話的中年子,已徐徐開口給了重重一擊。
說,「溫夫人錯了,是皇上留了溫二小姐。」
溫夫人霍地站起來,目瞪口呆地看著來人,兩片皮子上下哆嗦著,問:「皇上?」
「正是皇上。」
轟的一聲,輕飄飄的四個字,像一道驚雷落在了耳畔。
溫夫人只覺自己兩戰戰,站立不穩,渾無力,眼前發黑,滿的話卻耐不住齒關閉,半個字也吐不出。
「天已晚,還請溫夫人早些離宮,一路小心。」
溫夫人木愣愣地聽著這話,兩眼無神地點了點頭,一步步往偏殿外頭走去。
原本明的天已逐漸暗沉,站在門口,驀地深吸一口氣加快了腳步,飛也似地逃離了這重重宮闈,逃回了英國公府。
一路上,溫夫人呼吸急促不穩,渾冷汗淋漓,幾乎的背衫。
馬車一在垂花門外停下,便匆匆往下走。
丫鬟來扶卻被一把用力推開。
一面走一面心神不寧地打發人去請英國公來說話,再三叮嚀,要快,再快些!
丫鬟得了令,疾步而去。
溫夫人先回了正房,憂心忡忡等著丈夫回來,額上汗珠越來越集。拿著塊素緞的帕子,反反覆復拭著,可這汗卻沒完沒了地往下滴,弄得愈發得心慌意。
驀地,門外響起了一陣急促的腳步聲。
猛地丟開了手裡的帕子,幾乎撲了過去,拽住方才進門的英國公,張兮兮地說:「國公爺,出大事了!」
英國公才剛剛打外頭進來,見狀不由得一頭霧水,皺著眉頭安地輕輕拍了拍的背,問道:「怎麼了這是?出門前不還都好好的嗎?」
Advertisement
「出門前是好好的,可這會卻真的是大事不好了!」溫夫人抓著他的胳膊不松,面惶恐,「蘿姐兒,……」
支吾著,卻又不知該從何說起。
英國公卻聽出來了兩分不對勁,扶著在椅子上坐下,追問:「怎麼了?」
溫夫人長嘆一聲,頹然鬆了手,將早前在花園中,溫雪蘿差點不慎摔跤,結果正巧被肅方帝扶了一把的事告訴了他。
「傷著皇上了?」英國公聽著,見神驚懼不安,眉頭鎖,急聲問道。
溫夫人卻連連搖頭,咬著牙說:「沒有,皇上把留在了宮裡!」
英國公登時面大變,重重一拍桌子,將上頭的茶震得「哐當」響,「胡鬧!你就這麼回來了?」
溫夫人見他生氣,抹著眼角哭道:「妾不回來還能怎麼辦?」
英國公又氣又驚,子往後一倒,一臉頹喪地落了座,唉聲嘆氣地道:「來不及了,事只怕已沒有轉圜的餘地了。」
近兩年,肅方帝做的荒唐事,說可真不。
他耽於,諸人皆知。
這一回,既是他將兒留在宮中,事焉還能有好?
英國公只覺得自己心頭似了一大塊石頭,沉甸甸的令人不上氣來。
他看一眼旁的夫人,嘆口氣:「且等等吧。」
今日想將兒接回來,是斷斷沒有可能的。他們只能咽了這口氣,等著宮裡頭下旨了。
英國公說著,面疲,惋惜不已:「同長平侯府的那門親事,雖則只是平平,可到底也比進宮強呀!」
「什麼親事?」溫夫人並不知此事,聞言不由訝然。
英國公站起來,搖搖頭:「長平侯林遠致,年歲上同蘿姐兒正合適,我原屬意於他,正準備等你回來今晚細細商討。也罷,事已至此,幸好我也只模糊地同其了兩分意思,並不曾請了人說合。」
Advertisement
然而想著肅方帝的品行,皇貴妃的強勢,東宮的太子,他這一顆心就忍不住高高吊了起來。
自己的兒他自己清楚,是個不肯安分的子。以皇貴妃的子,必不會容。
英國公十分擔心,溫夫人也沒好多。
夫妻倆長夜無眠,第二日卻並不曾等來任何消息。
無人來宣旨,甚至也無人來傳話。
英國公有些急了。
又過一日,事仍未有靜。
英國公心道再這麼等下去,只怕也是無用,便讓溫夫人宮求見皇貴妃去,好歹也問一問況。
溫夫人無法,時隔兩日再次宮,可這一回也不曾見到皇貴妃的面。
皇貴妃病了,不便見人。
溫夫人就這麼被打發了回來,夫妻倆人一商量,況這般糟,再不能繼續瞎等了。
兒沒名沒分地留在宮裡,既不是陪著娘娘公主,又不是宮中的宮人,這麼下去算是怎麼一回事?
英國公只得親自宮面聖,本已做好了見不著面的打算,不曾想肅方帝倒真見了他。
英國公便道,溫夫人病了,惦記小,想接了小回家侍疾。
瞧著眼下這靜,肅方帝本無意給溫雪蘿封號,他索也不去想,只盼著能將兒活生生地帶回家,已是極好。
可肅方帝聽了他的話,突然冷笑了起來,問:「怎地,怕朕吃了你兒不?」
英國公一聽這話苗頭不對,連忙跪倒忙說不敢。
肅方帝冷笑連連:「不敢?你都跑到朕跟前扯謊來了,你還有什麼不敢的?」
猜你喜歡
-
完結491 章

鳳花錦
仵作女兒花蕎,身世成謎,為何屢屢付出人命代價? 養父穿越而來,因知歷史,如何逃過重重追捕回歸? 生父尊貴無比,一朝暴斃,緣何長兄堂兄皆有嫌疑? 從共同斷案到謀逆造反,因身份反目; 從親如朋友到互撕敵人,為立場成仇。 富貴既如草芥, 何不快意江湖?
90萬字8 10800 -
完結536 章

傾城醫妃不好惹
一朝穿越,成了不受寵的秦王妃,人人可以欺辱,以為本王妃是吃素的嗎?“竟敢對本王下藥,休想讓本王碰你....”“不是,這一切都是陰謀....”
97.2萬字8 115582 -
完結492 章
穿越醫妃不好惹
穿越前,她是又颯又爽的女軍醫,穿越后,她竟成了沒人疼的小白菜,從棺材里爬出來,斗后媽,氣渣爹。夫婿要悔婚?太好了!說她是妖孽?你再說一個試試?說她不配為后?那我做妃總可以了吧。只是到了晚上,某皇帝眨巴著眼睛跪在搓衣板上,一字一頓地說天下無后是怎麼回事?
88.1萬字8 19935 -
完結14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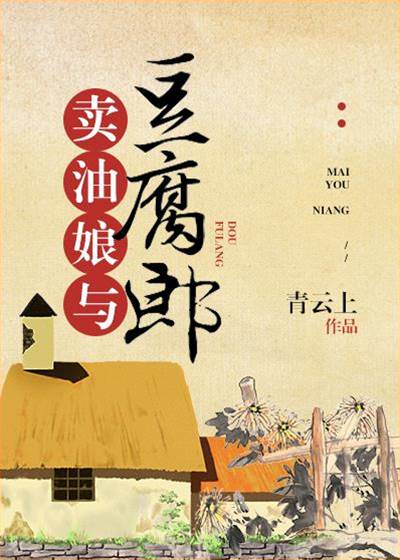
賣油娘與豆腐郎
每天早上6點準時更新,風雨無阻~ 失父之後,梅香不再整日龜縮在家做飯繡花,開始下田地、管油坊,打退了許多想來占便宜的豺狼。 威名大盛的梅香,從此活得痛快敞亮,也因此被長舌婦們說三道四,最終和未婚夫大路朝天、各走一邊。 豆腐郎黃茂林搓搓手,梅香,嫁給我好不好,我就缺個你這樣潑辣能幹的婆娘,跟我一起防備我那一肚子心眼的後娘。 梅香:我才不要天天跟你吃豆腐渣! 茂林:不不不
77.7萬字8 12345 -
完結257 章

春水搖
赫崢厭惡雲映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 她是雲家失而復得的唯一嫡女,是這顯赫世家裏說一不二的掌上明珠。 她一回來便處處纏着他,後來又因爲一場精心設計的“意外”,雲赫兩家就這樣草率的結了親。 她貌美,溫柔,配合他的所有的惡趣味,不管他說出怎樣的羞辱之言,她都會溫和應下,然後仰頭吻他,輕聲道:“小玉哥哥,別生氣。” 赫崢表字祈玉,她未經允許,從一開始就這樣叫他,讓赫崢不滿了很久。 他以爲他跟雲映會互相折磨到底。 直到一日宮宴,不久前一舉成名的新科進士立於臺下,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包括雲映,她脊背挺直,定定的看他,連赫崢叫她她都沒聽見。 赫崢看向那位新晉榜首。 與他七分相似。 聽說他姓寧,單名一個遇。
38.5萬字8.18 469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