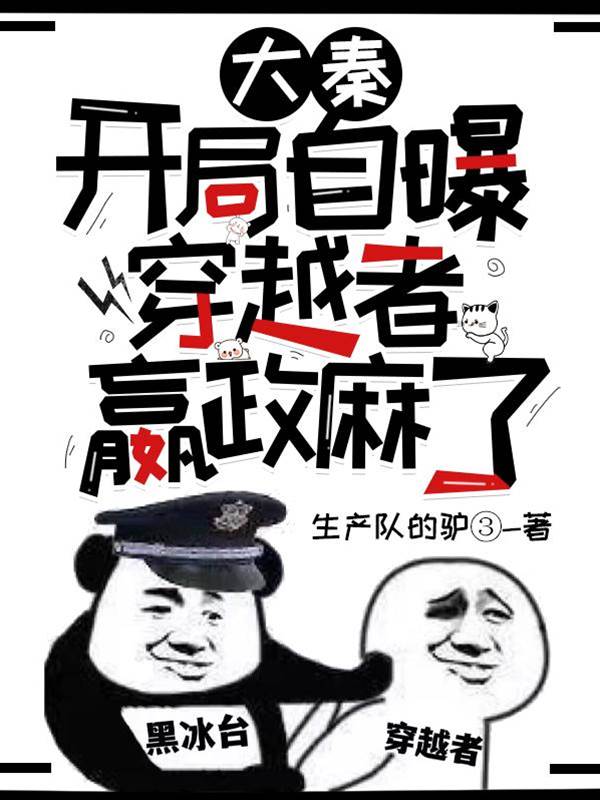《紹宋》 第六章 人心(續)
“非只如此,還有一事。”張浚駐足于空的府衙道旁,看了眼從后不遠的府衙,又了下前方數百步外人群聚集的那個路口,卻是搖頭嚴肅以對。“你知道今日早上韓世忠有個侍從來找我嗎?”
劉子羽即刻頷首:“剛剛憲臺找到我時還跟我說,幸虧韓世忠有心,沒讓那個侍從提昨夜召見之事,否則今日憲臺便要休了。”
“那你知道那個侍從找我到底說了什麼嗎?”
“請憲臺賜教。”上午艷之下,劉子羽多散了點之前的怨氣。
“那侍從對我說,韓太尉聽說家清苦,平素下面的人進貢些東西,一定要拿出來賞賜,以至于側連一些可用之都無,甚至有時夜間點蠟燭也都只點一……然后他在前方有些繳獲,想拿來進貢,又怕家不用,所以問我該如何應對?”
“必然是昨夜親眼所見。”劉子羽想到之前張浚的講述,也是陡然醒悟,繼而又是一嘆。“我也隨行在多日了,也聽到一些說法,但不料家真的如此清苦……”
“非只是清苦。”張浚愈發無奈。“彥修,你的眼界著實需要再高些……國難之時,誰不清苦?行在這里,半年發不了俸祿,不人卻拖家帶口,到淮南前一頓姜豉都當寶貝,不算清苦?便是你劉子羽剛剛安定了家人,便從東南趕來行在,匹馬行數千里,難道不算清苦?我只問你,你為什麼不覺得清苦?”
“我父自縊以赴國難,我二弟一家走的慢,夫人、三個兒子盡數死于中,國仇家恨,如何會在意什麼清苦不清苦?”劉子羽幾乎是口而出。
“難道家不是國仇家恨?”張浚再度嘆氣。
劉子羽環顧四面,眼見著一隊前班直披甲佩刀遠遠走開,方才微微皺眉:“天家也有此番誼嗎?更何況還有那番落井之蹊蹺事,聽說家自那之后,有為北面之事容,也不營救二圣,儼然與父兄不和。”
Advertisement
“東南都是這般傳的嗎?”張德遠明顯頓了一下。
“壽州大捷前,便頗有此類言語傳播,之后更是不,卻是往好的一面傳了,畢竟于東南而言,二圣又能有什麼好名聲呢?”
“這倒也罷。”張德遠不由松了口氣。“其實行在這里人盡皆知,家言語中對二圣確實頗為不敬,之前又是不許與金人議和,又是不許在興復兩河前談及勾還二圣之事。前些日子在路上更是說出了靖康之禍,在于二圣先天下而降……如此態度,東南有此言語也屬尋常。只是彥修,你想想,若非心存怨氣,又何至于此?而既然有怨氣,那多還是在乎的。只不過家在乎的卻未必只是某一人罷了。”
“這倒是有些道理。”劉子羽也深呼了一口氣。“靖康之變,實亙古未聞之恥,家因此有怨氣,有恨意,也屬尋常……不過,家有此勾踐之志,難道不是好事嗎?”
“是好事,卻也不是好事。”張浚連連搖頭。“這便是我要說的關鍵了。依我看,家專心于興復雪恥是對的,但若只有一個興復雪恥的念頭,其余事端都不去想又如何?你劉子羽國仇家恨,與金人勢不兩立,難道就不在意親眷家人、故鄉舊友了嗎?前幾日建州生,你不還向我詢問相關事端嗎?諸位行在大臣,誰又不想著自己階高一些呢?便是素來謙恭守和的呂相公,之前聞得李相公不來,不也順水推舟認了南?可家呢?”
“家……”
“呂相公對我說,家落井前、落井后,行事都極自私……可在我看來,家落井前自私無疑,可之后諸般行事,殊無私念,只是大公若私,又或是公私一,本難辨罷了。”張浚正言道。“一個證據便是,自從家落井之后,一意只在抗金興復,財貨、寶、子,乃至個人命皆拋之腦后。”
Advertisement
“也是。”劉子羽也是若有所思。“便如李伯紀李公相如今被留在東南,東南都說他有苦難言,因為家自將皇嗣、太后都托付于他,為臣子,除了鞠躬盡瘁又能如何呢?可反過來說,哪個天子會將的廢立權責托付一個臣子,還不是為了抗金?但……”
“但如此作為,哪里是一個二十歲人能得了的?”張浚終于說出了自己真正想表達的意思。“家太累了……之前李相公在時宛如木偶,壽州作戰時又繃到不行,而一旦西行又忐忑不安,生怕自己做不好。須知,你我二十歲時,何曾能擔天下于肩上?”
“可家畢竟是天子。”
“天子也是人,且當今這位天子,二十歲前只是悠游自在而已。”張浚愈發無奈。“你們這些人,只想著他是天子,覺得他該圣賢,卻不把他當個人看……一會來個強勢之人要他做木雕,一會來個老的嫌他抗金太過莽烈要他顧全大局,一會又來個莽撞的想著讓他英明神武。殊不知,你們若只一味這樣,將來天子一個繃不住,做回昔日南京(商丘)模樣,又是選浣,又是一力避戰的,你們又能如何?難道要將北面五馬山那個什麼信王或者揚州才數月的皇嗣推上去?韓良臣、張伯英能答應?!”
劉子羽微微皺眉,儼然不想涉這個話題,卻又不得不問:“所以,便要讓我留下,充實中樞?”
“不然呢?”張浚無奈苦笑。“眼下形,為臣子,總不能給家選妃,勸家理會國事,多曬曬太吧?唯一能為的,不過是盡量推薦人才,讓彥修你這般人留在家側,幫著家作規劃,讓家做事時生波折……”
Advertisement
劉子羽放聲一嘆,儼然是被說服了,卻還是忍不住微微氣悶起來。
“不管如何,如今天下安危其實都是系在這一位上的,家穩才能天下穩!”張浚苦口婆心。“我自己何嘗不想出去主政一方,做點大事?但最起碼要等到家這里徹底安頓下來,有了規制才行吧?”
劉子羽聽到這份上,只能勉力頷首不再多言。
且說,張浚此番言語,多有他自己臆測之論,而且為家私人,所謂文臣中頭號心腹,偏向家的立場擺在那里,便是劉子羽雖然這些日子與他相極好,卻也不是全然信他的。
不過,有一句話張德遠倒是一言道破了關鍵,那便是壽州大捷后西行至此的家明顯有些忐忑不安,明顯有些不知道該做什麼……這是理所當然的,因為趙玖從來沒認真當過一個正經家,也不知道該怎麼當一個家。
一過來,立即被幾個人隔絕,好不容易掙開束縛,便是坐在那里干等李綱,李綱來了當木偶,李綱病了以后正好憋到了極致,便去破罐子破摔跑到淮上倚仗韓世忠、張俊打了一仗……仗打贏了,這位趙家也收了心,照理說該好好當家了,然而一來道路不靖,南不能落地,大家也沒心思教家如何做事;二來壽州大戰多給趙家添了點彩,也不是誰都有膽量教他做家的,于是才有了眼下這種浮躁現狀。
而這,也正是趙家之前犯糊涂起意留下完銀可的一個重要原因,他似乎認定了抗金的‘正經事’就只有作戰,所以有些聞敵而喜。
回到眼下,趙家本人可能是因為愚鈍,又或者是因為在局中的緣故,倒是沒想這麼多,恰恰相反,這日他一覺黑甜睡到下午,便先收到了一個好消息,繼而振起來——無他,東京留守、天下兵馬大元帥府副帥、樞使宗澤又來奏疏了,而且奏疏的容讓人振。
Advertisement
宗爺爺這份札子里說的很清楚,州被他徹底收復了,京東東路的青州、濰州也是確定被金人放棄了,如今是個李的人占據著……總而言之,金人大規模撤軍以定局,只要趙家好生占據城池穩妥守備,那完全不用擔心完銀可,后者或許會繼續攻擊,但一旦不能得手,必然北走。
當然,信的最后不免再度詢問一遍趙家,到底來不來東京?
前半截的重要報且不提,只說后面這話中的客氣,幾乎讓趙玖喜極而泣……須知道,穿越過來整整大半年了,除去中間李綱當政那段時間沒發外,宗爺爺前后給他這位趙家發出了十二封邀請函,都是讓他回舊都安頓,平均每半個月一封。
而之前十一封,全都是國家大義和忠孝節氣,又是‘祖宗大一統之勢再難全’,又是‘已經給二圣修了小宮殿,家自來住舊宮’,每句話都在準確的著某人的脊梁骨,道德綁架用的太溜了,以至于趙家想解釋都難。除此之外,就是東京已經有了多多兵馬,有多多糧秣,正待家至此,整頓六師渡河北伐!
但這一次,這麼客氣的邀請,趙家還真是第一次見。
這說明了什麼?這說明經過壽州一戰,經過趙家戰后迅速而絕境的行,一路走到汝這里,那位此刻正駐守在正北面東京的當世第一帥臣終于開始有點信任他趙家了!
唯獨礙于臉面,所以還在梗著脖子繼續邀請罷了。當然了,七十歲的人了,傲一點完全可以理解。
總而言之,建炎二年的這個春天,對于整個天下而言,還是金國進一步昌盛、擴張,而大宋進一步萎靡和失控……畢竟京東兩路、京西、關西被掃,大面積損兵折將,各地士民紛紛南下,城市存儲被掠奪殆盡,而與此同時,堅持抗戰的河北幾座城市,卻在不斷被拔除。
不過,如果只論趙家和行在來說的話,眼下雖然還有些波瀾,可大略形勢卻還是向好的。
這主要是因為兵馬得到收集,人心也得到了一定凝聚,而且按照宗澤、韓世忠、劉子羽的言論來看,只要妥當應付,完銀可這里也不是什麼天大的問題,那麼屆時立南也就是眼可見了。
一個安穩的陪都對于行在上下的意義,不言自明。
往后幾日的形發展也大略如此,且不提外圍那些風風雨雨,只說行在這里,隨著趙家派出去的招人手,蔡州境的諸多潰兵、盜匪、義軍紛紛降服,然后統一接了行在的招安。
其中,雖然因為銀可向不明,所以韓世忠沒有著急下手統一整編,但眼見著地圖由敵域變己方疆界,所有人的安全都還是得到了顯著提升。
又過了一兩日,就連唐州、潁昌府都有好消息傳來——彼的各種獨立武裝,雖然沒有上來同意,但果然如劉子羽說的那般,本質上沒有拒絕的理由,卻多是猶豫觀。想來,隨著韓世忠與王德急速引軍進彼,或許他們也該下定決心了。
然而,就是這麼一日,三月初八上午,趙家正與新晉近臣劉子羽一邊下棋,一邊討論‘土斷’之事,卻忽然見到了一個意想不到的臣子。
“臣翰林學士林景默見過家!”小林學士氣吁吁、面慘白,由侍省大押班藍珪引,卻是甫一見到家便俯首相對,并說出了一番讓人頗為震的言語。“臣行到唐州比,便得到訊息,范致虛在南驚恐難耐,日前主要那駐守武關的宗印和尚出關救他,結果那趙宗印引數千兵出關,在南西北被金軍一支偏師輕松大敗,趙宗印自知罪大,本沒有回武關,也沒有去南,而是逃到襄投奔范瓊去了!武關十之八九,已經失陷!”
房檐下,趙玖著一枚棋子沉默了一會,居然沒有怒。
“如此說來……南豈不是不保?”倒是一旁早已經起避開小林學士的劉子羽口而出。“因為此番金人完全可以放心攻下南,然后從容從武關折返關西。”
趙玖依然沒有說話,只是有些無力……能說什麼呢?
韓世忠、宗澤、劉子羽,甚至自己和行在上下其他人都盡心盡力了,眼前氣吁吁的小林學士之前更是甘冒奇險,然而,還是頂不住一個作妖的和尚。
“家!”小林學士猶豫了一下,還是勉力再言。“劉晏去北面汝州找韓太尉了……他讓我回來務必要與家說,小心金人不去南,反而會趁勢來取汝!因為金人既然在西面有了后路,之前在北面汝州、潁昌府截斷金軍退路的布置反而累贅。”
趙家陡然抬頭,卻居然沒有太多慌之態:“朕,知道了。”
猜你喜歡
-
連載3173 章

重生萬歲爺
秦昊穿越了!不知道幾輩子修來的福分,竟然穿成了一國之君!可他還冇在喜悅中回過神來,便得知了一個殘酷的真相。原主是個徹頭徹尾的昏君,一直以來被那位宰相大人掌控,就連後宮佳麗都必須臣服於宰相女兒的威嚴。
271.8萬字8 102318 -
完結2629 章

從軍行
「近衛軍團何在,可敢隨我馳騁漠北疆場,馬踏燕戎王帳」 一個身披紅袍的將軍立馬橫刀,「願往」 身前的百戰之卒異口同聲的應答。 一個由小山村走出來的少年,從軍只為給家裡省點賦稅,只想攢錢娶青梅竹馬為妻,隨著軍功不斷,一步步陞官,大權在握之時卻山河破碎,城破國亡。 他登高一呼,起兵抗敵,他要建立一個屬於自己的王朝! 他要給自己心愛的女人一個天下!
559.3萬字8.18 53129 -
連載118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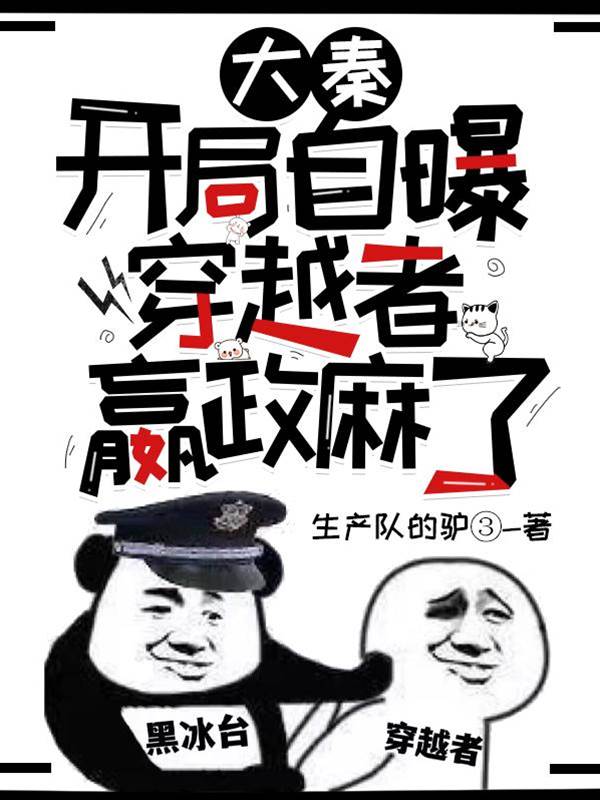
大秦:開局自曝穿越者,嬴政麻了
始皇帝三十二年。 千古一帝秦始皇第四次出巡,途经代郡左近。 闻听有豪强广聚钱粮,私铸刀兵,意图不轨,下令黑冰台派人彻查。 陈庆无奈之下,自曝穿越者身份,被刀剑架在脖子上押赴咸阳宫。 祖龙:寡人横扫六国,威加海内,尓安敢作乱犯上? 陈庆:陛下,我没想造反呀! 祖龙:那你积攒钱粮刀兵是为何? 陈庆:小民起码没想要造您的反。 祖龙:???你是说……不可能!就算没有寡人,还有扶苏! 陈庆:要是扶苏殿下没当皇帝呢? 祖龙:无论谁当这一国之君,大秦内有贤臣,外有良将,江山自然稳如泰山! 陈庆:要是您的贤臣和内侍勾结皇子造反呢? 祖龙:……谁干的?!我不管,只要是寡人的子孙在位,天下始终是大秦的! 陈庆:陛下,您的好大儿三年就把天下丢了。 祖龙:你你你……! 嬴政整个人都麻了!
247.2萬字8 916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