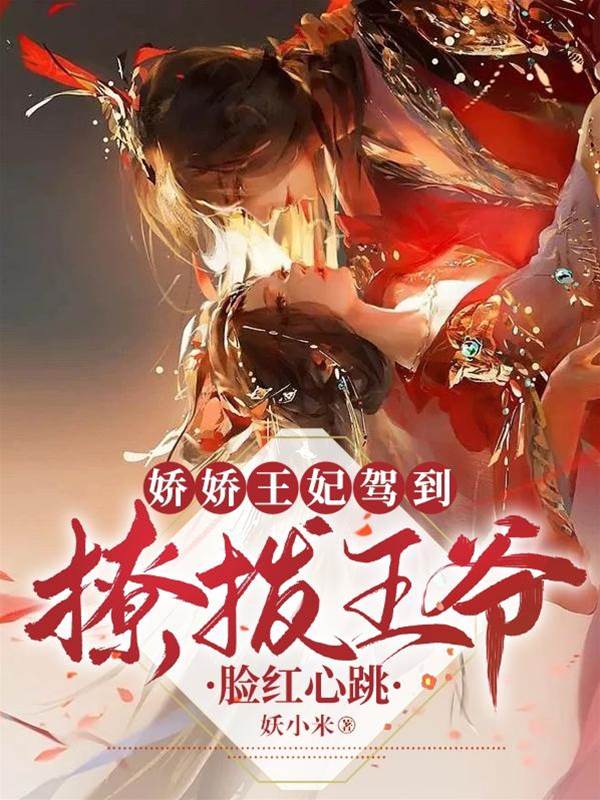《重生之庶女歸來》 第749章 深夜幽會何人
燕王朱棣迎出了王府,一雙鷹目盯著轎隊,確認是孟瑄本人來了,微微瞇起眼睛。
廖之遠跳到朱棣的邊,熱絡地為他介紹道:「王爺久等了,山貓幸不辱命!這位孟七將軍,王爺對他一定不陌生,前幾天剛兵不刃地收走了王爺的十八萬燕州兵。他哥哥孟三公子,日在朝堂上給王爺找氣生,比三個保定侯還難纏。這對兄弟,我全給王爺弄來了!」
何當歸眉心一跳,廖之遠說的這些事如此重大,卻一件都沒聽說過,看來有人故意對封鎖了消息,其中還包括皇帝。
廖之遠繼續道:「今天,總算讓咱們捉到把柄,他夫人清寧郡主公然行兇,傷害了一位善良無害的出家道姑。是可忍,孰不可忍?王爺,絕對不能放過他們!」一臉小人得志的古怪表。
何當歸倒覺得廖之遠是裝的。說不清為什麼,廖之遠給的覺,戲弄的分多過於敵意。
朱棣輕咳了一聲,責備廖之遠:「你這隻野山貓,開玩笑也不分場合,幸好孟將軍雅量容人,又深知你的脾氣,否則先拿你開刀。」
孟瑄微笑:「是啊,廖家大公子最出名的本事就是開玩笑,我不會生他氣的。」
「太好了,各位請。」
眾人開開心心進了府,後花園的涼亭長廊里擺了個臨時公堂,衙役、捕令牌、驚堂木,一樣不缺。朱棣溫和地解釋道:「清寧綁架和傷害陸夫人,大小算是一件案子,形式還是要走一遭的,否則會有史參奏本王偏私義。」
「王爺果然公道。」孟瑄致謝。
原告忘心從下轎開始就低垂著頭,沉默不語,臉還是很蒼白。
何當歸以一個大夫的角度看,覺得忘心與其來公堂爭一口氣,不如靜臥吃幾副葯,看忘心的況可能都撐不過一場堂審。可是不準備勸忘心,因為了解,鑽牛角尖的人是最難勸的。
Advertisement
哪怕再多的人證明,陸江北是因為練武才放棄了夫妻溫,並不是因為外面有別的人,鑽牛角的忘心也不會接。用自殘的方式來陷害「敵」,可以看出忘心是個很絕很自傲的人。能接敗給假想敵,卻不能接不戰而敗。
「那麼,開堂吧。」朱棣隨意地揮手,充當佈景板的衙役站兩排。朱棣也注意到忘心的出氣多、進氣,於是了一個綉墩給,請先陳述被害經過。
忘心幽幽回憶道:「我看見清寧郡主何當歸與一個男人,為了掩藏,將我捆綁,毒打我,還想殺我滅口。我上的傷痕就是明證,我的丫鬟和廖將軍、安寧侯段曉樓都親眼看見我被綁在何當歸床下,是最好的人證,何當歸本無從抵賴。」
朱棣聽后一臉驚訝,借口更,把孟瑄到了屏風后,用商量的口吻說:「撇去命案不談,先皇敕封的郡主行為不端,罰是嚴重的,不但要褫奪封號,還會被幽閉在皇家寺廟,下場凄慘。若本王知道本案中還摻雜了這個因素,是不會公開審理的。」
孟瑄淡淡道:「倘若審理之後不屬實,那麼該罰的人就不是郡主了。」
朱棣笑:「聽聞忘心居士從不說謊,不管怎麼看,都對郡主很不利啊。」
「或許吧。」
「如果將軍有心救郡主的話……」朱棣暗示地說,「本王可以暫且退堂,你我室敘話。」
孟瑄婉拒道:「多謝王爺意,我和清兒都激不盡,只怕陸夫人傷那樣,已等不了了。倘若案子還沒審完,先有個三長兩短,死不瞑目,我對陸大總管也難有代。」
朱棣聽得面一滯,心中的火氣騰起來,虧得皇室修養功課做得好才沒當場發作。
Advertisement
這時,段曉樓帶著兩個人趕來燕王府,其中一個是何當歸認得的蔣邳,也是錦衛中人。他兄長蔣毅是錦衛的叛徒,傳聞說蔣毅投了寧王朱權。
「快,你給大嫂療傷,你診脈!」段曉樓指揮著蔣邳和另一個大夫打扮的老頭。
蔣邳與段曉樓、廖之遠等人不同門派,他的暖真氣可以助人療傷,對普通人而言就是聖葯。忘心卻不肯讓蔣邳傳功,而理由卻讓所有人一愣:因為男授不親,子不能同丈夫之外的男子親近,療傷也不行。
段曉樓急道:「大嫂,你的傷再不治,命堪憂!」
忘心近乎冷酷地說:「生死有命,假如我活不過明日,那就是我命該如此。」
段曉樓駁不過,只有干著急。
旁邊的廖之遠過來,搭著肩膀,悄悄耳語道:「忘心說親眼目睹了何小妞昨夜會郎,嘿嘿,陸家宅院的外圍機關重重,不識機關的人縱然長翅膀也飛不進去。如果忘心所言不虛,那麼有嫌疑當何小妞哥哥的人,除了你,就是老高了。」
段曉樓忙道:「高絕被冰針釘在床上,睡得死死的。」
廖之遠故作訝異:「這麼說,那個無恥的夫就是你了!好啊,沒想到段你是這種人,說一套做一套,說自己已完全放下了,原來是騙人的!」
段曉樓氣得一肘將他搗開,罵道:「什麼夫?再不管好你的,我讓你變死貓!」伴隨這話,鋥亮的方天畫戟出現在段曉樓手中,一記橫劈,華璀璨,整個臨時公堂上的人都覺冷風颼颼而過。
「夫要殺人滅口!」廖之遠撲到蔣邳後,低聲威脅蔣邳說,「你見死不救的話,我把你的青樓相好的花名喊出來,讓大夥兒都聽個新鮮!」
Advertisement
蔣邳氣得咬牙:「你們訌,幹嘛牽扯上旁人?我也打不過段!」
廖之遠躲過段曉樓一記下盤攻擊,友好地循循善蔣邳:「你不是會使毒嘛,你哥哥的極品毒藥,沒送你一瓶兩瓶?」
蔣邳搖頭:「不幹,我不要得罪段,我家還和侯府做著生意呢。臭貓你走開,離我遠點,你青樓相好兒的名字我也能背出一長串,你威脅不了我!」
「靠,你走著瞧!」廖之遠見煽蔣邳失敗,更大聲地嚷嚷,「夫殺人滅口了!小侯爺惱怒了!」
何當歸天,好似什麼都沒聽見。
段曉樓只恨從前沒一碗啞葯,讓廖之遠變啞。打鬥之中,餘見何當歸無悲無喜的淡淡神,段曉樓心頭一,低聲喝罵廖之遠:「你再這樣,連兄弟都沒得做,我不是說笑的!」
「我哪樣了?」廖之遠一邊躲閃刀刃,一邊裝傻。
「你說我可以,但是不許說。」段曉樓將廖之遠抵在立柱上,一字一頓道,「清白如水,不容你公然污衊!」
廖之遠眨無辜的貓眼,道:「又不是小爺我說的,是我們的好大嫂,陸夫人當堂指證的。」貓眼觀察著段曉樓頹然和泄氣的樣子,廖之遠興緻尚好地說,「段小侯,你講點理好不好?別總撿柿子呀,有本事去一顆的。」
段曉樓收刀,看忘心,再看何當歸……他確實沒廖之遠說的那等本事。
外面鬧的靜這麼大,屏風后一起「更」的朱棣和孟瑄當然不耳聾。
朱棣無法說服孟瑄讓雙方各退一步,和和氣氣地室詳談。但聽到外面的哄鬧聲,朱棣並不急著出去,一直聽段廖二人鬧到頭、收場了,他才走出屏風,又驚又怒地責備他們:「你們兩個,何統、何統!你們,真是……」一副氣得無可奈何的樣子。
Advertisement
段曉樓愧疚地說:「我一時失控,將公堂弄得一團遭,讓王爺審不案子,請王爺降罪責罰。」
朱棣嘆道:「唉,好吧,就依你的意思,暫且擱置此案,另外罰你去城防營練兩個月的兵,不可進城,不能回家探親。」
段曉樓低頭道:「多謝王爺。」
廖之遠這次明白過來,段曉樓不是腦袋發燒,才在燕王府里刀槍地打人,而是故意要砸了這個公堂,讓燕王審不下去案子。看來段曉樓心中也很清楚,已嫁人的郡主如果行為放,玷辱了皇室名,是連天子都沒有理由赦免的一樁大罪。一旦落實,何當歸就會人唾棄,永不翻。
「唉。」廖之遠怏怏不樂,「段曉樓永遠是段曉樓,頭號獃子。」
這獃子以為能把全天底下的人都救過來嗎?很明顯,忘心與何當歸之間,有一個人是本救不得的。聰明如段曉樓,這一刻卻失聰了。所以錦府的人才公論,這天底下找不出第二個段曉樓。
「不必了!」
何當歸開口阻攔,「難得以公正嚴明而聞名朝野的燕王主持公堂,還是這一堂就審清楚,問明白吧。」否則公堂里的話傳開,不知會傳什麼樣子。到那時,連段曉樓都會被連累了名聲。
與同時喊出「不必退堂」的,是大步走出屏風的孟瑄。
孟瑄走到何當歸邊,牽著的手,轉對眾人微笑著解釋道:「全是一場誤會,先前之所以沒有說,是怕陸夫人聽后到打擊,撐不住。現在陸夫人已看過大夫了,我也可以說出實了——昨夜和清兒在一起的人,就是我。」
猜你喜歡
-
完結447 章

重生攻略,腹黑太子你別跑
被渣男賤女聯手欺騙,全家慘遭滅門的卿親親,重生回到了六歲時。 。爹娘捧在手掌心,祖母外公搶著疼,更有四個玉樹臨風的哥哥把她當成眼中寶,寵妹無下限。 。卿親親滿意:這才是天之嬌女應該有的生活! 。神秘筆者所寫話本風靡京城,無數貴女千金求一見。 。卿親親:錢我有的是,誰做點心好吃,我就跟誰見面。 。假閨蜜終於得到琴仙賞識,收為徒弟,喜極而泣。 。卿親親:跪下喊個師祖再說。
110萬字8 50954 -
完結102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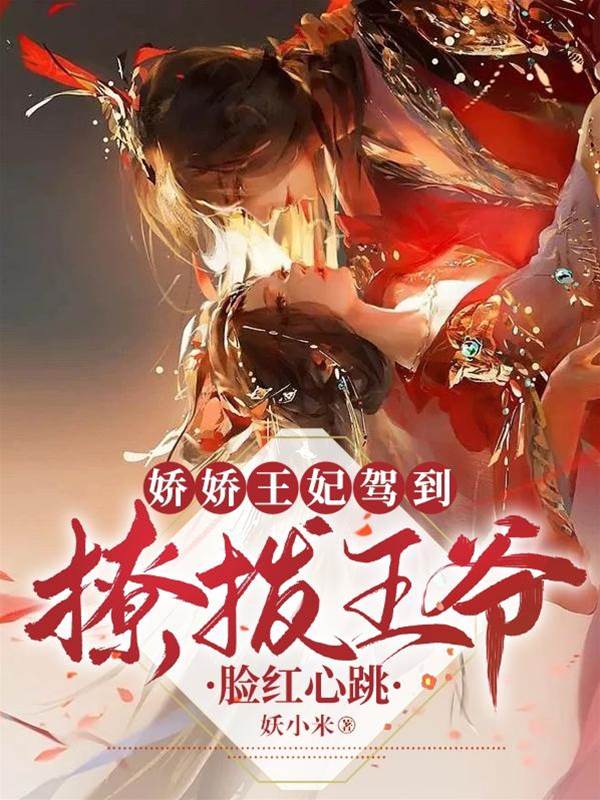
嬌嬌王妃駕到,撩撥王爺臉紅心跳
水洛藍,開局被迫嫁給廢柴王爺! 王爺生活不能自理? 不怕,洛藍為他端屎端尿。 王爺癱瘓在床? 不怕,洛藍帶著手術室穿越,可以為他醫治。 在廢柴王爺臉恢復容貌的那一刻,洛藍被他那張舉世無雙,俊朗冷俏的臉徹底吸引,從此後她開始過上了整日親親/摸摸/抱抱,沒羞沒臊的寵夫生活。 畫面一轉 男人站起來那一刻,直接將她按倒在床,唇齒相遇的瞬間,附在她耳邊輕聲細語:小丫頭,你撩撥本王半年了,該換本王寵你了。 看著他那張完美無瑕,讓她百看不厭的臉,洛藍微閉雙眼,靜等著那動人心魄時刻的到來……
183.7萬字8.18 101698 -
完結327 章

嬌骨
【閱前指南:甜寵雙潔爽文,有智鬥權謀,伏筆細節多,多人物刻畫,女主不吃虧,不理解的地方後期都會填坑,文風輕鬆是為方便閱讀】 宣王賀鈞廷。 《獨寵皇妃》這本書中,作者寫他屠盡北狄王庭,寫他披甲造反那一日連破十二城,寫他六親不認冷酷到骨子裏的薄情,寫他一生沒有所愛,最終像個煢煢孑立的瘋子頭也不回地走入了燃著大火的皇宮。*** 薛清茵穿成了這本書裏的驕縱女配,爹不疼兄不愛,重度戀愛腦,偏偏心上人對她棄若敝履,最後被迫嫁給風流魏王,夜夜守空房,結局淒慘。 她想了想,大膽點,不如選宣王! 反正這位死得早,她美美當有錢寡婦。 薛清茵嬌氣得很,進王府沒多久,就要賀鈞廷背她, 可以是可以,拿夜夜腰疼腿軟換的!哪裏還有什麼守空房? 不對啊。 這和我在書裏讀到的不一樣!說好的宣王其人冷酷寡情不近女色呢?*** 後來,薛清茵一躍成為禦前紅人,人人追捧,她的命運已改。她卻不想當寡婦了。*** 從此…… 你為我手中劍,我為你護心甲。 我們愛彼此不屈的靈魂。*** 宣王很早便知道她說喜歡他是假的,但無妨。 她是這個荒誕又醜惡的人間中,他們唯一的光。
75.2萬字8 2127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