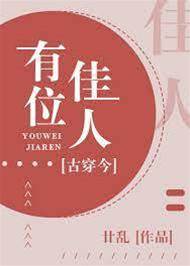《打死不離婚[ABO]》 78
“俞澄!”俞抒手著他的臉:“你再不禮貌,就帶你回去了?”
這幾年雖然沒看到徐桓陵和哪個Omega走得近,但是這不代表他真的沒人,俞澄問這話實在是太尷尬了。
俞澄撇撇,徐桓陵出沒有抱俞澄的那只手拉著俞抒被袖子遮擋的手腕,笑著說:“沒事。”
俞抒被徐桓陵拉著的手嗖的麻到了心臟,手指抖,吞了好幾次口水,才把手收回來揣在兜里。
“對不起。”俞澄糯糯的給徐桓陵道歉,一臉的討好:“我問了不該問的問題。”
“沒有不該問。”徐桓陵抱著他一邊走一邊耐心的和他解釋:“叔叔以前做了不好的事,所以我的Omega離開了。”
“他不會再回來了嗎?”
俞抒和徐桓陵同時一愣,徐桓陵臉僵了一下,搖頭說:“不會了。”
“別難過。”俞澄在徐桓陵臉上吧唧一口:“你要是不嫌棄,我讓我爸爸做你的Omega,他雖然沒你這麼溫,但是做飯還是不錯的。”
“俞澄!”俞抒覺已經控制不住想揍這個小崽子了。早上還讓俞抒得流眼淚,現在又讓人管。
徐桓陵倒像是毫不在意,笑出了聲,俞澄的腦袋說:“你爸爸要是愿意,叔叔沒意見。”
“我不愿意!”俞抒說。
意料之中的答案,徐桓陵沒有說什麼,抱著俞澄推開主樓的門走了進去。
保姆早就聽到靜,已經開始在往桌子上端早餐了。徐桓陵把俞澄放在椅子上,給他系好圍兜,彎腰問他:“先喝粥還是吃包子,廚房還包了湯包,很好吃。”
“吃包子!”俞澄抄起筷子先叉了一個包子放在面前的碗里,嘟著小吹熱氣。
Advertisement
徐桓陵在他旁邊的位子上坐下,給俞抒盛了一碗粥:“你是喜歡先喝粥是嗎?”
俞抒點點頭,在俞澄的另一邊坐下,低著頭接過徐桓陵的粥。
徐家的飯廳空了,當年的主位和兩邊的位子都空著,偌大的餐桌上只有三個人,顯得特別冷清。
粥還是以前的味道,可是喝到里淡如白水,俞抒心里生出一說不清,卻很抑的覺。
很多事還是一樣,很多事,又不一樣了。
吃到一半,俞澄嚷著要上廁所,俞抒本來想帶他去,可是想想自己在這里已經不是主人了,只好讓徐桓陵帶他去。
曾經,似乎也不是。
徐桓陵帶他去了自己房間的衛生間,沒有去一樓給客人用的。
衛生間里沒有準備俞澄用的小凳子,徐桓陵只好掀起馬桶圈,扶著他站在馬桶上,幫他子。
俞澄不好意思的捂著,對徐桓陵笑了笑:“徐叔叔你不可以看我,我是Omega。”
徐桓陵被他逗笑了,轉過頭去說:“我不看你,你快尿吧。”
俞澄尿完,徐桓陵又抱著他洗手,俞澄一邊沖著水,一邊往鏡子里看了一眼,驚訝的說:“徐叔叔,你看,我們兩是不是特別像!”
徐桓陵抬頭去看鏡子,瞬間就像是過電一樣愣了。
徐桓陵只穿了襯西,第一顆扣子隨意的開著,俞澄也穿了白的薄,被徐桓陵抱在懷里睜圓了眼睛看著鏡子。
鏡子里的兩個人一眼過去,確實是出奇的相似,特別是鼻子,幾乎一模一樣,哪怕俞澄還沒長出鮮明的廓,也能看得出來。
俞澄眼睛很大,像俞抒,可是型和臉型,和俞抒就不大像。倒是有些像……,徐安菱小時候。
Advertisement
徐桓陵心頭巨震,抱著俞澄的手止不住的抖。
或許只是,巧而已,小孩子的長相,怎麼能說得準。
“等你長大了就不像了。”徐桓陵勉強笑了一下:“小時候很多孩子都長得像。”
“我上和你還有一樣的味道,所以我特別喜歡你。”俞澄不在糾結于長得像不像,沖完手讓徐桓陵把你自己放下來。
徐桓陵恍惚的拿巾給他手,聞見了俞澄上的松木香,帶著點兒甜,腦子里一團麻。
俞澄對著徐桓陵勾了勾手指,小聲:“徐叔叔。”
“怎麼了?”徐桓陵湊過去。
“叔叔,我告訴你一個,你要幫我保哦。”
“什麼?”徐桓陵沒覺得他有什麼大,只是覺這孩子實在是太可了。
俞澄故作神的往門口看了看,沒看到人,才著聲音說:“我告訴你,其實我現在三歲零一個半月了,我爸爸騙你的。”
【作者有話說:上一章的結尾那句,網頁上改樂,七八糟的,我已經重新改了,等審核呢,大家暫且無視哈。
徐總:……,我震驚了,這是我的孩子啊。
俞澄:是的呀,父親!
俞抒:不是,滾!俞澄,你這個叛徒!
眾人:徐總這個,木魚,把朕的木錘拿過來,我要敲木魚!】
第79章 真相
徐桓陵彎著腰,像是被定了一樣,腦子一片空白,眼前一陣陣的發黑。
三歲零一個半月,那俞澄就是十二月份出生的。再往前推,如果孩子是九個月就從俞抒肚子里取出來的,那俞抒懷孕的時候,就正好是三月。
那是俞抒離開的時候。
如果是十個月的孕期,俞抒二月份本不可能懷孕,那是俞抒換腺前后。
Advertisement
徐桓陵像是找不到自己的呼吸一樣,好不容易找回了思考的能力,啞著嗓子問俞澄:“你怎麼肯定自己不是兩歲半?”
“反正就是!”俞澄說:“叔叔你信不信我?”
徐桓陵非常想相信,迫不及待。可一個小孩子的話,予兮讀家徐桓陵還不敢冒這個險。一旦這件事確定,那就是天翻地覆的變化。
太了,徐桓陵努力讓自己克制,讓空白的腦子轉起來,了俞澄的臉說:“你先下去吃東西,叔叔也尿尿。”
俞澄嗯了一聲,自己跑出去了。
徐桓陵關上門,扶著洗漱臺蹲在地上,捂著四年來早已經冰冷的口,大口氣。
如果俞抒真的有了自己的孩子,還把他生了下來,怎麼還能信誓旦旦的說要放他走,怎麼能讓他一個人養孩子,塉土讓俞澄一輩子都沒有父親。
章栩他不是俞澄的父親。
徐桓陵的心全了,抑了四年的瘋狂的折磨著心臟。
如果俞澄真的是自己的孩子,就算俞抒和章栩在一起了,起碼能留下俞澄,能留下一樣和俞抒共有的東西。
徐桓陵打開冷水把頭進去,用冷水讓自己冷靜下來。
說不定俞抒沒和章栩在一起,如果他連孩子的事都是騙自己的話。
徐桓陵努力想著這件事問誰最可靠,得出了三個答案,沈漣、俞瀚和齊舫。為了穩妥起見,徐桓陵決定三個都問。
沈漣最近不在國,那就先問俞瀚,齊舫經過曾經的事,早就已經恨了自己,他能不愿意說,或是會提前把自己找他的事告訴俞抒。
徐桓陵整理好緒下樓,把自己全然偽裝什麼都不知道的樣子。
吃過早飯,徐桓陵出去打了個電話,然后帶俞澄去三樓,陪他看了部卡通電影,又帶著他在后院逛了一圈。
Advertisement
整個過程俞抒形同虛設,一直都是跟在后面,徐桓陵也沒敢和他多說話,怕一說話,就暴自己的心。
元昇接到徐桓陵的電話,就買機票馬不停蹄的去了國外,去俞抒曾經留學的地方。
今年暖冬,現在快過年了,也沒再下雪,天氣很適合放風箏。
徐桓陵陪俞澄放了一個下午的風箏,讓廚房準備了晚飯,吃過之后才送俞抒和俞澄回去。
“叔叔再見。”中午沒睡覺,俞澄有些困了,被俞抒抱著一直打哈欠。
“再見。”俞抒彎腰親了親他,頭發蹭到俞抒,俞抒趕往后退了兩步。
俞抒驚慌的偏過頭去,問徐桓陵:“你還不走嗎?”
“我和你哥說幾句話。”徐桓陵說:“你帶俞澄去洗澡吧。”
俞抒抱著俞澄上樓去,俞瀚才問徐桓陵:“有什麼事?”
“去書房說吧。”
俞瀚的書房只有他一個人用,把門關上之后,其實俞瀚心里已經覺到徐桓陵要問什麼了?
“俞澄很可。”徐桓陵開口說。
俞瀚心里噔的一聲,想著怎麼回話。
“他和徐安菱小時候特別像。”徐桓陵又說:“鼻子有些像我。”
這種不直接說重點的對話方式,讓人本不知道怎麼接話,接錯了就相當于自底細。
“你要問什麼直接問吧。”俞瀚在沙發上坐下。
“俞澄是不是我的孩子?”這次徐桓陵直奔主題,直勾勾的盯著俞瀚,分析他是不是說謊。
徐桓陵發現是遲早的,畢竟俞澄那麼黏他,而且他們長得那麼像,怎麼瞞都是瞞不住的。
俞抒的這個,俞瀚當初說過要永遠保守,不能讓徐桓陵知道,可是現在俞瀚想想,俞抒就要和章栩結婚了,瞬間覺得這個沒有任何保守的價值。
徐桓陵再可惡,再不是人,或許也比章栩好些,至徐桓陵敢作敢當,也勇于認錯,而章栩,總給俞瀚一種心機很深,又很極端的覺。
“是。”俞瀚嘆了口氣說:“徐桓陵,你應該知道,我也不怎麼喜歡你,這件事,我本來是不想告訴你的。”
“那現在又為什麼告訴我了?”徐桓陵得到肯定的答案,有些站不穩,扶著書桌慢慢到地上坐著,本控制不住自己的表,一會兒一臉冷漠,一會兒又傻笑。
“因為俞抒在和章栩談結婚,他為了不讓你知道俞澄的世,為了不再和你糾纏,選擇了和章栩結婚。”
猜你喜歡
-
完結212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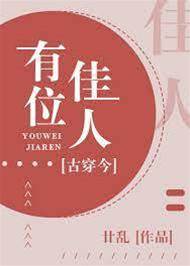
有位佳人[古穿今]
沈嶼晗是忠勇侯府嫡出的哥兒,擁有“京城第一哥兒”的美稱。 從小就按照當家主母的最高標準培養的他是京城哥兒中的最佳典範, 求娶他的男子更是每日都能從京城的東城排到西城,連老皇帝都差點將他納入后宮。 齊國內憂外患,國力逐年衰落,老皇帝一道聖旨派沈嶼晗去和親。 在和親的路上遇到了山匪,沈嶼晗不慎跌落馬車,再一睜開,他來到一個陌生的世界, 且再過幾天,他好像要跟人成親了,終究還是逃不過嫁人的命運。 - 單頎桓出生在復雜的豪門單家,兄弟姐妹眾多,他能力出眾,不到三十歲就是一家上市公司的CEO,是單家年輕一輩中的佼佼者。 因為他爸一個荒誕的夢,他們家必須選定一人娶一位不學無術,抽煙喝酒泡吧,在宴會上跟人爭風吃醋被推下泳池的敗家子,據說這人是他爸已故老友的唯一孫子。 經某神棍掐指一算後,在眾多兄弟中選定了單頎桓。 嗤。 婚後他必定冷落敗家子,不假辭色,讓對方知難而退。 - 新婚之夜,沈嶼晗緊張地站在單頎桓面前,準備替他解下西裝釦子。 十分抗拒他人親近的單頎桓想揮開他的手,但當他輕輕握住對方的手時,後者抬起頭。 沈嶼晗臉色微紅輕聲問他:“老公,要休息嗎?”這裡的人是這麼稱呼自己相公的吧? 被眼神乾淨的美人看著,單頎桓吸了口氣:“休息。”
49.8萬字8 8185 -
完結115 章

出獄之后我懷了渣男的種
三年前,一場大火,兩個人。枕邊人和心頭肉,靳東陽毫不猶豫選擇把枕邊人沈念送進了監獄。沈念在獄中一天天的挨日子,日日夜夜,生不如死。半個月後,沈念莫名其妙的大出血。命都丟了一半。三年後,沈念出獄。沈念勢不再做枕邊人,一心逃離靳東陽。可偏偏踏在雲頂之上的人,卻揪著他不肯放手。出獄前的一場交易,讓沈念肚子裡意外揣了個種。靳東陽得意的笑:是我的種,你得跟我。沈念悶悶的想:有種怎麼了?老子自己養。 斯文敗類豬蹄攻x誓死不做枕邊人受。
29.6萬字8.18 1158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