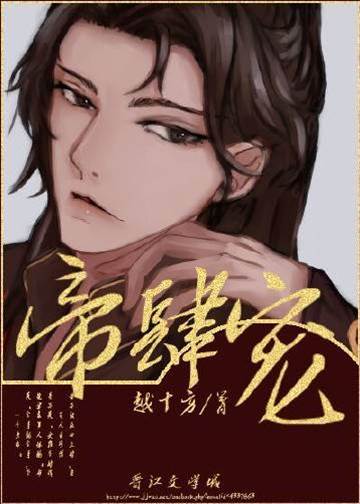《表哥萬福》 第33章 屠龍
黑人心有不甘,想要勸他:“主……”
“陳叔,一頭惡龍出爪牙殺了人,你說有罪的是惡龍本,還是殺了人的爪牙?”
周令懷低頭翻手中的書冊,他側臉蒼白削瘦,著令人心碎的病態之有種難以言喻的俊秀矜貴,垂下的眼睫很長,在眼底投了晦地淡影,令人捉不。
陳叔神變得復雜難言,握了手中的劍柄,手背上青筋跳,五指關節泛白。
“只因出手是惡龍一只爪牙,所以斬掉惡龍一只爪,就算報仇?你右手殺人,我斬你右手,這就是報仇?”他邊浸潤了一冷意,邪肆,墨一樣眼眸中,一片暗無天:“我卻不是這樣認為,殺人償命,天經地義。”
“殺人償命,天經地義”這個八字,呧著他的舌尖,被他放在里慢慢地咀嚼,令人心中膽寒。
頭頂上傳來平靜的聲音,宛如深潭般毫無波瀾,卻仿佛正醞釀著洶涌的暗,黑人猛然抬頭,腦中陡然浮現了“屠龍”二字,眼神中震驚、愕然、復雜、激各種緒不一而足。
周令懷淡聲問:“你覺得呢?”
黑人努力平復了心的震驚,腦中迅速分析了局勢:“自從三年前幽州驚變后,朝中的局勢越來越張,皇上沉迷丹,不常臨朝,朝政把持在閣、及威寧候等一干勛貴朝臣之手,朝臣們結黨營私、中飽私囊、貪臟枉法,勛貴們橫行無忌,跋扈囂張,各地藩王也是蠢蠢。”
Advertisement
說到這里,他話鋒略微一頓,抬眼看了主一眼,見主手里握著書卷,似是沒聽到他的話。
但是他知道,主在聽。
“滄州、梁州、云州也不大安穩,東夷、西戎、南蠻履犯大周邊境,與鎮守三州的藩王履履戰,每有損傷,三地藩王苦連天,履次上疏奏明皇上,請皇上派兵馳援。”
“聽聞年前,梁州平王奉昭京,當著滿朝文武的面兒,哭得一臉鼻涕一臉淚,說梁州苦寒,連稅都收不上,每年大小戰爭不計其數,打仗要錢、要糧、還要兵,他軍中的將士,已經三年沒換過兵甲,向皇上索要錢糧。”
提起這個,黑人語氣似有不屑,堂堂一地藩王,手握重兵,竟然連臉也不要了。
“你以為他們是在哭窮?”周令懷輕址了下角,輕輕合上了書冊:“他們哭的是命,誰哭得最難看,最不要臉,最窩囊,就最讓人放心,才不會步上幽王的后塵,他們倒是聰明,有仗打、有損傷、還窮,這樣的藩地才是某些人最希看到的。”周令懷語氣里充滿了諷刺。
黑人愣了一下,赫然明白了主的意思。
四州藩王鎮守大周邊境,本就為了守衛疆土,有仗打才有存在的必要,有損傷,還窮,朝庭才不會擔心藩王屯兵自重。
Advertisement
而幽王鎮守北境,常年與北狄戰,是四州最為苦寒之地。
北狄是大部族,狄人個個人高馬大,擅騎、擅、擅戰,每年秋季便會到邊城燒殺劫掠,鎮守幽州的幽王不得已才會大量屯兵,沒想……
周令懷微瞇了下眼:“能放得下尊嚴,連臉面都不要了,就說明他有所圖謀,且所謀甚大,大到連尊嚴也不值一提,甚至能將自己丟失的尊嚴,加倍討回來。”
黑人呼吸一滯:“主,您的意思是,平王……”
周令懷打斷他的話,聲音冷厲:“派人盯梁州。”
“是!”
虞窈帶著春曉和冬梅快步離開,忍不住想,那個黑人表哥“主”,對表哥也十分恭敬,不像平常家仆。
表哥他,似乎很神的樣子?
而且表哥還提起了威寧候府。
近幾日,對京里各府也有一些了解,威寧候府最為人津津樂道的是,家中出了一位皇貴妃。
這位陸皇貴妃,在皇上還在潛䣌之時,就被封了側妃,從此之后榮寵不斷,一路寵冠后宮,至今隆寵未衰。
因皇后娘娘有恙,后宮印也是由陸皇貴妃代為執掌,宮中一應事務也都由陸皇貴妃執理,陸皇貴妃在后宮里頭,是一手遮天。
做為外戚的威寧候府,也是京里頭最顯赫的人家,沒有之一,遠非虞府可以比擬。
Advertisement
虞窈約意識到,大約可能也許在無意間,撞破了一個關于表哥的驚天大?!
表哥突然進京,住進了虞府,肯定不會是投奔親戚這麼簡單。
春曉見小姐回來后,手里拿著花枝,抿著一言不發,一直悶頭往回走,有些奇怪:“小姐,你剛才怎麼跑到假山背面去了,奴婢都瞧不見你了。”
乍一沒見小姐的影兒,和冬梅嚇得差一點魂飛魄散,好在姑娘及時回來了。
想到方才驚險的一幕,虞窈也有些心有余悸:“假山背面的花,開得更漂亮一些。”
春曉連忙道:“這外頭不比府里,小姐以后可不行這樣。”
虞窈心不在焉地點頭,也不敢再到走,回到了廂房,坐了一會兒,覺得房里頭有些悶,領著春曉和冬梅去了禪房。
一路上奇石、疊山、理水,著寧靜大氣,地上都是磨出花紋的青石磚,兩旁種著常青菩提。
不大一會兒,虞窈就聽到不遠有誦經聲,禪房到了,守在外面的青袖迎了上來,領著虞窈進了其中一間禪房。
屋里頭不大,里只擺了桌椅,顯得十分空曠,四足博山香爐散著檀香味,丫鬟、婆子垂手站在兩旁,虞老夫人半靠著紫圓壽字彩錦引枕。
另一旁,還坐著一位圓臉老婦人,穿著墨藍繡金五蝠紋褙子,頭上戴著祖母綠抹額,頭發已經灰白了泰半,瞧著比祖母還要年長一些。
Advertisement
虞窈反應過來,這個老婦人,是鎮國候府的老封君宋老夫人,也是祖母閨中時期的閨友,恭敬地上前行禮問好。
宋老夫人將虞窈到跟前,握著的手:“過年那會子,我記得窈窈穿了一紅彤彤的石榴花子,圓乎乎地,瞧著一團喜氣,”說著忍不住笑:“這才不到一個月,就出落了大姑娘了,我記得窈窈還得兩月才十歲。”
ps:大表哥的心機浮出水面!
猜你喜歡
-
連載3575 章

錦鯉棄婦:隨身空間養萌娃
一覺醒來,安玖月穿成了帶著兩個拖油瓶的山野棄婦,頭上摔出個血窟窿。米袋裡只剩一把米;每天靠挖野菜裹腹;孩子餓得皮包骨頭;這還不算,竟還有極品惡婦騙她賣兒子,不賣就要上手搶!安玖月深吸一口氣,伸出魔爪,暴揍一頓丟出門,再來砍刀侍候!沒米沒菜也不怕,咱有空間在手,糧食還不只需勾勾手?且看她一手空間學識無限,一手醫毒功夫不減,掙錢養娃兩不誤!至於那個某某前夫……某王爺邪痞一笑:愛妃且息怒,咱可不是前夫,是『錢』夫。
322.4萬字8.08 312726 -
完結8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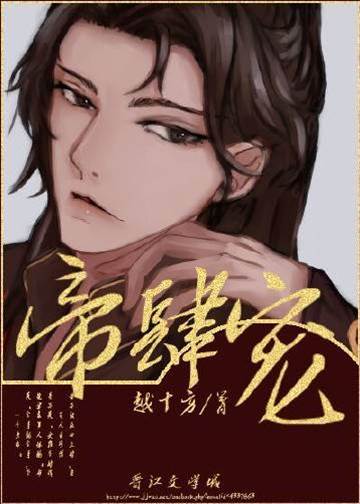
帝肆寵(臣妻)
從軍六年渺無音訊的夫君霍岐突然回來了,還從無名小卒一躍成為戰功赫赫的開國將軍。姜肆以為自己終于苦盡甘來,帶著孩子隨他入京。到了京城才知道,將軍府上已有一位將軍夫人。將軍夫人溫良淑婉,戰場上救了霍岐一命,還是當今尚書府的千金,與現在的霍岐正當…
28.8萬字8 26481 -
完結451 章

歡恬喜嫁
前麵七世,徐玉見都走了同一條路。這一次,她想試試另一條路。活了七世,成了七次親,卻從來沒洞過房的徐玉見又重生了!後來,她怎麼都沒想明白,難道她這八世為人,就是為了遇到這麼一個二痞子?這是一個嫁不到對的人,一言不合就重生的故事。
81.3萬字8 15674 -
完結532 章
醫庶無雙
原主唐夢是相爺府中最不受待見的庶女,即便是嫁了個王爺也難逃守活寡的生活,這一輩子唐夢註定是個被隨意捨棄的棋子,哪有人會在意她的生死冷暖。 可這幅身體里忽然注入了一個新的靈魂……一切怎麼大變樣了?相爺求女? 王爺追妻?就連陰狠的大娘都......乖乖跪了?這事兒有貓膩!
103.5萬字8 19342 -
完結206 章

賠罪
施綿九歲那年,小疊池來了個桀驁不馴的少年,第一次碰面就把她的救命藥打翻了。 爲了賠罪,少年成了施綿的跟班,做牛做馬。 一賠六年,兩人成了親。 施綿在小疊池養病到十六歲,時值宮中皇子選妃,被接回了家。 中秋宮宴,施綿跟在最後面,低着頭努力做個最不起眼的姑娘,可偏偏有人朝她撞了過來,扯掉了她腰間的白玉銀環禁步。 祖母面色大變,推着她跪下賠禮。 施綿踉蹌了一下,被人扶住,頭頂有人道:“你這小姑娘,怎麼弱不禁風的?” 施綿愕然,這聲音,怎麼這樣像那個與她拜堂第二日就不見蹤影的夫婿?
33.9萬字8.18 406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