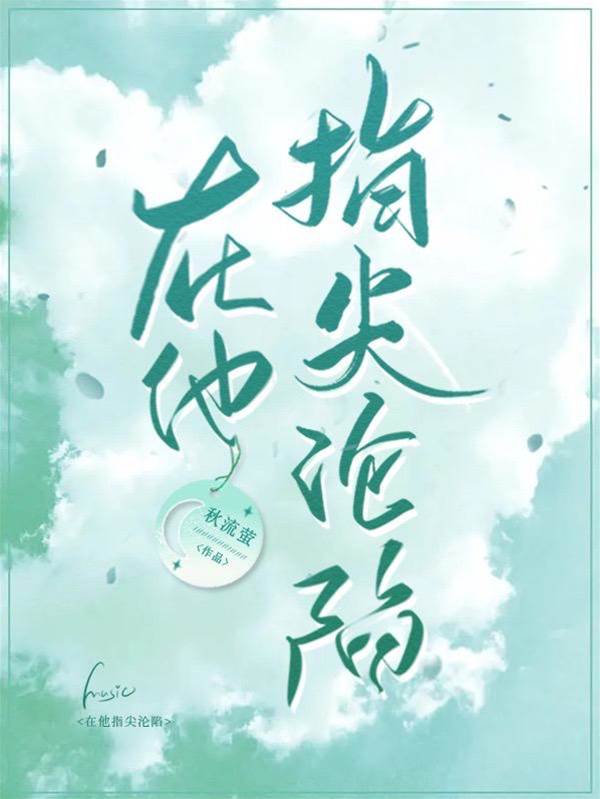《春風一度共纏綿》 第148章 我們是什麼關系?
我先給徐至打了個電話,我失蹤兩天,他一定快急瘋了。
從陸承北的別墅逃出來,我雖然帶了手機,但是已經被周錦文的手下搜走了,所以現在只能用好心大叔的手機打。
幸好徐至的電話我已經爛于心,所以很輕松就能鍵。
“嘟,嘟……咔噠。”電話很快被接通。
“誰啊?”
是徐至的聲音,顯得有些不耐煩,他似乎正在忙著其他的事。
“徐至,是我。”
我趕出聲,聽筒立馬安靜了。
大概停頓了有兩秒,徐至似乎才認出是我。
“安安?安安!真的是你嗎,安安,你在哪兒,安不安全,這兩天怎麼都沒聯系我,那天在會場之后你去了哪兒,我哪里都找不到你,打你手機也是關機,擔心死我了!你……”
徐至一如既往的聒噪倒是讓我心中的不安消散不,我趕讓他打住,“徐至徐至,你冷靜一點,我現在沒事。”
“那你在哪兒,安安!”徐至這麼說的時候,還帶著些微的哭腔,估計真的是急壞了。
反而變我在安他,“我現在沒事啦,不過有個地方要去,你一個小時后過來接我。”
我報上陸承北別墅的地址,和徐至約在那里。
徐至似乎只要聽到我安全的消息他就已經很滿足了一樣,也沒有問我去那個地方要干嘛,只是囑咐我要注意安全,所有的事等見到他再說。
我本來想給陸承北打電話的,后來想想,有些事不當然說的話,本說不清楚。
因為大叔開的是大貨車,不能直接進市區,所以就在環城路上把我放下來。
我本來想給他留錢,但是他不要。
老實說,也許是因為我的經歷使然,讓我不能輕易地相信別人。
Advertisement
在這麼倒霉的時候還能上一個好人,我說不定真的要轉運了。
陸慕舟塞給我的錢足夠打車去陸承北的別墅,我在去之前順路給自己買了雙底鞋。
因為從周錦文那里逃出來的時候,跑太快我丟了一只鞋,總不能一腳穿一腳沒穿這樣去見陸承北吧。
上的服也稀稀拉拉的,我索全上下都換了套行頭。
坐在前往陸承北家的計程車上,我莫名有種自己是去接頭的錯覺。
陸慕舟拜托我的事,我就盡力去試試,就當是報答他一直以來對我的好,以及放我離開的恩,從此,我們便可以兩不相欠。
此時天已經完全暗了,算一算,差不多是陸承北日常回家的時間。
現在宅子里估計已經套,我逃走的事,不知道陸承北會怎麼理。
如果看到我自己乖乖又送上門去,又會怎麼想。
車子停下后,我將上最后一張鈔票丟給司機,示意不用找了。
下車,看著燈火通明的宅邸,我莫名有些不自在。
從外面看不出里面是什麼況,很安靜,安靜得詭異。
深吸一口氣,我斂了斂心神便上前摁響門鈴。
“可以啊,程安安,這麼多人都看不住你。”
陸承北好整以暇地坐在沙發上,幽幽說著,角帶笑,但眼里一點溫度都沒有。
我不咽了一下口水,他生氣了。
不過我不是回來認錯的,我是來和他談條件的。
“你既然走都走了,還回來自投羅網做什麼?你是不是不得離開這里,離開我嗎?”陸承北的語速不急不緩,但他的目仿佛蛇一般纏上我,要將我纏撕碎一樣。
“我來找你說正經事的。”
開門見山,我直接在他對面坐下。
Advertisement
陸承北挑眉,他擺了擺手,將其他人屏退,而后盯著我的眼睛,問道,“你要和我說什麼事,有關陸氏的?”
陸承北的覺果然十分敏銳,我還沒切正題,他就自己先提了出來。
見我面尷尬,他又接著問了一句,“你見過他們了對嗎?”
“你說的‘他們’,是誰啊?”
故意繞個彎子,我不能讓陸承北掌握主權。
但是我這麼問,陸承北本來還算好的臉卻突然沉了下去。
“想和我打馬虎眼是嗎?”陸承北說著就站了起來,直接走到我面前,居高臨下地看著我,“安安,我有那麼可怕嗎?”
“……”這個問題還真的不好回答,不是他可不可怕的問題,而是我不喜歡他對待我的這種方式。
“不回答,好。”陸承北微微頷首,而后忽然俯,雙手撐在沙發上,將我圈住。
“你要干嘛!”我本能要退,但已經在沙發椅背上,退無可退。
陸承北微微瞇起眼睛,一字一句說道,“看來你還有些不明白,我和陸氏的事,不需要你手。”
“你以為我想手嗎!”陸承北的語氣仿佛是在怪我多管閑事,我本來還以為他會就我跑的事和我算賬,但是他就提了一句,卻馬上將話題轉到陸氏的問題上來。
我莫名心里十分不爽,因為有種不被重視的覺。
“程安安,你在玩火你知道嗎?”
陸承北說著就慢慢朝我俯下來,我下意識將頭撇向另一邊,“在玩火的人也許是你呢?”
“哈。”陸承北輕聲一笑,我以為他會親下來,但是他突然起,雙手也離開沙發,幽幽轉回對面坐下,搭起二郎對我擺了個手勢,“你想說什麼,說吧。”
Advertisement
“……”真不知道陸承北這是在唱哪一出,不過我也不想再和他這麼繞下去,便直接對他說,“產的事,你能不能放棄?”
“你給我一個理由。”
陸承北老神在在,似乎還真的打算好好聽我說。
我現在的確是陸慕舟的說客,不過讓陸承北放棄的理由,難道要說他不放棄,周錦文會發瘋嗎?
陸承北一聽還不樂瘋了,周錦文對他可一點不友好,他會走到今天,某種意義上還是周錦文的。
所以,我只針對自己的立場,理直氣壯地對他說,“你不放棄,我會有困擾。”
“哦,你會有什麼困擾?”
陸承北的咄咄人,讓我有些不自在,但我還是卯著子回道,“你不放棄,陸家人會一直找我的麻煩。”
我這麼回答,也算是很實誠了。
然而陸承北卻笑了起來,他幽幽看著我,冷不丁問了我一句,“你有困擾,我就得放棄,你說說,我們是什麼關系?”
被陸承北將了一軍,我瞬間啞口無言。
“我不同意放棄,如果你覺得會有麻煩,就留在我邊。”攤了攤手,陸承北耐人尋味地看著我,“你可以自己選。”
“……”我無語地著他,陸承北這是在我,可如果不能讓他放棄,我即使留在他邊也沒有什麼意義,說不定還會更麻煩。
就在我不知道該如何回答的時候,門口忽然傳來一陣。
我看過去的時候,大門剛好被踹開,徐至風風火火闖了進來。
他一看到我,兩眼立馬發亮,但在看到陸承北的時候,瞬間板起臉,一臉戒備。
“安安,你沒事吧?”徐至趕將我拉到他邊,警惕地盯著陸承北,“他沒怎麼你吧?”
Advertisement
徐至一來,我莫名松了口氣,“我沒事。”
“你是不是想囚安安?我告訴你,門兒都沒有!”徐至一上來就給陸承北一個下馬威,陸承北站起來,臉漸沉。
“安安,我們走!”沒給陸承北回答的機會,徐至說完就拉著我往外走。
“攔住他們!”陸承北命令一起,外面就圍過來幾個人,徐至簡直要氣炸了。
“陸承北!你不要太過分,安安已經和你沒關系了,我這次就帶回國,永遠都不回來!”
我從來沒見過徐至如此生氣過,他撂倒了幾個保鏢后,就拉著我往外跑。
跟演電影一樣,上車后我們就狂飆起來,徐至這舉仿佛是把我從狼窟中救出來的一般,一刻不敢停留。
但是很快我就從后視鏡里看到后面有車子追上來了,直到此刻我才有些后悔一沖就來找陸承北的行為。
他果然不肯輕易放我走,雖然說得好聽更讓我自己選擇。
他既不會放棄陸氏財產,也不會讓我離開他,陸承北怎麼就這麼霸道呢!
“安安,來之前我已經將手續都辦好了,我們回去取行李,馬上走好不好?”
徐至一邊飆車一邊對我這麼說,他的臉不太好。
其實我也是這麼想的,只是覺得對不起徐至,畢竟他現在會陷被車追的困境都是因為我。
而且回國是因為我想回來,現在走也是因為我有了麻煩,徐至似乎從來不為他自己考慮。
“徐至,我本來就想和你說這件事,與其在這座城市重新制造不愉快的回憶,我不如直接離開這個地方。”
聽我這麼說,徐至才變得有些高興,“那這次說定了,可不準再反悔了。”
有些無奈地對他笑笑,我點頭,“不反悔了,我……啊!”
就在我想說以后一直和他一起生活也可以的時候,徐至忽然打滿了方向盤,車子瞬間往左邊極速轉去。
離心力拉扯了我一下,將我后半句話給生生憋回去。
在頭暈目眩的同時,我聽到徐至咒罵了一句。
“該死,從哪里又生出一輛車,真是魂不散!”
猜你喜歡
-
完結1175 章
霸愛成癮:穆總的天價小新娘
一場空難,她成了孤兒,他也是,但卻是她父親導致的。八歲的她被大十歲的他帶回穆家,本以為那是他的善意,冇想到,他是來討債的。十年間,她一直以為他恨她,他的溫柔可以給世間萬物,唯獨不會給她……他不允許她叫他哥,她隻能叫他名字,穆霆琛,穆霆琛,一遍遍,根深蒂固……
183.4萬字8 184203 -
完結2167 章

許你萬丈光芒好
“你救了我,我讓我爹地以身相許!”寧夕意外救了只小包子,結果被附贈了一只大包子。婚后,陸霆驍寵妻如命千依百順,虐起狗來連親兒子都不放過。“老板,公司真給夫人拿去玩?難道夫人要賣公司您也不管?”“賣你家公司了?”“大少爺,不好了!夫人說要把屋頂掀了!”“還不去幫夫人扶梯子。”“粑粑,謝謝你給小寶買的大熊!”“那是買給你媽媽的。”“老公,這個劇本我特別喜歡,我可以接嗎?”陸霆驍神色淡定“可以。”當天晚上,寧夕連滾帶爬跑出去。陸霆驍!可以你大爺!!!【雙潔歡脫甜寵文】
196.3萬字8.33 198235 -
完結395 章

公關的品格
公關——一個智商與情商雙高、掌握著企業生死的職業。失業記者卓一然轉型成為一名戰略公關,在變化無常的商業競爭中,靠著自己敏銳的新聞嗅覺與聰明才智,一次次為世嘉集團化解危機,也在公關部的職場變遷中,一步步從菜鳥成長為公關精英……
89.8萬字8 42588 -
完結10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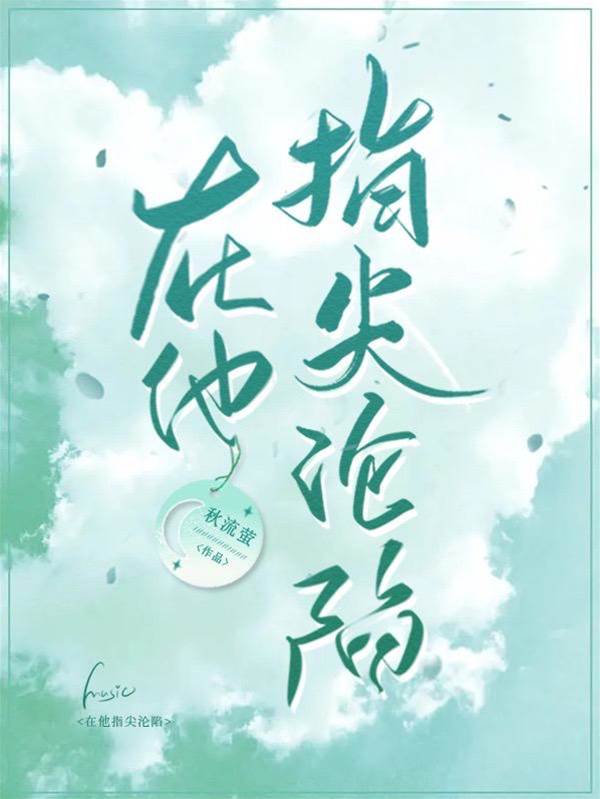
在他指尖淪陷
沈黛怡出身京北醫學世家,這年,低調的母親生日突然舉辦宴席,各大名門紛紛前來祝福,她喜提相親。相親那天,下著紛飛小雪。年少時曾喜歡過的人就坐在她相親對象隔壁。宛若高山白雪,天上神子的男人,一如當年,矜貴脫俗,高不可攀,叫人不敢染指。沈黛怡想起當年纏著他的英勇事跡,恨不得扭頭就走。“你這些年性情變化挺大的。”“有沒有可能是我們現在不熟。”-宋清衍想起沈黛怡當年追在自己身邊,聲音嬌嗲慣會撒嬌,宛若妖女,勾他纏他。小妖女不告而別,時隔多年再相遇,對他疏離避而不及。不管如何,神子要收妖,豈是她能跑得掉。 -某天,宋清衍手上多出一枚婚戒,他結婚了。眾人驚呼,詫異不已。他們都以為,宋清衍結婚,不過隻是為了家族傳宗接代,那位宋太太,名副其實工具人。直到有人看見,高貴在上的男人摟著一個女人親的難以自控。視頻一發出去,薄情寡欲的神子人設崩了!-眾人皆說宋清衍高不可攀,無人能染指,可沈黛怡一笑,便潦倒萬物眾生,引他墜落。誰說神明不入凡塵,在沈黛怡麵前,他不過一介凡夫俗子。閱讀指南:久別重逢,身心幹淨,冬日小甜餅。
20.2萬字8 20418 -
完結344 章

離開後,小叔悔不當初
【追妻火葬場 先虐後甜 雙潔 HE】薄肆養了她10年,卻在一天晚上喝醉酒闖入她閨房。意濃之際,他喑啞著開口,“我會負責”。桑田滿心歡喜,憧憬和他攜手共度一生。他卻牽起了白月光的手,一度要步入殿堂……她一直以為他是迫於形勢,他是身不由己,可他對她十幾年的關懷備至是真的。直到有一天,她聽到他和他母親談話……她才意識到一切都是謊言,是他從一開始就布的一個局。迷途知返,她藏起孕肚離開,搖身一變,成了海城第一豪門最尊貴的公主。……再次相見,薄肆看到她懷裏的兩個小女娃和站在她身後英俊挺拔的男人頓時紅了眼眶。他將人堵在衛生間抵著牆,不可一世的男人也會低頭,聲音哽咽,“孩子我不介意,跟他離婚,孩子我養。”
62.6萬字8.33 2023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