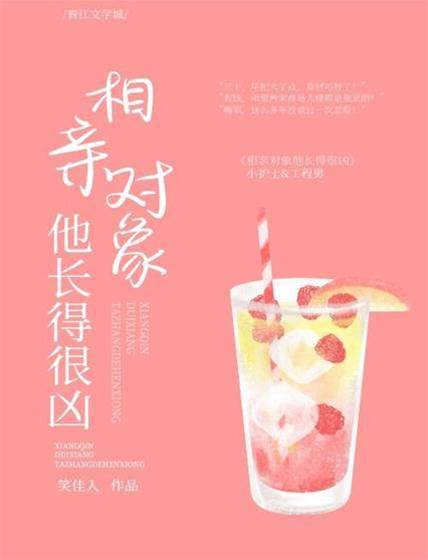《反派同窗他命帶錦鯉》 第87章
姜嶙正于茫然狀態, 猛然一聽聞硯桐有辦法,立即湊了過來,“你說什麼辦法,快告訴我。”
“你別著急, 聽我細細跟你說。”聞硯桐道,“你現在被關在這里,到時候府的人找來, 他們能帶你逃走是最好, 若是沒能逃走, 你絕無生路。”
姜嶙似乎能想象到聞硯桐話中的嚴重后果,連聲音都抖了, “那我該怎麼辦?我、我不想跟他們一起……”
“你現在去跟外面的人說,你愿意接他們做他們的老大, 然后跟他們共同議事。”聞硯桐道。
“不不!”姜嶙當下急道,“我不可能跟他們同流合污, 我不想謀逆!”
“不是你謀逆,而是你需要打部,幫助府,里應外合擊潰他們。”聞硯桐降低了聲音, 循循善道, “這正是你表真心,立功的時候啊。”
姜嶙愣了一下,“我做應?”
聞硯桐道,“你想想, 你父親培養的這群私兵能耐不小,還能盤踞在山頭上,從行宮里把你救出來,屆時府來了,約莫也要與他們惡斗一場,若是你在這時候幫助府把這些反賊都抓起來,可不就是立大功嗎?”
姜嶙道,“但是我、我不知道怎麼去幫助府。”
聞硯桐微笑道,“你放心,你現在只要取得他們的信任就好。你跟他們說自己想通了,皇家害你抄家,殺你父兄,得你顛沛逃命,你必要復仇反擊。”
姜嶙瞪眼,“我怎能說這般大逆不道的話!”
聞硯桐嘖了一聲,“只是演戲而已,你要讓他們相信你有復仇的決心。姜嶙,你若想活命,就必須拿出十十的演技,若是被他們看出了端倪,你也沒有活路的。”
Advertisement
姜嶙聽得渾抖,背上已出了一的虛汗,聞硯桐的話一直在耳邊打轉,讓他手腳冰冷。
聞硯桐聽他沉默了,便沒再說了,心道說這些應該也夠了。
昨夜池京禧告訴,要想辦法勸姜嶙假意歸順這些面人,擊碎這個嚴的組織,若是從外面撞,要費很大的力氣,但是里外夾擊,事就會簡單很多。
的話已經說得這樣明白。姜嶙若是不答應,最后也只有被死,因為姜家私兵這個組織最后的結局就是被擊潰,只有幾個活著逃走了。
但若是姜嶙答應了,并且在這件事上立了功,那他的結局就不好說了。
時至今日,聞硯桐投在這個故事里之后,已經不在乎自己能改變多事了,反而是想盡辦法去改變他們的結局。
姜嶙作為文中的一個小炮灰,他能不能改寫命運,全在他自己的一念之間了。
他在另一邊猶豫考慮了很久,最后下了決定,對聞硯桐道,“我若是在此事上立了功,真的能活下來嗎?”
聞硯桐對這個問題猶豫了一下,說實話也不知道。
但是想到昨夜池京禧的話,便點頭,“一定能的,我以小侯爺的名義擔保。”
昨夜池京禧說的,若是姜嶙答應做應,便可有一條生路。
姜嶙道,“好,我愿意假意歸順他們,聞硯桐,知道這件事的只有你,我能相信的也只有你,你可一定不要毀約。”
聞硯桐堅定道,“我不會的。”
到了姜嶙的孤注一擲,有也些為之容,便道,“不過你放心,你并不是一個人,留意左肩上系紅繩的人,他是府的應,你可以信任。”
“左肩上系紅繩?”姜嶙疑道,“什麼樣的紅繩?是不是很明顯?”
Advertisement
聞硯桐照著池京禧的話復述,“反正跟其他人的不一樣,你仔細看就是了。”
姜嶙將的話默默記下,然后起喊來了面人,表示自己想通了。
面人當即去請示了頭領,不過一會兒就有人折回來打開了門,將姜嶙放了出去。
他趁夜被劫出來,還沒見過這個盤踞地的真正模樣,先東張西了一番,而后被領著走過大半個鎮子,忽而傻眼了。
道路兩邊來回巡邏的面人左肩上竟然都系著一紅繩,一眼去,姜嶙只覺得全部都一樣。
他認真看了許久,愣是沒找出與眾不同的那個,心口憋著一口老。
接下來的時間,就剩下聞硯桐一人了,沒有了姜嶙在隔壁啰嗦的聲音。且自那夜以后,池京禧也沒再來過。
飯還是照常送,雖然飯食簡單,沒什麼好吃的,但是聞硯桐也不挑,頓頓都吃的飽飽的,保證自己的力和神。
只有要上茅房的時候才會被人放出去,但也有人看守,偶爾能瞟幾眼這里的模樣,其余的時間都在小黑屋里關著。
一連幾日,都被鎖在房中,由于擔心池京禧和傅子獻的安全,所以時間過得非常煎熬。
但總安自己,這些姜家兵的結局已是固定的,不可能有翻的機會,現在只有耐心等待,等府的人勘測好地形,在周圍布好埋伏,就能夠行。
所以要沉住氣。
可不巧的是,傅子獻突然出事了。
這日有個小年輕給聞硯桐送飯,多問了一句,“你上沒帶什麼值錢的東西吧?若是帶了就趕出來。”
聞硯桐剛接過飯碗,聽到這話,立即把飯碗放在地上,把懷里的銀票,腰上的玉佩,頭上的簪子一并遞了出去,佯裝諂笑道,“這是我全的家當了,就這些,大哥你全拿走吧。”
Advertisement
那小年輕見如此果斷利索,愣了一下,而后順勢把東西都接了下來,說道,“你還是聰明點的,不像那個,都被打的站不起來了。”
聞硯桐一下子意識到他口中的“那個”指的有可能是傅子獻,于是神猛地一變,“你說什麼?那個怎麼了?!”
小年輕不滿的看一眼。
聞硯桐立即掩飾自己的失態,出假笑,“大哥,你說的是傅家的爺嗎?我與他有些,所以想問問他出什麼事了。”
那小年輕收了的東西,破例多了兩句,“我們頭想從他上拿走一塊玉牌,他死活不讓,當場起手來,如此不知好歹,當然讓好一頓教訓,如今在床榻上躺半日了,死活難料。”
聞硯桐驚得嗓子都有些抖,“可他……不是傅丞相的兒子嗎?你們頭為什麼要對他手?”
小年輕嫌問得太多,惡聲惡氣道,“這與你何干,識相點就老老實實呆著,什麼話也別說,不然下一個就是你!”
聞硯桐只好沒再問,待他走了之后,這一頓飯吃的極其不安寧。
傅子獻不應該那麼死腦筋才對,他又不是牧楊,怎麼可能不懂變通,為一個玉牌被打這樣?
端著飯在屋中急得團團轉,
難道這個玉牌對他來說有特殊意義?
是他娘留下的?
可就算如此,等這些人被府抓住之后,玉牌也是能要回來的啊,他為何這般固執?
聞硯桐百思不得其解,印象中的傅子獻不該如此,他很聰明的,雖然子有些靦腆。
匆匆將一碗飯吃完,忽而意識到自己不能再干等著了,必須要做點什麼,不然池京禧也有可能傷。
于是在面人來收碗的時候,攔住了那人,低聲說道,“這位大哥,能不能幫我帶一句話給你們領頭人?”
Advertisement
那人莫名其妙的看一眼,似乎不想理會,轉要走,聞硯桐又道,“清泉映蘆花。”
那面人一聽,當下震驚的看一眼,整個人震住了。
聞硯桐只擺了副高深莫測的模樣,“快去。”
面人連忙跑出去,連碗都忘記收了。聞硯桐有些忐忑在房中等了一會兒,就聽見門外再次傳來腳步聲。
立馬站得端正,保證自己神深沉,不端倪。
門被推開,一個材高大的人大步進來,臉上的面是紅的,對著聞硯桐上下打量。
聞硯桐就站著不,眼眸像是攏著寒霜,盡量學著池京禧的樣子,用冰冷的眼神看他,讓人捉不。
也不知道自己學了幾分,僵持片刻之后,那人率先開口,“這話是你說的?”
聞硯桐便接口道,“清泉映蘆花。”
紅面道,“清泉可有水?”
“清泉沒有,墨池有。”聞硯桐道。
這是姜家兵十分的暗號,只有幾個領頭人才知道。姜家人在皇室安排的有應,但是一直沒有與這群私兵有接,唯一一點只有這句暗號。
當初從書中讀到,姜家兵被府擊潰之后,逃出去的幾個人之中,只剩下一個領頭人,而且被姜家的應找到了,書中特地寫了他們對暗號的場景。
只是那是發生在后來的事,聞硯桐意識到自己該做些什麼的時候,便把這句暗號掏出來。
這是很冒險的舉,若是稍有不慎,就會被掉腦袋,不確信自己能夠獲取十分的信任,但是只要有五六分,就足夠了。
那紅面見對上暗號,也沒有立即相信,只是有些質疑道,“為何會抓至這里?”
“這要問問你自己手下的人了。”聞硯桐鎮定道。
“那又為何一早不說?”紅面又問。
聞硯桐道,“沒有必要,我不想暴份。”
“現在有必要了?”
聞硯桐皺眉,“你們做了蠢事,我不想被你們連累。”
紅面知道指的是傅子獻一事,沉默片刻道,“已經罰過了。”
聞硯桐氣勢一下子兇起來,“罰有什麼用!你可知我為了取得他們的信任費了多大的工夫!”
紅面冷冷的看,“并不妨礙他對你的信任吧?”
聞硯桐也沒被嚇到,冷笑一聲,“你們貿然行,讓我的計劃功虧一簣,如今還上趕著找死,若非顧念姜大人恩,我大可撇清關系讓你們自生自滅。”
紅面沉默,隔了好一會兒才道道,“你想如何?”
聞硯桐聽他如此說,當下松了一口氣,知道他這是初步相信了,了一把手心里的冷汗,聲音依舊平靜,“我要見姜爺。”
猜你喜歡
-
完結211 章

神醫狂婿
因一場意外失去了全部的記憶,曾經呼風喚雨的風雲令主跌下神壇,淪為豪門贅婿,受盡奚落淩辱,一忍就是三年……這天在機緣巧合下,雲紋墨戒衝破了第一層封印,恢復了部分記憶的秦風,終於迎來了曙光,開啟了逆襲之旅……秦風因何失憶?雲紋墨戒又為何會被封印?這背後究竟有什麼驚天秘密……平時忍氣吞聲的「窩囊廢」,究竟會上演什麼樣的傳奇人生?天下風雲出我輩,一入江湖歲月催。皇圖霸業談笑中,不勝人生一場醉……
38.3萬字8 304463 -
完結6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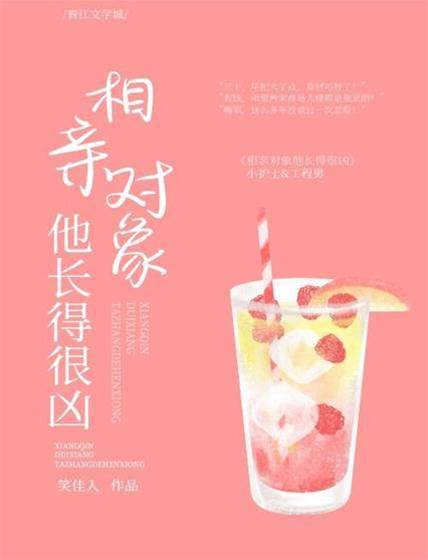
相親對象他長得很兇
江桃皮膚白皙、面相甜美,護士工作穩定,親友們熱衷為她做媒。 護士長也為她介紹了一位。 「三十,年紀大了點,身材可好了」 「有錢,市裡兩家商場大樓都是他家的」 「嘴笨,這麼多年沒談過一次戀愛」 很快,江桃
20.8萬字8.57 43724 -
完結185 章

歸德侯府
韋氏王朝太元十二年,吏部尚書家中嫡長孫重傷了當朝歸德侯幼子。 次月,吏部尚書許家的嫡次孫女許雙婉,定給了歸德侯長子宣仲安為妻。 歸德侯府被皇帝不喜多年,許雙婉被家族與父母放棄,代兄行過淪為棄子,為堵悠悠眾口入了滿門病殃子的歸德侯府。 從此,四面楚歌的許府二姑娘為了活得好一點,不得不走在了一條遇神殺神、遇魔滅魔的路上,身後還緊跟著一個比她還心狠手辣的病秧子丈夫。
68.5萬字8.18 28828 -
完結125 章

朝暮為歲
轉學第一天,周歲迷路了。她隨手推開路邊腸粉店的店門,靠門邊身著一中校服的男生一邊扒拉盤里的腸粉,一邊給迷路的她打開手機導航。不幸的是,她還是遲到了。更不幸的是,剛見過面的腸粉同學也遲到了。——而且好像是因為她。直到和他走進同一間教室,并且在相鄰的兩張課桌椅落座時,周歲的愧疚感油然而生,主動向那位「腸粉同學」兼「現任同桌」表達一下友好。“陳昭。”那人冷淡又疏離,丟下兩字,悶頭往桌上一趴。——睡覺去了。*南城大學的宿舍里,室友聲情并茂地大聲朗讀論壇熱帖—— 「撈一名計科院大一新生,超級無敵帥。」周歲壓根沒當回事。直到兩年沒見的人重新出現。陳昭把人壓在南大超市的貨架前,指尖一挑,勾起她想要的最后一包餅干,低聲求她:“能不能讓給我。”周歲慫得一逼,轉身逃跑。直到某日——室友拉著出現在操場,揚言要親眼看到那位帥名遠揚的計科院學弟。然而她心心念念的帥氣學弟,伸著手將一瓶未開封的礦泉水遞到周歲面前,問:“學姐,請問你要喝水嗎?”周歲在室友“窮兇極惡”的眼神下拒絕了。那人卻得寸進尺,將擰開瓶蓋的水重新遞過來,語氣溫柔又貼心:“幫你擰開了,喝不喝?”*夜幕暗沉時分,有人敲門。周歲毫無防備地開門,撲面而來的酒氣和靠倒在她肩上的男人驚了她好一會兒。隨即天旋地轉,頭頂的水晶吊燈在她眼中換了個方向。意識回籠,她跌坐在陳昭的腿上,才明白過來,那人在裝醉。“答應我。”他語氣近乎誘哄。她不敢抬頭看他,垂著眸,視線亂瞟,睫毛一直不停的顫。陳昭噙著笑,笑聲在她心上輕輕地撓。——“和我在一起好不好。”
17.9萬字8 7701 -
完結122 章

霍律師,我愿意
霍燃一直知道,他和蘇予是兩個世界的人。她是千金大小姐、成績斐然、溫柔善良;而他是嫌疑犯的兒子、家境貧寒、冷漠寡言。但從他見到蘇予站在臺上,宣讀入學誓詞的那一刻起,他就想將她據爲己有。四年相戀,四年分離,從窮學生到知名大律師,他所有的努力,都是爲了走到她身邊。久別重逢,他把她逼在牆角,揚脣輕笑,他說:“這一次,案子與你,我都要。”與你相遇,是不可抗力。贏了再難的案子,都不如贏得你的心。
19.1萬字8.18 372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