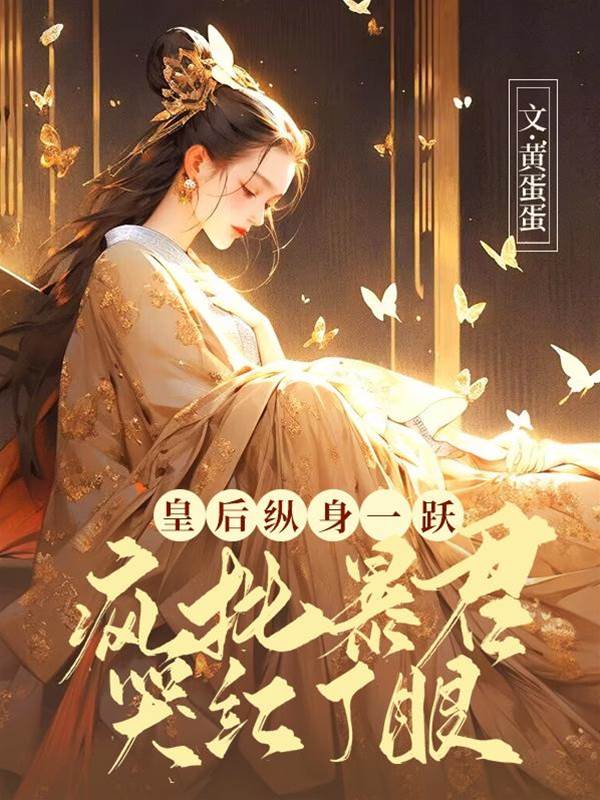《深宮繚亂》 第6章 驚蟄(2)
在場的人聽了這消息,皆面面相覷。太皇太后有請,可是件石破天驚的事兒。如今這當口,哪家的姑娘能進后宮見上主子們,不拘是太皇太后還是皇太后,哪怕是位太妃,都是與前程大大相關的,所以憑什麼是?
嚶鳴并不這份殊榮,蹲了個安道:“諳達,不知老佛爺傳我,究竟有什麼吩咐?”
太監哪兒能隨意說話呢,蝦腰笑道:“姑娘可別為難奴才了,奴才聽差辦事,不敢妄揣上意。您就跟著走吧,橫豎不能是壞事兒呀。”
既不是壞事兒,那必定是好事兒,可眼下的好事兒都帶著不吉利,好事兒也不能稱之為好事兒。
松格惴惴攙出了棚座,主仆兩個走在夾道里,云翳中短暫出一線天來,柱子一樣打在們足前。傳話的太監有頂子,不像那些辦雜差的蘇拉謹小慎微,他噯了聲道:“半拉月沒見著老爺兒①啦,今兒倒好,恰落在咱們這片,多大的造化呀!”
嚶鳴笑了笑,“可不,今兒驚蟄,萬復蘇,天兒要暖和起來了。”
“暖和了就有春雷。”太監嘿地一笑,“一候桃始華,二候倉庚鳴,三候鷹化鳩。您瞧瞧,多好的節令。”
皇后才崩的,在后宮太監的里竟還能蹦出“多好的節令”來,嚶鳴愈發為深知到悲哀。只是不好多說什麼,低頭隨他往慈寧宮方向去。走到半道上忽然想起來問:“諳達,我們家太太可也在老佛爺跟前?”
那太監回頭瞧了眼,“您是說公爺福晉麼?這會兒鐘粹宮哭臨還沒完,暫且不好過慈寧宮來。”閨閣里的姑娘,冷不丁獨自見那麼大的人,難免要害怕,便和煦著問,“姑娘以前面見過老佛爺沒有?”
Advertisement
嚶鳴說沒有,“我是什麼人呢,配得太皇太后召見。”
太監最會看人下菜碟兒,喲了聲笑道:“瞧姑娘這話說的,您是納辛納公爺家的格格,您阿瑪早前勤王立過大功的,您要不配,天底下可沒人配得上了。先頭老佛爺違和,前兩年也沒召親貴小姐們進宮敘話。如今逢主子娘娘大行,老佛爺心里頭難,見了姑娘好排解排解……老佛爺一向最疼皇后主子。”
這太監滿沒一句實在話,嚶鳴懶得應付他,不過笑了笑,提袍邁進了慈寧門。
太皇太后在西暖閣召見,暖閣南邊的一溜大窗戶都鑲著玻璃,錯落放了一層綃紗簾子。匆匆看了一眼,沒能瞧真周。很快迎面有人上前來納福,“老佛爺正盼著姑娘呢,姑娘快進去吧。”一面招人來領走隨行的松格,一面打起竹簾,將引進了前殿。
宮廷是個等級制度極森嚴的地方,慈寧宮當上差的有六人,底下聽差的太監宮還有一二十。自打進宮門開始,每一門上都有人侍立,這些人眼觀鼻鼻觀心站得筆直,絕沒有一個一子或抬一抬眼,時候久了,簡直要懷疑他們是不是活人。
嚶鳴走到暖閣前,心里還微有些發憷。趁著侯旨的間隙站住腳定了定神,聽見里頭宮回話,說納公爺家小姐到了,太皇太后應了句“請進來吧”,才舉步邁門檻。
慈寧宮外都鋪著氈,殿外用棕,前殿按規制用紅。暖閣里相對要松散得多,用回疆進貢的栽絨毯,織出獅子滾繡球的圖案,踩上去腳下綿綿的,像踩在云端。
嚶鳴目不斜視上前,暖閣里并不只太皇太后,陪坐的還有好幾人,也不知道都是誰。反正甭管是誰,這刻所有人都在審視,這些尊貴人兒的眼睛,比針芒還鋒利。
Advertisement
但越是毒辣,就得越從容。太皇太后坐在南炕上,素服的下擺平整搭在腳踏前,嚶鳴兩手加額,恭恭敬敬叩拜下去,“奴才鄂奇里氏,恭請太皇太后萬福金安。”
靜謐的屋子里響起脆生生的嗓音,十分鎮定自若,一點兒都不怯。太皇太后頷首慨:“這聲口多水亮,像鸝鳥兒似的……伊立吧。”吩咐跟前宮,“快攙起來。”
嚶鳴起,才大致看清在場的人。當然不是放平了視線打量,只能微垂著眼,拿余去瞧。因著皇后新喪,宮里妃以下的須服,慈寧宮和壽康宮的長輩們都著素服,不甚敞亮的暖閣里按序坐了四五人,有種窅冥沉悶的迫。
上首的太皇太后不是十分威嚴的長相,一般上了年紀的人,臉架子相較年輕時都要和許多。但若說慈眉善目,斷斷也談不上,一個鞠養教誨了兩代帝王的人,在神上所施以你的重是無形的,無所不在。
至于底下兩側陪坐的,必然有皇太后和太妃,只是人多,無法判斷誰是誰。原本們把傳來,像看猴兒一樣看,也不讓到多忐忑。然而這群人中間摻進了另一張悉的面孔,了一眼,心里便一——那是深知的母親,果勇公福晉。
薛福晉站了起來,一縞素,面很憔悴,大概是哭得太厲害了,眼睛仍是浮腫的。驟然離世,對的打擊空前大,嚶鳴沖蹲安,扶了一把,勉強笑道:“老佛爺和太后、太妃們都是極和氣的,你不必怕。”說罷引給在場的每一個人磕頭,說,“這位是太后主子,這位是敏貴太妃,這是榮太妃……”
姑娘行禮如儀,行舉止沒得挑揀。敏貴太妃擱下茶盞,不無惆悵地嘆息:“瞧見這孩子,就像瞧見了大行皇后。兩個人段差不多,一樣得,一樣進退有度。”語畢出手絹來掖淚,“可惜了皇后,這樣大好的年紀,天命不永……”
Advertisement
這是在提醒太皇太后勿走老路,別送走一個,又迎進來一個。
暖閣里的人聞言,自要應景兒紛紛抹淚,可也只有薛福晉哭得真切,哀聲道:“貴太妃說得很是,這兩個孩子差了兩歲,擎小兒就好,常是兩府里混著住,一對兒姐妹花似的。奴才家里子嗣運尚可,唯獨姑娘運不旺。奴才夫婦好容易得了皇后主子一個,想讓兩個孩子做個伴兒,索認了嚶兒做干閨,全們姊妹的誼。當初皇后主子進宮,嚶兒年紀還沒到,兩個人分別,別提多傷心。故而皇后主子不時傳召,也是念著,不忍割斷了姐妹的緣分。”
薛福晉說起往事,幾乎控制不住要大放悲聲,但忌諱目下形,在嚶鳴安下略平了平心緒,這才又道,“誠如貴太妃說的,奴才見了這孩子就想起大行皇后,心里刀絞似的。可人死不能復生,事兒既然出了,也請萬歲爺和老佛爺及太后節哀。總算老天待奴才不薄,皇后主子雖崩了,奴才還有這個閨,瞧著,也能略解解這喪之痛。”
太皇太后點頭,臉上神也很哀致,悵然道:“事發突然,前幾天各宮請平安脈,我還特特兒問了皇后脈象,都說不礙的,一冬都熬過來了,開了春天氣一暖和,自是百病全消。可誰知……”一聲長嘆后還是溫言勸,“你要看開些兒,人之生死自有定數,佛陀涅槃才得正果,何況你我。”說著轉眼來打量嚶鳴,微微一笑道,“你也別拘著,坐下說話吧。”
嚶鳴蹲安謝恩,欠在薛福晉旁坐下,心里惴惴的,薛福晉一口一個“閨”,不論是對還是對齊家,都不算好事。
果然的,太皇太后把注意力集中到了上,“納辛是個有學問的,嚶其鳴矣,求其友聲……這名字取得真窩心。人活一輩子,有的人為財,有的人為權,有的人為,我料著能這個名字的,必定是重重義的孩子。嚶鳴,你今年十八了?”
Advertisement
嚶鳴起說是,“回老佛爺的話,奴才是四月里生人,再過兩個月就滿十九了。”
太皇太后聽了,長長哦了聲,“宮中大選的日子是二月初十,也就差了一個多月罷了。后來聽說你子不好,如今可大安了?”
當初納公爺為了不讓參加三年一回的選秀,特往宗人府報病出缺,這件事若能含糊過去,倒不是什麼大事,橫豎鉆空子的員多了,不納辛一個。但若是宮里要追究,那事就了不得了,降級、申斥,都是往輕了說的。
嚶鳴知道茲事大,更要謹慎應對,便俯首道:“謝老佛爺垂詢。回老佛爺話,奴才十歲上曾有一回落水,后來得了哮的病。家里阿瑪和額涅四為奴才求醫,上年偶然間遇上個游方的郎中,開了十劑藥,把奴才的病勢控制住了。只是病兒還在,每年了三九就要犯。捂得熱乎些,不吹涼風還猶可,若吹了涼風,那就說不好了,連躺下都不能夠,夜里得坐著睡。”
太皇太后點頭,“宮里藥房有個揚州選上來的醫,周興祖,最得皇帝重,每月養心殿請脈必是他。他醫高超,從他手上治好的疑難雜癥不老,回頭打發他上你府里去,他瞧一瞧,總要去了病兒才好。”
這一說,激出嚶鳴一冷汗來。只覺手腳都麻了,還得住不至失儀,呵著腰說:“奴才何德何能,讓老佛爺為奴才的病費心。周太醫是為主子們瞧病的,奴才人微福薄,不敢勞。”
太皇太后卻和皇太后相視一笑,曼聲道:“你福澤深厚得很,仔細作養子,將來好日子長著呢。”
至于后來是怎麼走出慈寧宮的,嚶鳴已經想不起來了。只記得人飄飄的,像離了魂似的,見到福晉第一句話就是“額涅,怎麼辦呢”,把福晉嚇了一大跳。
作者有話要說: ①老爺兒:太。
猜你喜歡
-
完結247 章

崔氏玉華
早當家的本地女的故事 崔氏玉華,她是尊貴的崔氏女,也是低賤的胡漢雜種,決絕的親娘從小苛求,讓她早熟懂事,格外機敏,欺壓利用都無所懼,娘讓我好好的活著,我便要好好的活著......
74.5萬字8 11803 -
完結488 章

踹翻渣男后,全京城排隊求娶
上輩子,顧櫻為了一個江隱,放棄東平伯府嫡女的尊嚴,死纏爛打,終于嫁他為妻。后來,江隱位極人臣,先謀國,后殺她父,滅她族。而她被渣男渣姐合謀打斷雙腿,扔在破廟,受盡侮辱,整整十年。重生后,顧櫻浴血歸來,占盡先機。復仇第一步,抱住“未婚夫永安小侯爺”大腿,踹渣男,斗渣姐,將汴京世家勛貴玩兒得團團轉!復仇第二步,跟“未婚夫”退婚,遠走邊疆,帶著幼弟去找父親!復仇第三步,找個“三從四德”的聽話男人把自己嫁了,遠離渣男,會不幸!可她萬萬沒想到,自己陰差陽錯抱住的大腿,竟然不是小侯爺,而是傳說中神秘狠辣的...
86.8萬字8.18 145079 -
完結403 章
盛寵醫妃世無雙
神醫殺手雲念一朝身死,再次睜眼時成為了駱家人人可欺的軟包子二姑娘。 駱晴看著滿屋子利欲薰心的“家人”們,決定手起刀落一個不留。 順便再帶著家產,回到京城去找她的仇人們。 殘暴皇帝愛煉丹? 那就讓他中丹毒而亡! 仇人臨江王中了蠱? 那就讓他蠱毒發作爆體! 世人皆說平陽王深情,亡妻過世以後仍然娶了一個牌位當王妃。 可是直到有一天,他遇見了駱晴。
95.2萬字8 18984 -
完結30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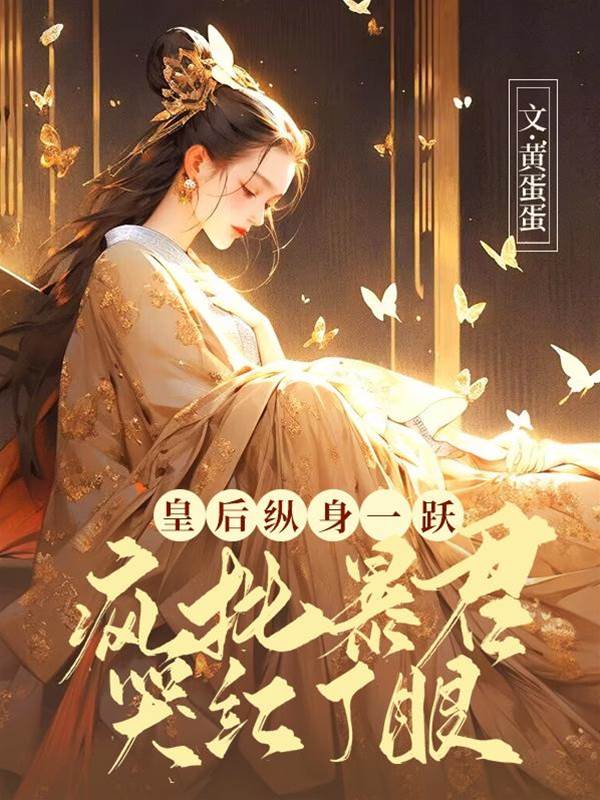
皇後縱身一躍,瘋批暴君哭紅了眼
【1v1,雙潔 宮鬥 爽文 追妻火葬場,女主人間清醒,所有人的白月光】孟棠是個溫婉大方的皇後,不爭不搶,一朵屹立在後宮的真白蓮,所有人都這麼覺得,暴君也這麼覺得。他納妃,她笑著恭喜並安排新妃侍寢。他送來補藥,她明知是避子藥卻乖順服下。他舊疾發作頭痛難忍,她用自己心頭血為引為他止痛。他問她:“你怎麼這麼好。”她麵上溫婉:“能為陛下分憂是臣妾榮幸。”直到叛軍攻城,她在城樓縱身一躍,以身殉城,平定叛亂。*刷滿暴君好感,孟棠死遁成功,功成身退。暴君抱著她的屍體,跪在地上哭紅了眼:“梓童,我錯了,你回來好不好?”孟棠看見這一幕,內心毫無波動,“虐嗎?我演的,真當世界上有那種無私奉獻不求回報的真白蓮啊。”
53.4萬字8.18 4176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