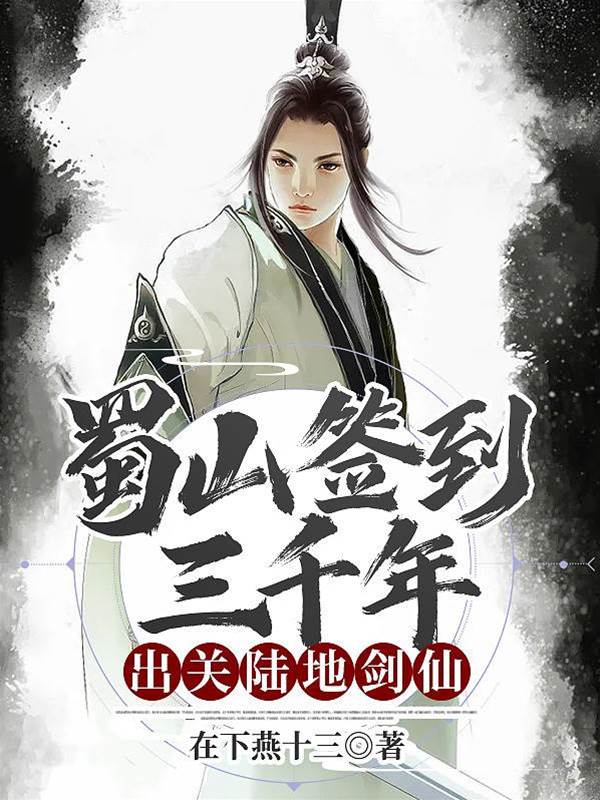《妖王的報恩》 第101章
胡青輕輕拍了拍袁香兒的肩膀:“阿香,你怎麼了?”
袁香兒看見胡青,才從恍惚中清醒過來,
“阿青,我做了一個夢,夢見了一個老人,他告訴我說他是兩河鎮的河伯。”
袁香兒把夢里的形大致說了一遍。
“你這是被托夢了。奇怪,兩河鎮又不遠,他為什麼不親自來。”胡青在的邊坐下,手捻起袁香兒脖頸上的南紅吊墜,“阿香,你用過我的法應該有所會,人類的神力相比妖魔十分脆弱,容易妖魔的影響乃至控制。你的雙魚陣只能護住,一定要對神類的法多加小心。”
袁香兒想起了自己被白篙和窕風拉幻境的經歷,“是啊,在神力的控制上,許多妖魔確實強大而有力。窕風甚至能用神力構建完整而真實的世界,讓我幾乎沉迷其中不了。”
“你也不用妄自菲薄啦,”胡青笑盈盈地把一盆洗好的往晾繩上曬,“窕風那樣以瞳至幻為天賦能力的妖魔,你都能打贏他,已經很厲害啦。”
掛在繩上的隨風擺,在石桌上投下斑駁翻飛的影子。
袁香兒著這張自己從小就趴在上面的石桌,石頭的冰冰涼涼,傳來一和自己通相連之意,袁香兒運轉靈力,桌邊石紋便開始流轉,現出其中的小世界。
自己能戰勝窕風,還是多虧了師父的相助。如果是師父在家,聽見河伯求上門來,想必不會坐視不管。
袁香兒手幫胡青一起披曬,“我去兩河鎮看看好了,或許真的有什麼特別為難的事呢。”
兩河鎮與闕丘鎮比鄰,距離并不遠,坐牛車的話一天都可以趕個來回。上一次為了虺螣的事,袁香兒已經去過一次。
Advertisement
出門的時候,遇到鄰居家的二花。
二花的父親以殺豬為生,在市井上開了個豬鋪子,家境算得上是殷實。聽說袁香兒要去兩河鎮,二花回提了一副豬下水并兩刀三層,托袁香兒帶給嫁到兩河鎮的大姐。
“大花姐嫁得好人家,還差你帶這個?”袁香兒打趣。
大花,二花的家中雖說父母也拼命生了幾個弟弟,但對家里的兩個孩也并不算苛待。為了兒幸福,給大花挑了個讀書的人家,了嫁妝,高高地嫁了,聽說丈夫還是個秀才。
這對殺豬賣的商販人家來說,是難得的好姻緣,談婚論嫁的時候不知道引來多街坊鄰居的羨慕。
“左右你替我帶給大姐便是。”二花把打包好的豬塞給袁香兒,“你還不曾嫁人,家里長輩又寵著,如何知道做人家媳婦的辛苦。”
袁香兒懷里抱著變小狼的南河,搭上了載客的牛車,慢悠悠往兩河鎮行去。
沿途看著波粼粼的大河,袁香兒不住和趕車的大叔搭話,打聽兩河鎮的形。
“咱這兩河鎮啊,沅水和酉水就匯在家門口,從前那是隔三差五就要發一次大水。記得我小的時候,鎮子上還常常給河神送新娘子以求平安。把那十七八歲的大姑娘,披上嫁,放在木板上推到河中央去。”
趕車的大叔四五十歲的年紀,路上跑得多了,見多識廣,喜歡嘮嗑,什麼都能說兩句。這一段往事說得一車的人都聽住了。
“那新娘子還能回娘家嗎?”車上一個七八歲的孩懵懵懂懂地問到。
的母親按住了的,輕輕搖頭,“不可妄議神靈。”
“害,獻給河神了,哪還能在人間呢。”趕車大叔向地上呸了口痰,“每到那個時候,河邊看熱鬧的人群里三層外三層,新娘子的家人都是拿了錢的窮苦人家,但也還是舍不得,免不了哭哭啼啼相送。有時候新娘子不肯,掙扎得厲害,還得捆綁起來。當真是可憐。”
Advertisement
“這些年似乎沒聽說了。”車上有乘客問到。
“大概三十年前,突然間鎮上數十人都夢見了一位白胡子的老人,一位人面蛟尾的男子,說他倆乃是河神,令大家不許再以活人祭祀,鎮上居民這才廢了舊俗,修建河神廟,豎了兩位河神金在廟中供奉。果然,這些年來風調雨順,水患也了許多。”
“我曉得,我曉得。我見過外婆家的河神廟,屋頂上有一個金燦燦的寶葫蘆。”牛車上的小孩忍不住興地說。
袁香兒繼續打聽,“近來兩河鎮上可有發生什麼大事?妖魔強人出沒之類?”
“哈哈,你這小姑娘家家一個人出門怕了吧,抱一條這麼小的狗子頂什麼用?放心啊,咱兩河鎮的治安是出了名的好。大叔給你載到最熱鬧的紫石大街再放你下去。”
趕車的大叔果然將們載到繁華熱鬧的街區。
街口就是兩河鎮標志建筑河神廟。
大概是風調雨順了多年,廟里祭拜的信眾并不多,淡淡的香煙中,袁香兒步了河神廟。
廟里供奉著兩座神像,其中一人慈眉善目,白須飄飄,正是袁香兒夢中所見的酉水河神。另一人人面蛟,披甲持銳,威嚴魁梧,乃是傳說中沅水水神。
袁香兒燃了三炷香,在了神龕前的香爐中,那香煙不凝,隨風潰散。神龕中的神像面容呆滯,不到任何靈力可以通之。
到底是什麼為難之事,讓河神都無法解決,他甚至不能說清楚話語,只能匆匆托夢,連真都沒現出一個呢。
袁香兒在廟中逛了半圈,沒有任何收獲,只得退出廟來。
這條街被稱為紫石街,紫紅的河石鋪就的地面已經有了上百個年頭,厚厚地鋪滿了時的印記。街道上一群的孩子們玩著屬于孩的游戲,稚的歡笑回在長長的巷子中。路邊有賣糖葫蘆,糖畫,面人等等各孩喜小吃的小販在擺攤售賣。
Advertisement
人類的孩中,甚至時時會看見一兩只為人形的小妖,混雜在人類的孩子中玩鬧嬉戲。
袁香兒喜歡這樣的市井熱鬧,抱著南河邊走邊看,為了不引人注目和方便起見,南河一路化為小狗一般大小,任憑袁香兒抱著走路。
“上一回和虺螣一起來,沒來得及逛一逛,這一次我們好好耍耍,多買點好吃的帶回去。”袁香兒向著打聽到的大花婆家所在之走去。
迎面走來一個大腹便便的中年男子,邊一位的小妾扶著他的手臂伺候行走。那男子志得意滿,著肚皮笑盈盈地走路。卻不知自己的肩頭趴著一只淋淋的魔。錯而過的瞬間,那魔甚是扭頭過脖子看著袁香兒,
“你看得見我吧?我覺你剛剛看見我了。”
袁香兒面無表地向前走去。
那魔長脖子看了半天,這才回去,跟著那男子走了。
袁香兒停下腳步了口氣。不太喜歡這些人間由怨念滋生的魔,難纏,無法通,外形還恐怖。
“這個兩河鎮的魔是不是也太多了些?還是我們闕丘好,除了兩三只無害的小妖,基本沒有這些七八糟的魔。”
闕丘安寧平靜,如世外桃源。乃是因為曾有師父坐鎮,禍害人間之不敢隨意進吧。
此刻,袁香兒的右手邊是熱鬧的街道,左手恰是一條幽暗的胡同口,那胡同既臟又窄,兩側高墻夾道,只能進淺淺一點,是個沒有出路的死胡同。
袁香兒擼著南河脊背的發,突然發覺手中的小狼不太對勁,那發下的很明顯死死地繃了。即使了他的發,它們也依舊繃得像是一塊塊鐵片。
“怎麼了,小南?”袁香兒把南河舉起來。
Advertisement
銀白的小狼勾著腳,繃著沒有說話。
“怎麼了啊?”袁香兒搖他。南河長大以后,形雄健而矯捷,十分麗。但其實袁香兒心底還是最喜歡他這樣一小團茸茸的模樣,時常找借口讓他變這個樣子,好抱在懷中肆意。
“我不是第一次來到這里。”南河終于說道。
“我知道啊,上一回和虺螣一起來過。”
“上一回也不是。”
袁香兒的笑容就淡了,南河在遇到之前只來過一次人間。
把南河抱在懷中,輕輕了他的耳朵。
“我從天狼山上悄悄溜出來,來到這個鎮上,就在這個位置看見了一群人類的孩子在玩耍。那是我第一次見到人類。”
天真的小南河變了人類小男孩的模樣。
一個人類的男孩發現了在一旁窺的他,“喂,哪來的?會玩毽子嗎,要不要一起玩?”
那個毽子的東西是用一堆鳥類羽綁在銅錢上做的玩,可以在腳上上下翻飛的踢著。南河學得很快,他迅速為了踢毽子的佼佼者,彩的羽毽子在他的腳踝,肩膀,膝頭,仿佛被牽引著一般地跳躍。引得一群孩子圍觀好,齊聲給他數數。
那一刻他真的很開心。他是兄弟姐妹中最小的一只狼,哥哥姐姐們連打架都不屑帶他。
人間的熱鬧有趣和新到的朋友讓他到無比的快樂。
游戲結束之后,孩子們紛紛取出幾個零用錢,圍著賣零的商販們。那些晶瑩剔的糖果讓南河咽了咽口水,但他不知道從哪里能獲得換這些食的錢幣。
“喏,分你一個。”最開始招呼他的那個男孩手里拿著一雙竹簽,他把竹簽上一團金黃粘稠的麥芽糖攪開,分兩團,遞給了南河一。
“拿著呀,甜的。”
“啊,給我的嗎?謝謝。”
“謝啥,咱們是朋友了,明天還來這里玩啊。”
明天還來這里玩。南河笑著往回走,手里舉著一團琥珀的麥芽糖,高高興興地想著。
……
“就是在這個巷子里嗎?”袁香兒問他。
南河沉默著沒有說話,他化為高大俊的男子,站在巷子口。
漫長的時過去了,自己已經年,但這條巷子幾乎還和一百年前一樣污濁暗,甚至連那地磚的裂似乎都沒有變化過。
他幾乎可以看見小小的自己被在法陣里,折斷了四肢,那一塊金黃的糖掉在了泥地里,被人隨意踩在腳下,他甚至還來不及嘗到那位朋友口中說的甜味。
一只連指甲里都沾著污的手過來把他提了起來,肆意撥弄兩下,嘿嘿嘿地笑著,
“天狼,看我抓到了什麼?一只這樣小的天狼。”
“無論是剝皮煉藥,還是契為使徒,都發了,掙大發了,哈哈哈。”
那個時候,他心里有多仇恨和怨念,甚至想要殺死這個世界上所有的人類。
一只的手到了他的臉頰上,南河掙了一下,清醒過來,才意識到是袁香兒在安他。
“沒什麼,一百年前的事了。我都已經忘了。”他扶著冰涼的磚墻悄悄了口氣,向袁香兒出一點笑容。
“那是你第一次見到人類吧,那些人真是太可恨了,換了我是你,我可能都恨死人類了。”
“幸好,第二次就遇到了你。”
“啊,我那時候,好像也沒對你多好。”
袁香兒已經不記得剛開始是怎麼樣和南河相的了,最開始的時候,印象最深的是一撮邦邦的小尾和那總氣鼓鼓對著自己的屁。
“你對我很好,把我裝在籃子里,再一次帶進了人類熱鬧的市井中,給我吃桂花糖,還給我繪制躺在里面就很舒服的法陣。”
如果不是遇到了你,我或許至今還憎恨著人類,或許我已經每天埋頭在殺戮中,沉淪為一個盲目嗜的復仇者。
那個人握住了他的手腕,吻上了他的雙。南河后退了半步,脊背已經抵上了冰涼的墻壁。
“阿香……唔。”
他想說話,胡同口雖然昏暗,但街道上好多人,近在咫尺,熱鬧喧嘩。
袁香兒的手腕晃了晃,遮天環的芒亮起一道明的圈,將二人的影,軀,和那逐漸溢出的濃香收容在完全明的小天地中。
邊就是人來人往的街道,雖然那些人看不見,但他們的存在依舊讓南河繃了神經,越是這樣繃著神,到的刺激就越強烈。
“阿香,別在這里……”
口中說著別在這里,卻已經被自己溢出的甜香薰得頭皮發麻,很快徹底忘記一切,沉淪進極致的快樂之中。
這條幽深的小巷本是他一生中難以磨滅的痛苦回憶,但從今日之后,快樂的回憶覆蓋了那份深深的刻痕,取代了那份永恒的痛苦。
袁香兒和南河找到大花婆家的時候,天已經微微近黃昏了。
大花又驚又喜地到院門外來迎接。
“阿香,你怎麼來啦。你看你,我結婚你都沒回來,這下舍得來看我了。”大花又是埋怨,又是歡喜,將往家里迎。
這是一棟青磚白墻的大院,已經有了不年頭,白墻斑駁,朱漆落。橘紅的斜傾瀉在半邊院子中,院子里有著不人,都紛紛站起和進家門的客人點頭示意。
袁香兒頓在門檻,差點想要往回走。在那些笑面相迎的影后,站著一個腦袋巨大,軀窄小,端端正正穿著長袍的影。
那魔的巨大面孔上細眉小眼睛,還帶著一頂低品階的帽,也正跟著眾人一起低頭行禮。
(要我吃了他嗎?)南河的聲音在腦海中響起。
(不不,他沒有惡意,一般是祖先留在家中守護后代的靈。我只是被他嚇了一跳,這腦袋也太大了。)
猜你喜歡
-
完結751 章

九天戰神
葉揚穿越異世,得九天玄劍認主,習神秘功法《戮神訣》,走上一條靠殺戮修行之路,逐漸揭開九天玄劍隕落之謎,殺上神界,血染九天。 家族中,面對家族弟子的排擠,他如何嶄露頭角? 學院裡,面對無數天才的壓迫,他如何崛起爭鋒? 帝國內,面對殘忍嗜血的敵人,他又如何迎戰? 如何解開自己的身世之謎?如何守護身邊如花似玉的美女?
204.6萬字8 115691 -
完結1354 章

天命逆凰之假小子拽翻天
玄武大陸,玄者與武者的天下。 他,司馬相思,大陸五大世家中司馬世家直係的十三“少爺”,因不能修煉,被親父拋棄,成為棄卒。 她,相思,二十一世紀的一普通大齡剩女。 當她的一抹靈魂附體於折損的司馬相思身上時,一切,開始改變。 異世重生,為了抗衡家族加註在她身上的傷害,也為了尋找身世之謎,她,踏上了成長的道路。 重生的她,入大陸險地,機緣之下,得天命契獸,開啟封印,亦開啟在異世的強者之路,巔峰之行。 端木千雪,她,迴歸母係家族後的新名字。 十年一度的茶會上,一展天賦,名動天下,自此成為大陸千萬年來驚才豔豔第一人! 她,關於自己的身份,卻對她的生死契約獸淡然一笑,說:竟然吾是命定所歸,那吾必重振吾族的榮耀,與你重振大陸,共傲巔峰,人若阻之,吾必誅人,神若阻之,吾必弒神,縱是逆“天”,吾亦在所不惜! 都曉“他”小小年紀,一張俊顏絕天下,又有誰知,“他”竟是她!
212.8萬字8 8857 -
完結1192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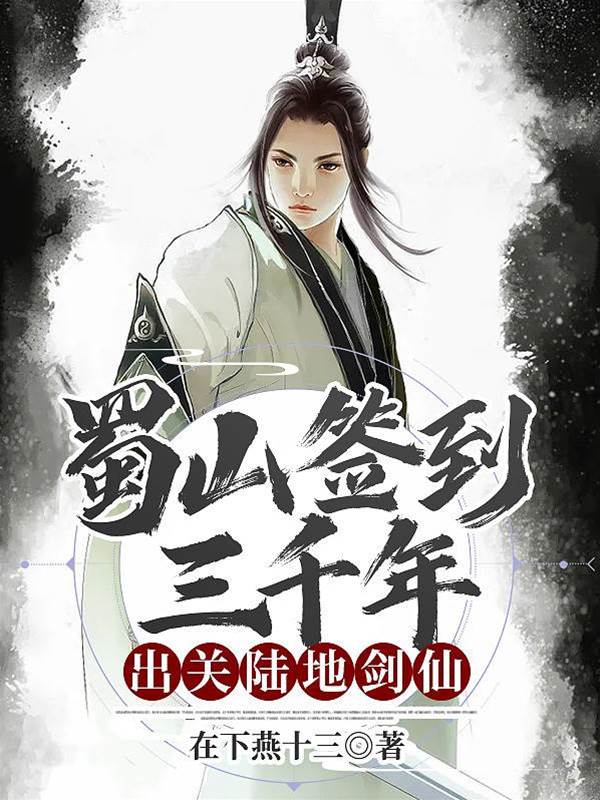
蜀山簽到三千年,出關陸地劍仙
赵凡刚穿越成为蜀山少宗主,还没有来得及大展拳脚,享受众星拱月的待遇,却因为前身私闯禁地致使紫青双剑暴动误伤门人,被蜀山宗主打入锁妖塔不得翻身! 但幸运的是,赵凡刚被带到锁妖塔,就意外激活了签到系统,在系统的帮助之下,他如同开了外挂一般在锁妖塔内默默变强。 “叮,锁妖塔大门前签到成功,奖励先天剑体。” “叮,锁妖塔内签到成功,奖励培元丹。” “叮,锁妖塔妖坟古门签到成功,奖励极品飞剑。” …… 三千年后,赵凡盘坐虚空,仙道气息震动苍穹,终成一代陆地剑仙,问鼎修仙长生路
238.9萬字8 80905 -
連載426 章
仙業
夢從海底跨枯桑,閱盡銀河風浪。 —————— 九州四海,玄宗魔門,天人外道,淨土僧伽。 煉炁,授籙,服餌,佔驗…… 入無窮之門,遊無極之野,與日月齊光,與天地為常。 前塵皆客,再世為人。 這一次。 只願求長生!
137.4萬字8.18 145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