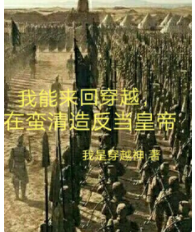《穿越之絕色寵妃》 第九十五章、巫匪之地
提及令牌,若奕平淡的眼眸起了波瀾,淡聲道:“此爲巫匪的當家令牌,顧名思義,可以持此令牌之人,也只有巫匪的兩位當家人。”
“巫匪?”安雨欣微微斂了眸,仔細端詳了下手中的令牌,忍不住問道:“那這土匪的頭目也太大意了些,連當家令牌丟了都渾然不覺!”
卓越眉宇間卻著一輕愁,看著安雨欣道:“姑娘有所不知,巫匪是他們對自己的所稱,而巫峽鎮的百姓卻都視他們爲恩人。巫匪裡的人大多數原都是鎮上的百姓,但因巫峽鎮屬兩國界,無人問津,而又位屬乾旱、崎嶇之地,以致鎮上的土地無法耕作。民以食爲天,沒有糧食對於百姓來說無疑等於頭頂的天塌了下來。因此,鎮上的人漸漸搬離,大多數都搬到了鎮旁的山上,並以巫匪自居。這些年,他們一直是靠打劫兩國通往的商隊爲生,而後將所得與鎮上百姓平分。”
“既然如此,那些巫匪也算是劫富濟貧做好事了!”安雨欣面上劃過一抹詫異,但是隨即又有些疑道:“但是又爲何做出這等強搶良家婦之事呢?”
“卓越方纔所說,不過只是前景。”卓青看向安雨欣,接著道:“本因巫匪的接濟,巫峽鎮的百姓生活漸漸都得到改善,家家都可以溫飽。但不知因何原因,從兩年前開始,巫匪不再接濟救助鎮上的百姓。不僅如此,也不再如以往一樣只劫取商隊,而是見人就劫,見錢就搶,甚至將鎮上的年輕子都劫到了山上。鎮上的百姓無力與之抗衡,在失去接濟和巫匪的欺下。走的走,逃的逃,漸漸地只剩下些承不來長路遊走的婦孺和老人。便了我們現在所見的這片荒涼之景。”
Advertisement
“原是如此。”安雨欣恍然的點了點頭,“在兩國界面臨這片荒涼之地。又要承巫匪的欺,真是苦了這些百姓了。難道就沒有辦法救他們嗎?”
若奕面上的神凝轉爲肅然,清淡的語氣含了低沉道:“沒有辦法。若是想幫這些百姓,解救巫峽鎮的荒涼之景,便要將這片土地劃爲大寒。但此地爲與燕國的界,但若這麼做的話,只怕會讓況愈加不妙。這些年燕國雖表面上對我寒別無二心,實則背地裡一直在儲蓄兵力。一心壯大權勢吞併鄰國與我寒抗衡。若是在此刻將此地劃爲我國領土,只會愈加引起燕國的不滿從而使之有合理的理由反攻。而只要戰爭一起,苦的便不只一個巫峽鎮了。”
安雨欣此刻的眼眸黑的純粹,氤氳著難以言喻的緒。
這些百姓在流離失所、承欺之時,心中定是存著恨的吧,恨放棄了他們的君王,恨讓他們的命運淪落至此的那些決策者。
但這又何嘗不是爲君王的無奈和痛心之...
爲了更多的百姓可以得到安生,爲了避免戰爭紛帶來的更多民不聊生,他只能狠下心做了選擇。但是抉擇之後,又怎會不心痛...那些被他拋棄、被他親手放任而去自生自滅的百姓。也同樣是他的子民啊!
看著若奕說這些話時,面上的溫雅深沉,眸中的鬱深邃。安雨欣似是漸漸開始懂得,他上所揹負的是怎樣沉重的一個包袱。心口有一瞬的涼氣涌過,讓人不由嘆息。
抑的沉默持續了許久,卓青略含所思的看了眼面前兩人的神,嘗試著開口將氣氛再次引正題,“依那人方纔所言,那位李大夫的妹妹,確是我們要尋的人無疑。”
Advertisement
語落,卓越面上卻微有不贊同。“此人方纔描述的相貌的確與...與小姐相符,但是屬下還是認爲。李蒙並非是不懂得明哲保之人。如若被搶走的人不是對他來說極爲重要的人,他又怎會願意以命相抵?”
安雨欣看了眼面重複沉靜的若奕。對各持看法的兩人道:“不管李大夫的妹妹是不是我們要找的人,既然此事被我們到,自然便不能袖手旁觀。”
“姑娘所言甚是...”卓青說著略顯遲疑,接著道:“只是...我們若想救人,便要尋得那羣巫匪的居。且不說山路實則陡險,單憑我們三人之力,就算上了山也不佔任何優勢。在沒有萬全的計策得以保證兩位主子的安全下,屬下定不能讓二位犯險。”
卓越不由皺眉道:“難不就在這裡坐等?等到那羣巫匪將人放了嗎?”
卓青臉鐵青的看向卓越,卓越方纔恍悟,自己剛纔所舉不是勸著兩位主子上山犯險麼...隨後想開口挽回,卻不知該如何言語了...
若奕低垂著墨眸微掀了下眼簾,須臾,沉靜的開口:“你們兩個先將李蒙的安葬,然後上山打聽一下巫匪的居地,切勿打草驚蛇。待你們歸來後,我們再商討應對的計策。”
語落,卓青和卓越面上的古怪之方纔退去,恢復正,齊聲應“是”。
——————————
“你說,若是讓那些朝中老臣們得知,明日登基大典時坐在龍座之位的只是個替,而真正的新帝此刻卻同我在打掃茅屋,會不會齊齊上奏告我個藐視天子啊!”安雨欣說著開始浮想聯翩,想到那些老臣吹鬍子瞪眼又無可奈何的模樣,就忍不住想笑。
Advertisement
見安雨欣面上的俏皮笑意,若奕自知定是某人又陷自己想象中的景去了,不由搖頭一笑。
經過兩人之手,凌無章的茅屋已呈一片井然有序的簡潔之象。兩人並肩坐在門前的長凳上,安雨欣的心中卻猶如被風拂過的水面,無法平靜...
若奕握手中的荑,輕聲道:“我既選擇出宮來到這裡,你又何必還想著讓我回去。”
安雨欣收回恍惚的神思,輕語喃喃道:“我如今倒不是怕擔上紅禍水之名了,只是那些老臣所說並不無道理。國不可一日無君,更何況還是每位君王一生僅此一次的登基大典,你真的就準備讓他人代之嗎?我還是放心不下...”
若奕無聲一笑,攬上安雨欣的肩,“你儘管把心好好收著便是,我的易容雖不能與丹王伯伯相較,但置於那些人自是足夠了。再說,我此番決定也不只是因爲你。若晗是我一母同胞的妹妹,我對的擔心,不比你。”
聞言,安雨欣眸中的氤氳的雲霧散去,輕嘆一聲,道:“自古君王在面臨江山與人不可兼得的抉擇中,都是選擇江山而棄人。倒並不皆因薄,只是人更江山罷。怎麼如今到了你這兒,顛覆的如此之大...”
若奕淡淡一笑,冬日的在他清雅冠絕的容上渡上了一層華,愈加襯得那般高雅而出塵。那雙清幽深邃的墨眸中,彷彿可以容納的下世間萬,此時卻只映得一人。他眸清雅和,微啓雙脣道:“國確不可無君,但我同樣不可無你。沒有你的天下,我要了又有何用。”
一如平日平淡輕緩的語氣,卻讓安雨欣心湖大震。擡眸凝著那雙墨眸,卻從中看到了足以化一切的深和無與倫比的堅決。
Advertisement
曾懷疑過他的心,曾質疑過自己在他心中的分量,曾在他捧著心意遞到自己面前時,搖擺不定。而卻未曾發覺從哪一刻開始,只要自己擡眸去,他的眸中便只清晰的映著自己一人,別無其他...
而此刻的所言,並非爲君王的承諾,僅是一個男人對心之人的真誠誓言...
心中是從未有過的安寧祥和,安雨欣笑的把腦袋靠在若奕肩上,“好啊!那以後你就負責執掌天下,我呢...就負責貌如花!”
語落,若奕輕笑出聲,那是隻有在面前,才那般肆意爽朗的笑聲。
雖不知明日會如何,也無法預料的到今後會有什麼在等待著他們。但此時此刻,只因彼此都在手可及的地方,他們的心如同此時的眸一樣,平靜而安寧...
忽而,覺到上傳來的異樣,若奕平靜的眸猛然暗沉,蹙起眉。
安雨欣覺察到旁突然僵的子,微微疑的擡起腦袋,看到若奕有些暗沉的臉和蹙的眉,憂聲道:“怎麼了?”
若奕看著安雨欣,眸中卻多了安雨欣不曾發覺過的緒,即使被他極力制,但卻似乎未起到什麼作用。隨即有些艱的開口,聲音卻異常的低沉,“出宮當日,長公主不請自來邀我品酒。我自知有異,提防。卻不料聰明反被聰明誤,還是中了的計!”
從若奕愈漸暗沉的面和眸底的深沉冰寒來看,安雨欣意識到事的嚴重,臉隨之一凜,“刻意誤導,讓你以爲酒壺和酒杯有問題,實則卻是在酒中了手腳,是嗎?”
見若奕點頭,安雨欣心下一沉,眸瞬間冷凝,“好一隻狡猾的狐貍!”
猜你喜歡
-
連載272 章

空間小農女,沖喜丫頭病相公
22世紀的女科研家餘苗,變成了古代的沖喜小丫頭魚苗,不止白撿了一個便宜的病秧子相公,還多了一大家子奇葩的孃家人。母親懦弱,弟弟瘦小,相公,秘密多多。魚苗手握自己研發的空間,邊致富,邊欺負欺負爭寵的美丫頭,還順手幫病鬼相公修理了惡仆。奶奶欺上門,大伯孃打秋風,小姑姑對她的相公癡迷到不可自拔,她皆一一解決掉,而病鬼相公,也在她的靈泉水的澆灌下,越加得玉樹臨風。銀子多多,小兩口蜜裡調油,不止成功地擺脫了一堆的極品親戚,更是財路官路皆亨通。考狀員,上京城,病鬼相公成了人中龍鳳,她卻因為沒有孩子而被詬病。「娘子莫怕,不是你的問題,是為夫的。」
59.7萬字7.5 23057 -
完結889 章

謀御江山
莫笑人間少年夢,誰不少年夢皇朝,談笑風云,羽扇綸巾,少年白衣,絕代傾城……
150.9萬字8 13961 -
連載32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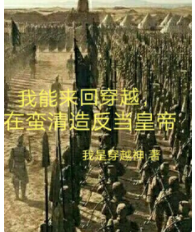
我能來回穿越,在蠻清造反當皇帝
殺伐果斷+冷血+爭霸文+造反+不圣母本書主角每隔一段時間會搞大清洗行動,每次屠殺幾百名上千名不聽話有叛心的手下將領們。對外進行斬首行動。主角建立帝國后,會大清洗
65.6萬字8.33 88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