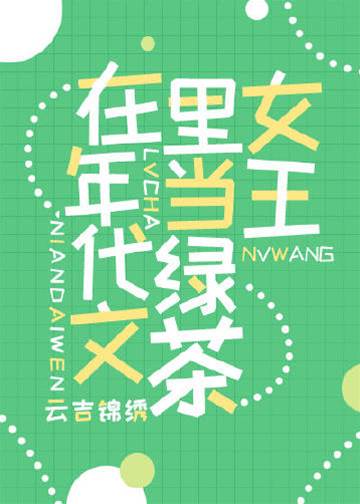《全球追更[快穿]》 第64章 第 64 章
景星闌這一覺, 直接睡了兩天兩夜。
他醒來時,時間已經到了第三天的下午。
過窗簾的隙照在屋,躺在床上的男人眼皮輕了兩下, 緩緩睜開了雙眼。
最先映眼簾的, 是頭頂的天花板。
這是一間陌生的臥室,面積不大, 看上去還有些陳舊。景星闌勉強支起半邊子想要下床,但作剛進行到一半, 他又突然停了下來。
——因為他看到了喬鏡。
黑發青年穿著一在民國文人中很流行的白立領長衫, 大概是因為寫累的緣故, 他不僅沒注意到景星闌醒了, 甚至還趴在桌子上睡得正香。
青年的神略顯疲憊, 纖長的睫隨著呼吸的氣流在空氣中微微輕, 即使睡著了,手里也依然松松地攥著一只鋼筆,而且筆尖的墨水已經把稿紙暈染出了一團墨點。
景星闌歪頭看了他一會兒,角不自覺地帶上了一笑意。
要是喬鏡醒過來, 他想,看到這一頁又要重寫, 恐怕就算表面沉默著不說話, 心卻肯定是極不高興的。
表現在小作上, 就是青年會輕輕抿一下,再飛快地眨兩下眼睛, 像是要讓自己牢牢記住這個錯誤以后不要再犯一樣。
非常可。
景星闌作小心地起,剛想把蓋在上的毯子給喬鏡披上, 方才還在沉睡中的青年就一下子驚醒了。
“……你醒了?”
他猛地抬起頭, 在看到景星闌時, 漆黑的眼睛中也忍不住泛起了一淡淡的喜悅。
“嗯,”景星闌停頓了一下,神有些懊惱,“吵醒你了?”
“沒有,本來我也沒打算睡多久。”喬鏡了太,一臉難以言喻地看著景星闌把毯子放下,然后直接赤/著上半走到他的書桌旁,好奇地拿起了一張稿子看了起來。
Advertisement
他咳嗽一聲,有些尷尬地移開視線:“那個,你能先穿好服嗎?”
就算房間里只有他們兩個大男人,但是景星闌穿這樣,喬鏡還是覺得有些不太自在。
“嗯?我原來的服……”
“太破了,我給扔了。”喬鏡指了指放在床頭邊上疊好的服,“這是我的,裁做大了,所以還沒穿過。”
景星闌看了一眼,發現那是一套黑的長衫,款式和喬鏡上這件一模一樣。
他的心又再度愉快了一些。
換好服,景星闌看了一眼四周,問道:“這里就是你現在住的地方?”
這地方也太寒酸了些,景星闌一邊打量一邊在心里琢磨著,接下來該怎麼說服喬鏡跟他一起搬出去住大房子。
就算青年穿著寬松的裳,景星闌還是一眼就看出這段時日他又清減了許多,連原本就細的腰也窄了一圈。
虧他還在現代辛辛苦苦自學營養學,他在心里嘆著氣想,好不容易才把人投喂得圓潤一些,結果這下是真·一朝回到解放前。
喬鏡點點頭。
“其實原本是住學校宿舍的,”他低聲道,“但是宿舍不讓校外人進,所以我就退宿了。”
這兩天他之所以那麼累,就是因為在景星闌昏迷的這段時間,喬鏡不僅從學校退了宿,還在短短半天和房東簽訂了租房協議,把幾人以最快速度安頓下來,又因為學校附近的房子租金太貴,剛完這個學期學費的喬鏡實在囊中,只好徹夜不眠地寫完了《眾生渡》的前三萬字送到報社,并用它作為擔保,從許維新那兒提前支了一些稿費回來,這才把這個季度的租金問題暫且解決掉。
當然,這些喬鏡都沒有跟景星闌說。
Advertisement
他又不是什麼需要老師小紅花表揚的稚園學生,就算喬鏡不擅長也不喜歡和人打道,但他畢竟是從大學期間就依靠自己獨自離家生活的人。
年人必備的生活技能,這麼些年下來,他早就主或者被地學會了。
景星闌站在原地愣了一會兒,雖然喬鏡說得輕描淡寫,但他怎麼會不知道其中的麻煩和辛勞?
“你辛苦了。”他嘆息道,“接下來……”
他剛打算說接下來就到我照顧你了,喬鏡忽然正對他道:“景星闌,你不要有心理力。”
景星闌:?
他有些茫然,不太明白喬鏡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關于穿越這件事,我大概知道一點兒,”喬鏡含糊道,“不過總的來說還是一場意外,你算是被我連累的……所以,按道理說,我該跟你說一聲對不起。”
景星闌狠狠皺眉:“別瞎扯了。這明明是那只貓的鍋,跟你有什麼關系?”
在他昏迷期間,008已經向他解釋過了這次穿越的前因后果,景星闌也終于明白《地球之歌》中超越時代的知識是來自哪里了——除此之外,008還很兇地對他說,如果景星闌將來故意泄暴/喬鏡的份,或者敢對喬鏡不好,它就向總部申請把男人清除記憶送回地球,并且讓他這輩子無論用什麼電子產品,網速都永遠在404和2g之間徘徊。
雖然景星闌總覺它說這番話時那張黑煤球似的貓臉上莫名有些虛張聲勢的覺,但聽完之后他只覺得好笑,并沒有半分被威脅的自覺——
他當然不會做對不起喬鏡的事!
聽到景星闌主提起008,喬鏡有些驚訝地看了男人一眼,倒也沒問他到底是什麼時候知道的,只是道:“我不是這個意思。我是想告訴你,是我帶你到這個世界來的,所以自然要對你負責。”
Advertisement
景星闌心念一:“對我負責?”
“對,”喬鏡認真道,“我知道你心里有落差,但是不要,我有錢。”頓了頓,他又盡可能委婉地說道,“其實我的稿費還多的,所以你就不用去干那些……那些力活了。”
景星闌:“…………”
搞了半天,他哭笑不得地想,原來喬鏡真把他當那些靠搬運貨來維持生計的碼頭勞工了?
不過就當初景星闌那一打扮,連許維新都懷疑了半天,也難怪喬鏡會這樣認為了。
男人本想解釋,但忽然靈機一,咽下了到邊的話,轉而出一副期待的表:“真的嗎?那以后的日子里,就拜托喬老師了。”
他笑瞇瞇道:“我就負責在家燒飯做菜打掃衛生,你負責掙錢養家糊口,分工愉快,怎麼樣?”
喬鏡:聽著好像哪里不太對勁?
但是哪里不對勁他也說不上來,只好點了點頭,算是同意了景星闌這個說法。
不僅如此,老實的青年還轉從書桌上了鎖的屜里拿出了一個錢袋子,認認真真數出十枚銀元,放到了男人的掌心。
景星闌:“這是?”
喬鏡:“這個月的生活費。”
景星闌:“…………”
黑發青年還一本正經地叮囑他:“十枚銀元夠用很久了,但最好還是稍微省著點兒花。最近城里價很貴,生意都不太景氣,我擔心哪天報社就發不起稿費了。”
景星闌沉默了。
他神復雜地盯著手中的十枚銀元,當初還在國外留學的那會兒,這麼多大概也就夠他買兩本教材,如今,卻了他們一家一個月的生活費……
怎麼說呢。
突然就覺,肩上的擔子又沉重了一些啊。
*
Advertisement
《東方京報》報社,許維新表愣怔地盯著自己凌的桌面。
桌上攤著的,是喬鏡通宵寫完的稿子,《眾生渡》的前三萬字。
他坐在座位上,遲遲沒有作。
不知過了多久,這位總編才長嘆一聲,點燃了一支雪茄,默默地走到了臺。
其實之前在看到《乞兒》時,許維新就有這種預了。
當時他就說過,晏河清,或者說喬鏡,十年之必能夠打響自己的名聲,在文壇上嬴得一席之地。
——現在看來,還是他想得太保守了。
這個年輕人,本不是一塊尚待打磨的璞玉,而是一顆已經基本雕刻完畢、只差一次機遇便能夠大放彩的鉆石啊!
然而,讓許維新既激又糾結的,并不是因為喬鏡這本《眾生渡》寫的不好。
恰恰是因為寫的太好了,太真實了,太誅人的心了……許維新才會擔心,這本書,恐怕會在整個社會上引起軒然大波。
寫人的文學,古往今來有很多;
寫青樓子的文學,數一數倒也不;
但是寫喬鏡這樣,宛如每一個字每一句話都淌著、讓許維新讀完一頁就必須要站起來緩一緩,等做好心理準備后才能有勇氣繼續往下看的,古往今來幾千年,也就獨此一家了。
明明是不同世、不同地域、就連容貌品都完全不一致的七名子,有秦淮河畫舫上的名,艷名遠播,訪客絡繹不絕,日日抱著琵琶唱著金陵曲,過著紙醉金迷的生活;有上海灘歌舞廳出了名的百靈鳥,一襲紅,顧盼生輝,多男人對求而不得;
還有從小生活在院喚老鴇為“媽媽”的娼/之,格天真爛漫,小小年紀不學針線紅,也不想著如何討好男人,偏偏對路過和尚講的佛經聽了迷;以及因為丈夫欠債、被當做賭債賣到城市邊緣最下等“釘棚”的年老衰妻子,盡管每日被客人和公打罵/待自難保,卻偏執地認了一條跛腳黃狗當兒子,哪怕自己著肚子,也堅持要分給它一口吃食……
這只是一個開頭,許維新不知道喬鏡想為這些子安排怎樣的結局,但他有種預,無論是書中的名還是最底層的娼/,恐怕們最后的下場都不會太好。
就連晏河清給這本書起的名字,《眾生渡》,許維新都琢磨了很久。
佛渡眾生,渡的是誰?
或者說,這些子,真的有被世人算在“眾生”這一行列中嗎?
們究竟是人,是鬼,還僅僅只是男人眼中的一個工,一個象征的符號?
們接下來會經歷什麼?會不會有好人救們于水火之中?這些人彼此之間又有什麼聯系?
許維新不知道。
但他太想知道了!
他現在就是于一種,明明知道看了心里會糾結難一陣子,但是如果看不到下文,那更完蛋了,就像是被針扎了一樣,直接難一整天。
“總編,您想好了嗎?”
由于許維新這邊遲遲不做決定,報社的其他員當然也不敢私自刊登這篇小說,他們派了一個人過來,走到許維新的辦公桌邊,小心翼翼地問道:“下周一的報紙上,這篇文,咱們究竟發還是不發?”
如果發了……到時候會產生怎樣的后果,就算許維新在報刊行業工作了多年,也是完全無法預料到的。
要知道,當下開/院這一生意之所以能合法,不僅僅是因為它是個絕對的暴利產業,方部肯定也是有很大名堂的。喬鏡這本書,就相當于是公然打臉,直接扯下了他們的遮布啊!
人人皆知皇帝的新是蓋彌彰,但是無論何時,帶頭破真相的那個人,都注定要承更多的口誅筆伐。而若是放到現實,就是一旦上頭責怪下來,不但作者晏河清會倒霉,連他們報社也會到牽連,停業整頓什麼的都算是小事了。
許維新躊躇良久,最后連里叼著的雪茄都快燃盡了,這才勉強回過神來。
他死死地攥著手中的稿子,盯著標題的《眾生渡》三個大字,干脆豁出去了,狠狠一咬牙:
“發!”
他許某人,今兒個就當一次割喂鷹的佛陀,陪著晏河清一起,渡一回這天下眾生!
猜你喜歡
-
完結643 章

冥夫夜襲:繼續,不要停
小時候訂了娃娃親,十幾年沒見過面的未婚夫車禍人亡,我為了卻他的心愿,同他冥婚,豈料守夜三更,卻被色鬼爬上了床…… 被鬼纏身,又是冥夫,我是該順從嗎? 我你走開,我和你沒有任何的關系!
144.7萬字8 16573 -
完結1183 章

滿級大佬重回快穿世界
#1V1、團寵、爽文、寵夫充氣、沙雕、黑化、偏執# 撩了就跑的茶茶做夢也冇有想到,有朝一日她竟然還會重新回到任務世界。 本以為會麵臨一個又一個的修羅場,可是冇想到回來後那些男人竟然將她寵上了天。 傲嬌總裁:今晚月色真美,不如早點睡覺; 高冷校草:作業寫完,不如早點睡覺; 斯文教授:明天還有工作,不如早點睡覺。 茶茶:睡覺就睡覺,為什麼她的腰越來越疼了呢?! 某男勾唇,邪魅一笑:乖,過來,我幫你揉揉
199.1萬字8 12381 -
完結16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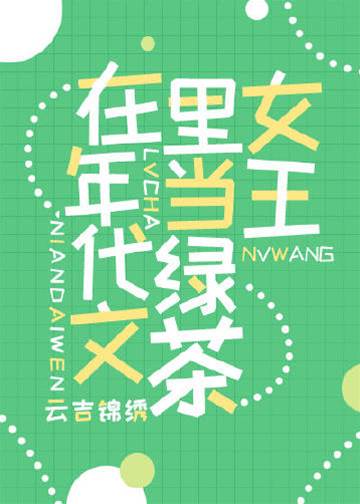
滿級綠茶在年代文躺贏
佟雪綠外號綠茶女王。她外貌明艷身材窈窕,仰慕者無數,過萬花叢而不沾身。等到玩夠了,準備做“賢妻良母”時,報應來了!她穿書了,穿到物質匱乏的七零年代,還是個身份尷尬的假千金!根據劇情,她將被重生回來的真千金按在地上摩擦臉,再被陷害嫁給二婚老男…
88.9萬字8.17 3266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