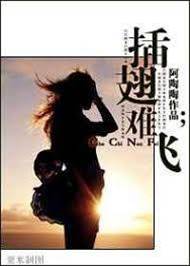《請勿高攀》 第15章 喝醉
他的嗓音低低沉沉的,像是被糲的砂紙磨過,傳耳中時有些麻麻。
舒清因抬手了耳朵,抱怨道:“你好兇。”
“你到底醉沒醉?看清楚我是誰了,”沈司岸擰著眉,傾下子仔細觀察的臉,“你是不是故意裝醉想趁機占我便宜?”
舒清因還瞇著眼,聞言又咧傻笑,“你有什麼便宜可占的?”
說完角還配合的往旁邊撇了下,做出十分不屑的樣子。
沈司岸瞇著眼看,復又捻起頰邊的一縷發纏在指中,聲音又比剛剛低了幾分,“有沒有你占占看不就知道了?”
埋在枕頭里的小腦袋又搖了搖,“我對人不興趣。”
沈司岸舌尖抵腮,眸漸暗,他不是什麼虛懷若谷的男人,給抱上床,當然不想讓其他人占了功勞。
他直接手將從床上撈起來,有力的胳膊環住的腰引坐在床上,人醉得渾無力,纖細的背脊綿綿的倚靠在他的手上,沈司岸單膝跪在床間,另只手托住晃晃悠悠的下。
的睡袍平,沈司岸到的蝴蝶骨凸出的地方和脊椎微微下陷的曲線,除此之外再沒有到任何束縛和搭扣。
他當然知道只要輕輕解開腰間的系帶,就能知道到底穿沒穿。
“睜眼,”沈司岸沉聲,“看清楚我是誰。”
舒清因睫了,眼皮宛如千斤重,間喃喃,“我想睡覺。”
被這樣托坐著并不舒服,雖然背后有只手牢牢地撐住,但還是喜歡和的床墊。
“舒清因。”
沈司岸抿,語氣中帶著薄怒和抑,掐著字眼了聲的名字。
扶著的那只手的手心正在發燙,有不可名狀的火苗徐徐燎繞至全,幾乎是拼命抑著的某種沖。
Advertisement
男人紅著眼,用氣音向問罪,“你玩我是吧?”
角向下撇,語氣含糊,“姐姐,我想睡覺,不想玩了。”
說完就真的好像要睡過去,睫不自覺地掃了掃下眼瞼,最后像把乖巧的小扇子靜靜安放著,落下一道淺淺的影,現在應該是卸了妝的,眼皮那塊兒沒有抹別的,卻又不同的瑩白,鋪著層若有若無的,和臉頰邊的天生的紅暈差不多,像是桃花瓣最深花心那部分的花蕊。
他了結,略帶急促的呼吸打在臉上。
舒清因不舒服的蹙起眉,下意識手擋住了這氣息,的指腹搭在他的間,似有似無的力道。
沈司岸忽然覺得有點,將的手抓開。
他著的指尖,像是著溫潤的玉,沈司岸垂眼看過去,發現手上還是什麼都沒裝飾。
只是這樣近的距離,才終于看到左手無名指那兒有圈小小的痕跡。
結婚了。
沈司岸從間吐出一口渾濁微熱的嘆息,最后又將放回到床上,坐在床邊邊冷靜邊發呆。
他用手肘撐著膝蓋,掌心蓋著眼睛,啟痛苦的嘖了兩聲。
再待在這兒誰都別想睡了。
冷靜過后,沈司岸下意識的了聲“Siri”想問問現在幾點了,然后才意識到他的手機落在自己房間里了。
但Siri還是回應了他。
“什麼事?”
他朝著聲音看過去,原來是的手機。
沈司岸挑眉,看來手機不怎麼認主啊。
“現在幾點?”
“現在是十一點四十八分。”
這麼晚了,沈司岸又想起今天是舒清因的生日。
好好的生日過得也不像生日,倒像是一年一次的大型企業聚會,這個壽星公好像也沒有很開心。
Advertisement
今天過去了,等下次生日就又是一年了,他想了會兒,拍了拍后微微鼓起的被子。
被子了幾下,人不耐的聲音響起,“干嘛?別吵我。”
“還兇,”沈司岸角微勾,也沒生氣,“看在你過生日的份上,陪你再呆十幾分鐘吧。”
等到十一點五十九分時,離生日過去還不到一分鐘。
沈司岸懶懶的掀起眼皮,臥室里昏黃的燈灑下溫的落影,將男人直的背映在床邊。
他漫不經心的啟了啟,而后對著沉沉睡過去的人說了句,“生日快樂。”
舒清因沒有回答,應該是徹底睡過去了。
***
次日清晨,舒清因是在床上醒過來的。
著太下床倒水喝,等走到客廳才發現這滿地的狼藉。
昨天真是放肆喝了很多。繞著客廳看了兩圈,才發現徐茜葉不知道去哪兒了。
印象中好像是送自己回酒店的,舒清因想了半天,也想不起為什麼一起床徐茜葉就不見了。
一個無業游民又不用上班,所以排除提前起床上班打卡的況。
套房門被叩響,侍應生隔著門問需不需要早餐服務。
舒清因去開了門,發現是侍應生的推車上都是些冷食的西式早餐。
宿醉過后,舒清因的胃還是不太舒服,吃不下這些填肚子的谷類,只能搖搖頭說不用了。
侍應生點頭,接著就要離開,舒清因又住他,“你不問問對門麼?”
既然是一樣的套房,那早餐服務應該也是一樣的。
侍應生回答,“沈先生昨晚不住在這里,他的早餐我已經給他送去樓下了。”
什麼意思?
但也沒心思想,今天是工作日,等收拾收拾就該去公司打卡了。
Advertisement
那侍應生正要走,剛巧在走廊盡頭看見了從電梯里出來的男人。
像是比較注重穿著的人,一般是很會這樣大搖大擺的穿著睡袍上下樓的,舒清因看到沈司岸還穿著睡袍,沉著臉朝這邊走過來的時候,一時間有些怔愣。
他的頭發還沒梳,的黑短發耷拉在額前,舒清因本能的盯著他和往日里不同尋常的地方,不知怎麼從心深浮起一淡淡的尷尬來。
張了張,撇過頭躲開了他的眼睛。
舒清因也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要躲。
沈司岸耷著眼皮一副懶洋洋的樣子,薄微抿,清俊的臉上浮起不明意味的神。
“醒了?”他拖著調子,淺眸盯著自己的房門,“這兩位酣戰一宿的還沒醒呢。”
舒清因有些懵,“什麼?”
沈司岸蹙眉,聲音有些沉,“昨晚的事兒,”然后見沖自己茫然的眨了眨眼,他又止住話,倏地扯著角不屑地笑了兩聲,“忘了是吧,我就知道。”
問他:“昨晚怎麼了?”
“你都忘了還問什麼問?”沈司岸挪開眼不再看。
舒清因看他表不太對勁,只好大膽假設小心求證,“我對你酒后了?”
“……”
沈司岸半晌才嗤了聲,“你想的。”
說完他輕輕咳了聲,不再接的茬,直接走到自己的房門口,有些不耐煩地敲門。
“起床,上早朝了。”
沒靜。
沈司岸轉頭又對舒清因說:“你打個電話給徐茜葉,讓趕起來,我和孟時今天還有事兒要辦。”
所以說徐茜葉晚上是睡在沈司岸房間里的?
頓時防備的看著他,“你對我姐做了什麼?”
沈司岸譏諷出聲,“你傻嗎?我被關在外面我能做什麼?你應該問的是你姐對孟時做了什麼。”
Advertisement
兩個人還在門外拉扯不清,酣戰一夜的人終于醒了。
徐茜葉還是穿著昨天那睡袍,像做賊一樣悄悄打開了門,然后剛打開就看見門口站著表妹和大侄子。
兩個人同時看向,憋了很久,也只能干的說:“……早。”
沈司岸揚了揚下,“孟時呢?”
“還在睡,”徐茜葉咬,面有些懊惱,“昨天喝多了,害你在外面睡了一夜,對不住啊。”
沈司岸面無表的看了兩眼,繞過進房了。
徐茜葉看著閉的房門,尷尬地鼻子,然后側又看見舒清因正冷著臉瞪。
還不等開口,舒清因涼涼出聲,“你昨天拋下我不管,在對門和別的男人睡了一夜?”
“…你聽我解釋,我那是喝多了。”
舒清因也不聽解釋,直接回房關門,留下腰還有些疼的徐茜葉在走廊上懷疑人生。
最后還是徐茜葉敲著門道歉,舒清因才勉強給開了門,盤問了有關昨天的事兒。
徐茜葉昨天晚上陪喝了不酒,又嚷嚷著要找男人,搞得徐茜葉這個做表姐也有些空虛,距離上一次談都不知道是猴年馬月了,再然后舒清因著房門非要找小帥哥道歉,好巧不巧對面房門開了,站著一個從頭到腳都長在徐茜葉審點上的酷男。
酒勁上頭,當酷男將抵在房門上和狠狠接吻時,徐茜葉整個都被火點著,恨不得化白骨給這男人吃進肚子里。
大約吻了十幾分鐘,兩個人都喝了酒,間換著彼此殘余的酒氣,孟時最后剎住了車,糙的指腹上的瓣,替去邊的銀。
男人剛接了吻,低音炮里還帶著濃重的?,問舒服嗎。
徐茜葉大腦充,迷迷糊糊的點頭。
男人揚起眉,冷的面龐染上幾分輕佻,還我侄媳嗎?
徐茜葉忽然像個心虛的罪犯,用力推開他,神惶恐,我們這樣是不對的!是會被浸豬籠的!
男人勾,接個吻就要被浸豬籠了?那待會兒你可能要直接被砍頭了。
之后男人扛著直接往里間走,天雷勾地火中,徐茜葉上是愉悅的,可是心深卻是對這段忌關系的擔憂。
和三觀沖突的雙重刺激下,徐茜葉知道自己這玩笑開大了,男人千萬不能這麼逗。
到最后男人流著汗對說只對人興趣時,徐茜葉已經沒什麼力氣再跟他開玩笑了。
“……”
舒清因聽著都覺得赤。
徐茜葉捂著臉有些不好意思,“我都多久沒男朋友了,這不也是一時糊涂。”
“算了,”舒清因扶額,“看在你拋下我之前還記得把我抱上床,這事兒我不計較了。”
徐茜葉啊了兩聲,“我記得昨天我進去之前,你還沒進房間啊。著房門要找小帥哥呢。”
“我今天是在床上醒過來的,”舒清因很篤定,“昨天是你抱我上床的。”
徐茜葉也很迷,“你做夢了吧?雖然你是比我瘦點,但我真抱不你啊,昨天是扶著你走就夠累的。”
“…那我怎麼?”
想了想,忽然睜大眼,隨后整個人陷呆滯狀態。
徐茜葉也不知道舒清因這是怎麼了,只知道從洗漱到換服,整個人都如同焉了吧唧的昨日黃花,仿佛被走了魂魄。
連口紅都能涂出峰外,要不是徐茜葉提醒,估計就頂著張香腸出門了。
兩個人也不說話,等走到停車場的時候,徐茜葉總算不放心的一把搶過手中的車鑰匙。
原本是司機早上來接回家,現在看舒清因這副樣子,實在不相信能平安無事的把車開到恒浚。
“我來開吧,就你這狀態,我還想多活幾年,”直接將舒清因趕到副駕駛,又問,“你是不是酒還沒醒啊?”
舒清因搖頭,“沒有,醒了。”
徐茜葉扣上安全帶,又想著得給司機先打個電話別讓人白跑一趟,結果停車場信號不好,手機號怎麼也撥不出去。
現在前腳走了的話,萬一后腳司機就來了怎麼辦。
但如果現在不走,等撞上通高峰期,舒清因又肯定會遲到。
“要不讓沈司岸送你去吧,”徐茜葉給出主意,“他應該快下來了,我在這兒等司機。”
“不要,”舒清因反應極快,“你在這兒等司機過來吧,我自己開車就行了。”
徐茜葉猝不及防被趕下車,眼睜睜看著表妹猛踩油門,以超高絕的倒車技,在十幾秒功將車調頭,然后留下一灘瀟灑的車尾氣。
這老司機般嫻的技,完全看不出是掛過科目二的人。
“搞什麼?”徐茜葉不明所以。
***
時間已經接近九點,沈司岸和孟時兩個大男人還沒從酒店出發。
孟時早就一清爽的坐在沙發上悠哉的喝著茶,等杯里的茶快見底了,才抬眼看著站在鏡子前系領帶的沈司岸,語氣無波,“你已經換了七條領帶了。”
沈司岸單手又扯掉了剛系好沒幾秒的領帶丟在旁邊,聲音有些悶,“今天非得去恒浚不可?”
“沈總,今天的行程是是你昨天晚上臨走前親自跟徐董約好的,”孟時淡淡的瞥了他一眼,“你想爽約?”
沈司岸走到孟時對面的沙發坐下,搭著扶手懶懶出聲,“你昨天真開葷了?”
孟時挑眉,“你問這個做什麼?”
“我看你昨天和恒浚的人聊天也沒這麼眉飛舞,我換條領帶你都催了好幾回,不就是想見徐茜葉?”沈司岸彎腰順勢也給自己倒了杯茶,語氣悠悠:“人本就不在恒浚上班,你見不到的。”
“在哪里上班?”
這句話幾乎是下意識的就問出來了。
沈司岸拖著調子,吊兒郎當的反問他:“想追?”
“有問題?”
沈司岸聳肩,“沒有,就是覺得人家既然能一聲招呼不打就走,連個聯系方式都不留給你,很明顯就是想玩419,你可能要吃閉門羹。”
孟時瞇眸,又淡淡說:“總比已婚的好。”
沈司岸握著杯柄的手忽然頓住,“……”
他再看孟時,發現這男人臉上寫滿了“來啊,互相傷害啊”幾個字。
猜你喜歡
-
完結7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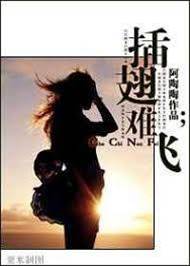
插翅難飛
美麗少女爲了逃脫人販的手心,不得不跟陰狠毒辣的陌生少年定下終生不離開他的魔鬼契約。 陰狠少年得到了自己想要的女孩,卻不知道怎樣才能讓女孩全心全意的隻陪著他。 原本他只是一個瘋子,後來爲了她,他還成了一個傻子。
23.5萬字8 17235 -
完結658 章

名門寵婚之老公太放肆
他和她的關係可以這樣來形容,她之於他,是他最愛做的事。 而他之於她,是她最不愛做的事。 ……安城有兩樣鎮城之寶,御家的勢,連家的富。 名門權貴聯姻,艷羨多少世人。 連憶晨從沒想過,有天她會跟安城第一美男攀上關係。 「為什麼是我?」 她知道,他可以選擇的對象很多。 男人想了想,瀲灧唇角勾起的笑迷人,「第一眼看到你就想睡,第二眼就想一起生兒子」 她誤以為,他總會有一句真話。 ……一夕巨變,她痛失所有。 曾經許諾天長地久的男人,留給她的,只有轟動全城的滅頂醜聞。 她身上藏匿的那個秘密,牽連到幾大家族。 當她在另一個男人手心裏綻放,完美逆襲贏回傲視所有的資本。 ……如果所有的相遇都是別後重逢,那麼他能對她做的,只有不還手,不放手! 他說:「她就是我心尖上那塊肉,若是有人動了她,那我也活不了」 什麼是愛?他能給她的愛,有好的也有壞的,卻都是全部完整的他。
106.3萬字8 71276 -
完結235 章

追妻漫漫行長的心尖寵
【京城大佬 美女畫家】【雙潔】【追妻火葬場】 陸洛晚如凝脂般的肌膚,五官精致絕倫,眉如彎月,細長而濃密,微微上挑的眼角帶著幾分嫵媚,一雙眼眸猶如清澈的秋水,深邃而靈動。 但這樣的美人卻是陸家不為人知的養女,在她的大學畢業後,陸父經常帶著她參加各種商業聚會。 …… 在一年後的一次生日派對上,原本沒有交集的兩人,被硬生生地捆綁在了一起,三年漫長的婚姻生活中一點一點地消磨點了陸洛晚滿腔的熱情,深知他不愛她,甚至厭惡她,逐漸心灰意冷。 一係列的變故中,隨著陸父的去世,陸洛晚毫不猶豫地拿出離婚協議,離了婚……從此遠離了京城,遠離沈以謙。 後來,命運的齒輪讓他們再次相遇,隻不過陸洛晚早已心如止水。 而沈以謙看著她身邊層出不窮的追求者,則不淡定了,瞬間紅了眼。 在某日喝的酩酊爛醉的沈以謙,將她按在懷中,祈求著說:“晚晚,我們重新開始好不好?” —— 都說沈以謙風光霽月,聖潔不可高攀。 在兩人獨處時陸洛晚才發現,他要多壞有多壞,要多瘋就有多瘋。 他道德高尚,也斯文敗類。他是沈以謙,更是裙下臣
46萬字8 1579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