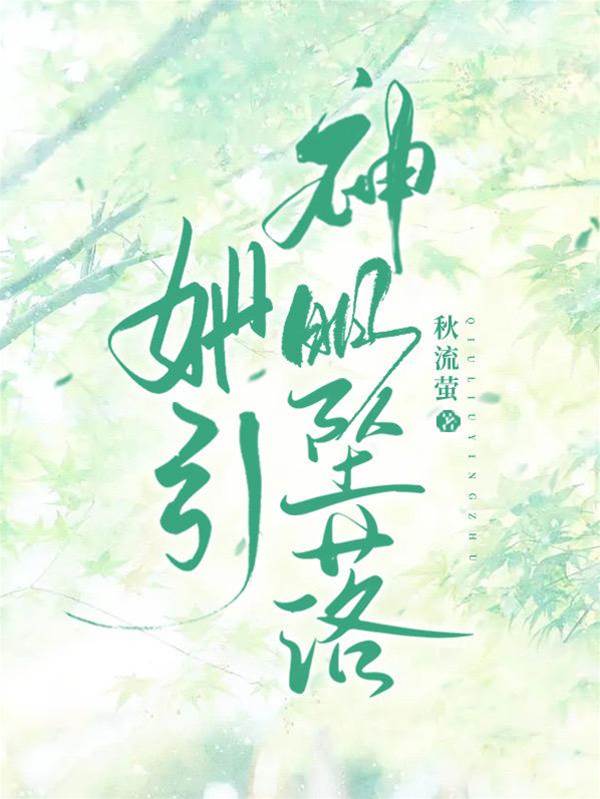《為她降落》 第54章 變故
收起手機, 車重新歸于安靜。傅南期閉眼往后靠,單手支了支太,吩咐傅平前面商場停一下。
傅平彼時正開車, 聞言道:“是要準備禮嗎?”
傅南期嗤笑:“這一大家子老老小小, 總得哄著。難得回去一趟,要是什麼都不準備, 難免被他們說閑話。你知道的,人的最碎。”
傅平涼笑:“其實不準備也沒什麼, 您跟他們也不親。”
傅南期神不, 向窗外時, 面是巋然不的冷漠, 語氣也輕飄飄的:“面子上總要過得去。”
溫淩離開酒店時,跟幾人在門口道別, 這時接到電話:“喂——”
“出來了嗎?我來接你。”傅南期在那頭道。
夜晚的寂靜讓這個人的聲音更加溫,溫淩心里也像是被一雙輕的手過似的,得不像話:“好。你在哪兒了?到了嗎……”
溫淩的聲音戛然而止, 因為看到了停靠到對面的那輛勞斯萊斯。
正要過去,小趙從后面跑過來拉住:“你沒開車過來啊老大?我送你吧。”
溫淩真不好拒絕的熱, 有點尷尬, 小趙已經看到了對面停靠下來的車子, 驚呼道:“靠!勞斯萊斯!這車牌……萬惡的資本家啊!”
溫淩輕嗽一聲, 莫名心虛:“北京街頭的豪車還嗎?你收斂點, 別太夸張。”
一旁的另一個男同事也道:“就是就是, 別跟個土包子似的。”
小趙正要懟他, 就見對面勞斯勞斯的車門開了,下來一個模樣俊朗的青年,登時眼睛一亮:“哇哦。”
原以為那儀表不凡的青年就是車主, 誰知,他繞到后座躬開了門。
這次下來的,是位穿煙灰長西裝的男士……溫淩回頭,小趙的已經張了“O型”,顯然是認出傅南期了。
Advertisement
短短的凝滯時間里,傅南期已經穿過了馬路:“好巧。”
還以為他是來赴約,沒想到竟然會跟自己這幫人說話,小趙寵若驚,話都不連貫了:“傅董您好!”
又對傅平道,“傅書你也好!”
傅平笑著點頭,問了兩句近況。溫淩知道,這是他慣常敷衍的態度,小趙卻像是被迷了心竅似的,一腦兒說了大堆出來。
好不容易送走這幫人,溫淩松了口氣,心道差點餡,又看向傅南期,暗含抱怨:“你怎麼直接過來了啊?”
“怎麼,我很見得不人嗎?”
“我不是這個意思。”不知道怎麼解釋,撓撓頭。
傅南期不逗了,在肩上微微推了把:“走吧,先上車。”
“嗯。”
上去后才知道,他這是要回老家看家人。溫淩張起來:“那我還是不去了吧。”
他看一眼:“我爺爺很和氣的,不用怕。”
還是不放心:“……那你爸媽呢?”
他頓了下,道:“我媽早年一直在加拿大生活,前年回來了,現下里在南京,很回來。我爸……”他想了想,道,“他人有點嚴肅,不過,不會沒事找事地為難人。”
他這話不但沒有安到,反而更加忐忑了:“……你說的我心里更沒底了,我還是不去了吧?”
他反而笑了:“你也有怕的時候?平時懟我不是很厲害的嗎?”
垂頭喪氣的:“那能一樣嗎?而且,我什麼時候懟你啊?我哪里敢!”
“真不敢?”他噙著笑。
“你正經點好不好?!說正事兒呢!”
話題又扯回來,傅南期想了想,又加了句:“就算他不喜歡你也沒關系,我喜歡就行了。我的事,從來都是我自己做主的,他們都管不到我,也很管我。”
Advertisement
他雖這麼說,溫淩還是愁云慘淡,一路上都哭喪著一張臉,猶如要趕赴刑場的死刑犯。
傅平都樂得不行,打趣:“要不你去畫個臉譜,就說你是唱戲的,今天剛唱完一場就被傅總拉來了,太匆忙了,妝還來不及卸呢。這樣,他們就認不出你了。”
“呸!狗里吐不出象牙!”他就跟杠上了是吧?
這樣七上八下的心一直持續到過崗亭、進大院,再進他家門。
傅南期果然沒有欺騙,他父親雖然年過半百,頭發烏黑,竟沒有一雜,神也非常矍鑠。
看到,目淡掃,說不出是喜歡還是不喜歡,只點了點頭,抬手讓坐下。
溫淩有些拘謹地在對面沙發里坐下。
之前就聽人說過,他父親是從政的,母親早年也是,不過后來退了,離婚后移居國外從商去了。
不管是傅家還是蔣家,都是非常顯赫的家族,祖上幾代的政治彩都比較濃郁。
溫淩進門時悄悄打量了一下,屋子是中式風格,擺設、裝飾都方方正正,很符合他這樣的家庭背景。
“我去給你們倒水。”傅南期起笑道。
溫淩在心里大大罵他不上道,但此此景,只能干笑著任由他走遠。
客廳里,便只剩下和傅憲兩人。
溫淩更加正襟危坐,大氣不敢出。
終于知道,傅南期上那子渾然天的威儀是怎麼回事了。跟眼前這位大叔比起來,傅南期顯得隨和溫多了。
當然,也不是說他兇,哪怕他什麼都不做,只是坐在那邊,就給人一種說不出的迫,讓人不由提起十二分小心。好在,他從始至終沒有為難,只問了些工作上的問題。
聽到是H大畢業且師從王耀慶院士時,看向,目中多了一份重視,笑了笑:“我跟王院士也算是老朋友了。學的是機械類的?你是哪一屆的?”
Advertisement
溫淩寵若驚,這才發現這人笑起來也是非常好看的,雖然眼尾已有了細紋,廓深邃,骨相清正,板更是拔如松。看得出來,年輕時必然也是一個不可多得的男子。
因為這一笑,溫淩忽然覺得他沒有那麼難以接近了,后來聊到自己專業和擅長的領域,更是來了興致,滔滔不絕,再沒有一開始的小心翼翼和拘束。
“聊得投緣?”傅南期端著兩杯茶回來,笑一笑,在邊坐下。
氣氛漸漸融洽起來。
雖然傅憲并不算一個和藹的人,溫淩卻沒有那麼害怕了,覺他比初見時更多一份親切。
尤其是說起他和王院士的一些往事時。
溫淩聲說:“老師現在在H大后面種起了地,都快把那一片地方劃私有了。不止有蔬菜糧食,還有茶葉呢。您要嗎?下次我去看他,幫您帶一點?”
傅憲笑了笑,呷一口茶:“那下次代我跟他問好。”
“嗯。”回答地鄭重。
在低頭喝茶時,傅憲不聲打量了會兒,這才收回目,邊多了不易察覺的笑意。
傅老爺子今天不在,其余人也不在家,溫淩只見了傅憲。
傅南期還要留下說會兒話,囑托傅平把送回。
溫淩這就告辭了。
傅南期一直送到門口,這才折返回大廳。
傅憲還在喝茶,滾燙的水下去,茶葉已經在玻璃杯里盡數泡開。他慢慢抿一口,才道:“認真的?”
傅南期淡笑著坐下:“我可沒有結幾次婚的打算。”
傅憲倒沒生氣,呵呵一笑:“人的一生很長,不同階段會有不同的悟和變數。你就能保證以后不會再離婚?”
傅南期小時候很討厭他看似淡然實則高高在上、一切都在掌控中的態度,長大以后發現,人在那個位置,往往不由己。
Advertisement
比如他現在,耳濡墨染加上自己的能力,至也不會在他面前落下風。
“人倒是長得漂亮的,雖然家世普通,氣質禮貌還可以。”傅憲道。
能得他這樣的評價,已經極為難得。
傅南期:“那我就放心了。”
傅憲看他一眼:“你爺爺那兒呢?跟簡家的事,你打算怎麼理?”
傅南期毫不在意:“那不是問題。”
傅憲看他會兒,還是告誡:“簡家丫頭可不是個省油的燈,別太過了,給人家留幾分面。”
“我知道了。”
他起跟他告辭,都要走了,傅憲不輕不重道:“聽說這丫頭以前是你弟弟的朋友。”
傅南期腳步停住,回頭:“您聽誰說的?”
這兄弟倆一樣,被人質問,永遠不會理虧,而是反客為主質問別人——傅憲道:“這不重要。我只是要你知道,你弟弟再怎麼樣也是弟弟,的事,別跟這些恩恩怨怨的混在一起,免得到時候后悔。”
他說得晦,其中的含義卻已經非常明顯。
傅南期漠然,半晌才道:“我跟是我跟的事,跟阿宴沒有關系……”
傅憲擺手打斷他,端著茶杯朝樓上去了:“有這句話就夠了。其余的事,你自己理。”
……
傅南期晚上10點多才回來,還給帶了一盒草莓。
溫淩洗干凈后,仔細去葉,抓了兩顆到里:“甜——”
“甜和酸,有時候只是人的主觀覺。”他也捻了一顆來吃,吃完后,皺皺眉,回了手。
“你們男人的抗酸和抗疼痛能力都很弱。”語氣嫌棄。
傅南期看一眼,失笑,拿紙巾拭上面沾到的水漬:“今天見過我爸了,什麼覺?”
溫淩還真被他問到了,猶豫會兒,道:“……頭發很黑,很神……”
傅南期頓了下,旋即笑出來,一點不客氣:“他那是染的。”
溫淩:“……”
新的一周,天氣繼續降溫,溫淩把能翻出來的服都搬到了傅南期這邊。
早上整理的時候,主臥房間的六個柜基本被塞滿了。占五個半,他半個,堪稱不可思議。
溫淩便用除螨儀整理床褥邊假惺惺地說:“我也不知道我的服怎麼會這麼多啊,覺沒多啊,以前想換兩件都找不到能換的呢。”
傅南期端著清咖在旁邊道:“每種款式都要來一件,每種也要占全,按照你這個標準,確實是不夠啊,應該把整個商場都買下來,或者自己開一家。”
溫淩撣大的手停住:“……”竟覺得他說的有幾分道理。
當然,里是不會承認的。
到了公司,溫淩召開了一個全會議,終于把產品的推廣和銷售方案和制定了。首先是分批次,聯絡之前就準備合作的公司,剩下的渠道,則由紫這個合作方來敲定——這也是一早就談好的。
本是兩全其的好事。但是,不知為何,這日下午部急召開了一個會議,這事兒就擱置了。
會議結束后,溫淩追了上去:“師兄,這怎麼回事啊?上面有什麼新的指示嗎?”
許述安似有難言之,頗為閃爍其詞:“的,我也不是很清楚,是上面下達的指令,我們照辦就是了。”
溫淩卻察覺出了不安的苗頭。
在A融資的時候,陳家恕和傅南期已經談妥,關于份占比和銷售渠道等方面的相關事宜。
不過H5的大獲功遠遠超出預期,反而打了計劃。加上后期融資新加的幾方,這個權衡就更加失衡。利益往往驅使人鋌而走險,瓜分不均,更容易出問題。陳家恕又是個老油條,在利益面前,和稀泥也是極為常見的事。
只是,這麼直接地打傅南期的臉,恐怕局面……溫淩憂心忡忡地回到座位上,進門時卻遇到了任淼。
剛從洗手間出來,正對著鏡子補口紅。
溫淩神思不屬,也沒怎麼看路,差點跟撞上。
任淼堪堪剎住時,臉難看,不過,不知道是想到了什麼,倏忽又笑起來。
溫淩面無表,眼里的厭煩不加掩飾:“好狗不擋道。”
任淼面一厲,連連冷笑:“你也囂張不了多久了,不看看現在是什麼形勢?我要是你,就快點引咎辭職或者跳槽,免得到時候里外不是人。”
肩而過的時候,任淼狠狠撞了一下。
溫淩按住左肩,回頭時,已經沒影了。肩膀上傳來的陣陣酸痛不斷提醒著,這一切都是真實的。
猜你喜歡
-
完結997 章

重生后我逃婚了
林甘棠重生回來時,神父正在問她:“你是否願意嫁他為妻?不論他生病或健康、富有或貧窮,始終忠於他,直到離開這個世界?”上一世的悲劇,從她深愛顧某開始。林甘棠:“我不願意。”賓客嘩然。 ——人人皆知溫晏清愛了林甘棠整整八年,但林甘棠從不曾回頭看他。新郎不是他,溫晏清黯然離去,遠走他鄉。卻得知新娘逃了婚。林甘棠有千萬個方法挽回日漸離心的親人摯友,唯獨對溫晏清,曾將他的真心欺過辱過踐踏過,不知該怎麼辦。林甘棠:“好難,總不能以身相許欺騙他啊。”“?”溫晏清:“求之不得。”
89.1萬字5 97323 -
完結997 章

白月光替身只想暴富
季彤一直有個愿望,就是給霸道總裁的白月光當替身:霸總把她養在私人別墅里,每個月給她上百萬的零花錢,平時什麼都不用她干,只在特定的時候讓霸總看兩眼,然后透過她的臉懷念遠走的白月光初戀。等到白月光初戀回來了,霸總就扔給她一張巨額支票加幾棟房子,惡狠狠的對她說:拿著這些錢滾,滾得越遠越好!季彤保證,自己一定是最敬業的白月光替身!直到有一天她穿進了古早霸總文里——霸總狗男人:彤彤,我愛你。季彤:當初白紙黑字簽的合同,說好只談錢不走心的!霸總狗男人:再給我一次機會。季彤:那是另外的價錢!
99.3萬字8 15607 -
連載3312 章
全城人都等我成寡婦
父親公司瀕臨倒閉,秦安安被後媽嫁給身患惡疾的大人物傅時霆。所有人都等著看她被傅家趕出門。 不久,傅時霆意外甦醒。 醒來後的他,陰鷙暴戾:“秦安安,就算你懷上我的孩子,我也會親手掐死他!” 四年後,秦安安攜天才龍鳳寶寶回國。 她指著財經節目上傅時霆的臉,對寶寶們交待:“以後碰到這個男人繞道走,不然他會掐死你們。” 晚上,大寶黑進傅時霆的電腦,留下戰書——混蛋,你來掐我呀!
300.5萬字8 85527 -
完結10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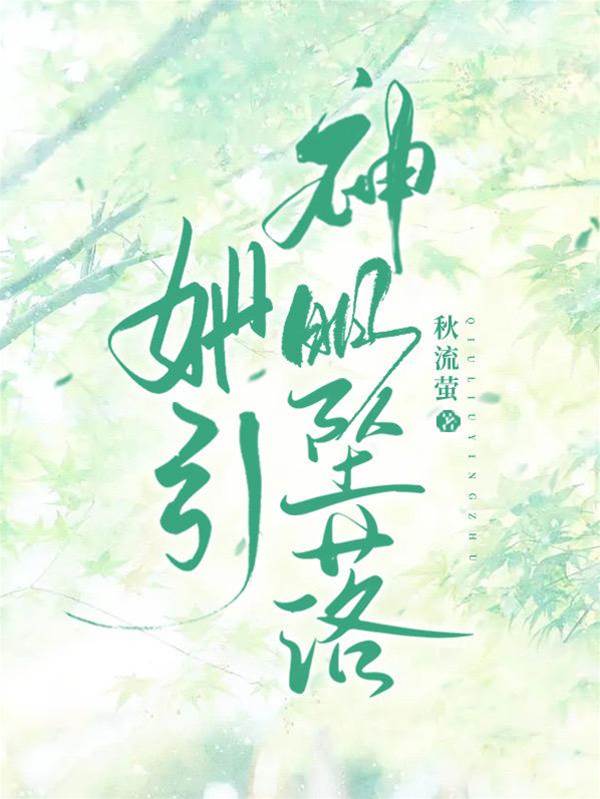
她引神明墜落
沈黛怡出身京北醫學世家,這年,低調的母親生日突然舉辦宴席,各大名門紛紛前來祝福,她喜提相親。相親那天,下著紛飛小雪。年少時曾喜歡過的人就坐在她相親對象隔壁宛若高山白雪,天上神子的男人,一如當年,矜貴脫俗,高不可攀,叫人不敢染指。沈黛怡想起當年纏著他的英勇事蹟,恨不得扭頭就走。“你這些年性情變化挺大的。”“有沒有可能是我們現在不熟。”宋清衍想起沈黛怡當年追在自己身邊,聲音嬌嗲慣會撒嬌,宛若妖女,勾他纏他。小妖女不告而別,時隔多年再相遇,對他疏離避而不及。不管如何,神子要收妖,豈是她能跑得掉。某天,宋清衍手上多出一枚婚戒,他結婚了。眾人驚呼,詫異不已。他們都以為,宋清衍結婚,不過只是為了家族傳宗接代,那位宋太太,名副其實工具人。直到有人看見,高貴在上的男人摟著一個女人親的難以自控。視頻一發出去,薄情寡欲的神子人設崩了!眾人皆說宋清衍高不可攀,無人能染指,可沈黛怡一笑,便潦倒萬物眾生,引他墜落。誰說神明不入凡塵,在沈黛怡面前,他不過一介凡夫俗 子。
20.2萬字8 44400 -
完結594 章

顧總求你別虐,夫人她快死了
【虐身虐心 男女主雙潔 偏執占有欲】 蘇佳夢救了顧承離兩次,一次將他從大火裏背出,一次捐骨髓治好他的白血病,卻換來他一句“我一定要讓你生不如死!” 顧承離認定她殺了他的心上人,恨她生下的自閉癥兒子,恨她霸占顧太太之位! 直到蘇佳夢跳下萬丈高樓,他才明白此生摯愛,原來是她…… 重活一次,她改名換臉,桃花不斷,小奶狗大叔型男圍著轉,而顧承離單膝跪地,當著眾人的麵,親吻她斷了兩根腳趾的腳背……
50.6萬字8 28945 -
完結385 章

閣樓裏囚著病嬌大佬的金絲雀
【1v1男主大病嬌?偏執瘋批?女主軟糯芭比】本文是牆紙病態愛,非女強,不喜勿點進去!!!雍城最尊貴的男人夜寒沉一眼看中了寧桑桑。為了將小姑娘搞到手,他一句話就讓寧桑桑父母破產。逼得寧桑桑父母將女兒親手奉上。他成功占有了心愛的小姑娘,本來想好好寵溺疼愛她,可她竟然心裏有別人。夜寒沉隻能嗜血的咬上小姑娘的脖子,留下印記,把她偏執瘋狂的關在婚房的閣樓上,日日疼愛,一步都不準離開!
35.6萬字8 1472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