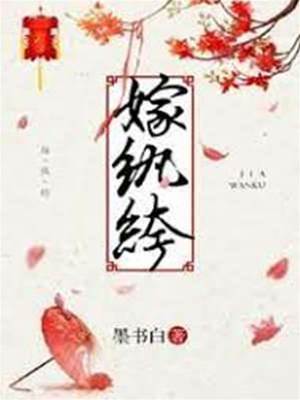《掌上齊眉》 第319章 謝云宴,你別弄丟了我
“你弟弟走丟之后,他報了嗎?”
謝云宴一針見。
蘇錦沅臉蒼白。
蘇萬全領著人四尋找,每天都是早出晚歸,足足找了大半個月,每天回來時都是哭喪著臉紅著眼睛,要麼是抱著掉眼淚,要不然就是哭著說對不起爹爹。
等到大半月后,京中老太太傳信說是子不行了。
蘇萬全才不得不放棄了尋找阿,帶著回京。
……可他從頭到尾都沒報。
“南也不是小地方,城門守衛,城中巡邏都不缺,就算他自己位低微調不了地方府的人,可你父親和汪大人關系莫逆,你又跟蕭家定有婚約。”
“那時候的蕭家在整個大晉朝中都是數一數二的門戶,權勢如日中天,汪大人雖不如現在,卻也不是無名之輩。”
“只要蘇萬全去了府,以蕭家和汪家的名義追究此事,讓南城守下命鎖了城門,派府衙中人城中搜捕,未必找不回你弟弟。”
假如蘇錦樂走丟是意外,或是被人擄了,驚府全城搜捕,總能找到線索,而且那些拍花子最怕的就是擄到權貴人家的孩子,怕惹來禍事。
但凡聽聞府出,至有五的幾率會將人直接送回城里。
蘇萬全蠢嗎?
他不蠢,他要是真蠢,也不可能瞞得住蕭家這麼多年,明明苛待蘇錦沅,卻還站著婚約的關系從蕭家換取好。
他既然不蠢,也知道府衙之事的那些道道。
那他明知道蘇錦樂丟了,為什麼不去報,反而只自己私下尋找,做出了一副急切之相,將年的蘇錦沅哄得團團轉。
蘇錦沅臉上散了個干凈,咬著時,神難看至極:“你是說……是他們……”
Advertisement
“我也只是猜測。”
謝云宴說道:“我從不想用惡意去揣測旁人,可是蘇家的人不同。”
“余氏這麼多年苛待于你,蘇萬全不可能不知道,他要是真的還記得你父親,念著跟你們的脈親,他就不可能像是之前那樣坐視不理。”
見微知著,蘇萬全對他弟弟,還有他弟弟留下的脈也并沒有那麼看重。
“我記得你之前曾經說過,你父親走后留下了一大筆錢財,還有一些人脈,蘇萬全和余氏去涇川接你們時,極有可能是沖著這些東西,還有你上跟蕭家的婚約。”
“你父親是為了救將軍而死,將軍重義,既定下婚約就一定會照拂你們姐弟,而在蕭家眼皮子底下,他絕無可能強占了你父親留下的東西。”
“人總是不知足的,貪心蒙蔽了雙眼時,什麼樣的惡事都做的出來。”
蘇錦樂要是還在,等他長大年之后,有蕭家撐腰。
蘇萬全就得將那些東西全數還給他們姐弟,否則就會背上謀奪弟弟家產的惡名,蕭家也絕不會放過他。
可要是沒了蘇錦樂,只剩下一個蘇錦沅。
只要哄得住,又是外嫁,給多東西給全都由得蘇萬全說了算。
蘇錦沅不提,蕭家也不會主去幫要那些東西,否則便會落得個貪圖蘇錦沅嫁妝的名聲。
謝云宴低聲道:“余氏的惡毒都是表面的,蘇萬全的冷漠絕藏得更深。”
“你弟弟走失的事也許真的只是意外,可是以你們當時的年紀,還有蘇家后來對你的態度,以及蘇萬全這些年從未提及過你父親留下之半句。”
“他不是沒有可能為著錢財朝你們手。”
蘇錦沅臉格外難看。
有些事不提從沒去想,可當有人提起之后,再去想起當年阿走丟的事,就能發現蘇萬全和余氏的古怪。
Advertisement
剛從涇川離開時,他們幾乎寸步不離地守著和阿。
傷心爹爹的死,對什麼都提不起興趣,阿就也跟著,哪里都不去。
那天夜里,是蘇萬全說南城熱鬧,要帶他們出去看花燈散心,也是他拉著他們一路走到了熱鬧的地方,卻突然說要去買點東西,將和阿放在了人群里。
到底是個孩子,被那些新鮮玩意引了心神,顧及不到阿。
可是余氏呢,還有一路上跟著他們的那些蘇家的下人。
怎麼就那麼巧全被人流沖散了,沒有一個人瞧見阿丟了?
蘇錦沅還記得,阿剛走丟時,無論是蘇萬全還是余氏都格外自責,說起阿就會掉眼淚,可是等回了京城見到老太太之后,兩人就鮮再提燈會上的事。
反而是老太太,不知道為什麼認定了是克星,覺得是弄丟了阿。
蘇萬全沒有反駁,余氏也沒有解釋。
周圍所有人都說,是因為貪玩,才會將阿弄丟了。
漸漸地,老太太罵,蘇心月也說,就連余氏也改口說是因為,阿才會走丟。
說的人多了,也就覺得真的是因為自己才將阿弄不見了,卻忘記了當時也才不過六歲,的容貌不差,比起阿來說更是個容易出手的孩兒。
若是真有人趁拐走了阿,又怎麼會放過同樣年的?
大概是因為,上還有蕭家的婚約。
蕭家的人也絕不會讓恩人的兒全數出事,所以蘇萬全不敢,也舍不得“弄丟”了?
蘇錦沅眼中出恨意:
“蘇!萬!全!”
他奪了爹爹留下的家產,不恨。
他視而不見余氏苛待,也不怨。
因為知道,寄人籬下本就是如此。
Advertisement
可如果真是他故意弄丟了阿,只為了爹爹留下的那些東西,跟他不共戴天!!
蘇錦沅“唰”地起:“我要回京城。”
謝云宴拉著:“回去做什麼?時隔這麼多年,就算當初真的是他故意,他也不會承認。”
將人拉著坐回了遠,謝云宴才蹲在面前說道:
“你先別急,我會立刻傳信給程叔,讓他去查當年的事。”
“如果真是蘇萬全做的,他定然會咬死不認,不過余氏是個守不住的,而且他們那時候既然帶的有下人同路,總會有人知。”
“我讓程叔先從余氏和當年蘇家那些老人那邊下手,實在不行,還有蘇心月,進了康王府不會好過,余氏那麼寵著,也許能知道一些事。”
謝云宴抬頭看著淚流滿面的蘇錦沅,手拂去臉上眼淚,一字一句地道,
“你信我,我會幫你找到弟弟。”
“如果真是他們做的,我也絕不會放過害了弟弟的人。”
他聲音微沉,帶著不容置疑的認真,一點一點的將心中的怨恨和焦慮平。
“別怕,我在。”
蘇錦沅眼淚洶涌。
自從爹爹死后,就再也沒有人跟說過這樣的話。
告訴,別怕,他一直都在。
眼淚眶而出,還沒落下就被他手盡。
謝云宴將臉上的眼淚掉之后,這才拿著錦帕替著手心上的跡,眉峰輕蹙時,臉上是不自覺流的心疼。
他向來傲骨嶙峋,立于人前從不跟人低頭。
可此時就那麼半蹲在前,用他那滿是薄繭的手小心翼翼地拭著掌心里的傷口,像是捧著珍寶,生怕損傷了半點。
蘇錦沅像是被什麼擊中,紅著眼時突然狼狽:“謝云宴……”
Advertisement
“嗯?”
他抬眼。
蘇錦沅展手指,握著他的手:“你要一直跟著我。”
謝云宴愣了一下,猛地抬頭看:“你說什麼?”
蘇錦沅眼神瑟了下,卻頭一次沒有避開,反而聲音沙啞的說道:“我說,別弄丟了我。”
掌心是從未有過的溫熱,耳邊的言語也是如此的真實。
他眼眸瞪大時有些難以置信,可當對上水跡未干卻澄澈漆黑的雙眼時,看到眼里的認真,所有的猜疑和不敢置信,都漸漸化了得償所愿的狂喜。
謝云宴小心翼翼地松開,然后又一點一點的試探著與十指纏,見未曾拒絕,手心便越握越。
沒有拒絕,也沒有掙。
眼前的人溫順至極。
“阿沅。”謝云宴輕喚。
蘇錦沅抿抿,低“嗯”了一聲。
“阿沅。”
又喚了一聲。
蘇錦沅瞪他。
仿佛得到回應,謝云宴角瞬間揚起,他抓著手心時,黑眸里乍然開波,粼粼細浪之下,那眼神之中全是掩飾不住的歡喜。
蘇錦沅被他臉上笑容煞到,有些不好意思移開眼,卻更多是從心底蔓延而出的喜悅。
想要出手,卻被他握得的,只能低聲道:“松手。”
謝云宴哪肯答應:“不要!”
蘇錦沅臉頰微:“你抓得我手疼。”
謝云宴這才想起手心還有傷,連忙松開手時,就見跡染在了自己掌心上,頓時懊惱,連忙拿著帕子替跡:“對不起,我剛才忘記了。”
“怎麼樣,疼不疼,要不我去找個大夫來……”
蘇錦沅連忙一把抓著他袖子,就只是掐破了點兒皮,要真找個大夫來,那得多丟人,將人拽了回來,說道:“就只是破了點皮,別去了。”
謝云宴只能蹲了回去,替吹了吹掌心。
蘇錦沅指尖微蜷,到底不好意思,連忙就想將手回來。
“夫人,茶煮好……”
珍珠端著煮好的茶水從小廚房那邊出來,剛過廊下就看到院中一幕。
天還沒徹底暗下去,一眼就看到了那石桌前面,謝云宴蹲在蘇錦沅前。
穿著玄的六公子拉著大夫人的手,低頭看著掌心,神虔誠而又熱烈,他低頭在指尖輕了下,眼里藏著的是毫不掩飾的慕。
“砰——”
珍珠手里端著的東西落了一地。
猜你喜歡
-
完結18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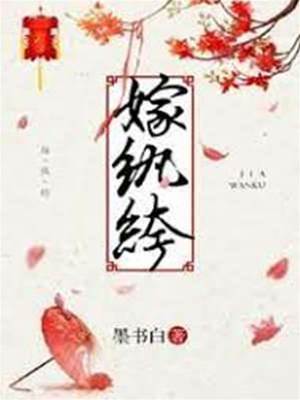
嫁紈绔
柳玉茹為了嫁給一個好夫婿,當了十五年的模范閨秀,卻在訂婚前夕,被逼嫁給了名滿揚州的紈绔顧九思。 嫁了這麼一人,算是毀了這輩子, 尤其是嫁過去之后才知道,這人也是被逼娶的她。 柳玉茹心死如灰,把自己關在房間里三天后,她悟了。 嫁了這樣的紈绔,還當什麼閨秀。 于是成婚第三天,這位出了名溫婉的閨秀抖著手、提著刀、用盡畢生勇氣上了青樓, 同爛醉如泥的顧九思說了一句—— 起來。 之后顧九思一生大起大落, 從落魄紈绔到官居一品,都是這女人站在他身邊, 用嬌弱又單薄的身子扶著他,同他說:“起來。” 于是哪怕他被人碎骨削肉,也要從泥濘中掙扎而起,咬牙背起她,走過這一生。 而對于柳玉茹而言,前十五年,她以為活著是為了找個好男人。 直到遇見顧九思,她才明白,一個好的男人會讓你知道,你活著,你只是為了你自己。 ——愿以此身血肉遮風擋雨,護她衣裙無塵,鬢角無霜。
81.5萬字8.46 48725 -
連載1636 章

絕世萌寶:神醫娘親超厲害
大齊國的人都以為瑾王妃隻是個寡婦,瑾王府也任人可欺。可有一天,他們發現—— 神醫門的門主喊她老祖宗。天下第一的醫館是她開的。遍布全世界的酒樓也是她的。讓各國皇帝都畏懼的勢力是她的外祖家。就連傳說中身亡的夜瑾居然都回來了,更是將她疼之入骨,寵入心髒。“天下是你的,本王的錢是你的,兒子也是你的,本王同樣是你的。”
146.8萬字8 114941 -
完結165 章

名門醫妃
韓雪晴穿越到古代,成為寧瑾華的王妃,安然病了,韓雪晴是唯一一個能救她的人,生的希望握在她的手里。不過慶幸的是她曾是一名現代的優秀外科醫生,是一個拿著手術刀混飯吃的她在這里一般的傷病都難不到她,只是這個世界不是那般平靜如水,有人在嫉妒她,有人想讓她死……
44.6萬字8 8301 -
連載252 章

替嫡姐與權臣洞房後
《替嫡姐與權臣洞房後》【清冷權臣為愛下高臺】【強取豪奪】【追妻火葬場】【甜寵先婚後愛】徐望月有個秘密。長姐身體不適,每晚上與侯爺同房的人其實都是她。原本以為這個秘密無人知曉,可是近來她越發覺得不對。那位清冷侯爺晚上將她弄疼之後,第二日總會有意無意問她怎麼也扭傷了腰,白天對她有多清冷,晚上就會瘋得她受不住。徐望月
53.6萬字8.18 2349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