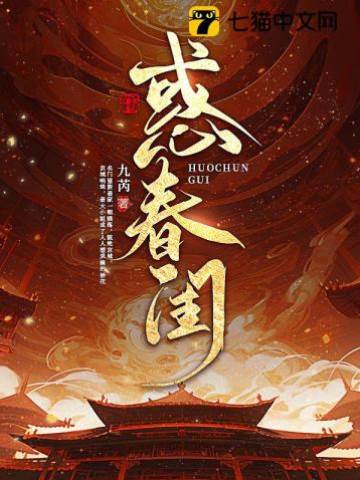《白日提燈》 第81章 瞑試
史彪和丁進出其不意,按照段胥的布置快速切斷了起義軍和丹支軍隊的聯系。同時在紫微的幫助下,唐德全投靠丹支的消息傳得沸沸揚揚,唐德全的部下十之七八都轉投了段胥麾下。唐德全還沒來得及出賣他們就已經變了孤家寡人,倉皇地跑去了丹支的地盤尋求庇護。
這下景州全境的三分之二就落到了段胥手里,他以歸鶴軍和孟晚的肅英軍為前鋒繼續攻打景州剩下的幾座城池。史彪曾經占山為王,對于山地的埋伏和攻擊最為練,戰法又非常無賴,最擅長以勝多聲東擊西,在戰場上大放異彩。丹支最引以為傲的的騎兵乃是護齊全的重騎兵,在山地不好施展,于是被史彪弄得疲于奔命。
孟晚帶的肅英軍就沉穩許多,史彪善于攻城卻不善于防守,一座城能在他手上來來回回數易其主。于是他們便配合著,突破由史彪來,穩固占據由肅英軍來,半個月的時間一點點把景州吃了下去。
在這時段胥適時地給齊州的起義軍首領趙興寫了一封信。趙興掌握齊州有一段時間了,大梁這邊涉的使臣也去了一波又一波,眼見著蔚州的錢將軍都歸了大梁,趙興卻還含糊其辭。
說實話,大梁給錢義的封賞十分厚,趙興也絕不會得。他明知如此還是態度曖昧,對于景州的起義作壁上觀,怕是想要渾水魚自己做一方霸主。
段胥這封信語氣很客氣,但是話里的容卻實在,叛歸丹支的唐德全被漢人義士砍了腦袋棄尸大街,趙興要是投丹支估計也是這麼個下場。他段胥之后要打幽州,就需要齊州這塊地方與景州一起合圍突破,要是趙興不肯歸順,那他怎麼打下景州的,就怎麼打齊州。到時候趙興可就不是功臣,而是逆賊了。
Advertisement
這封信到了沒多久,趙興便派來使者說愿意接大梁的封賞,將齊州獻出。
“趙興此人狡猾,他答應了要歸順但是此中大約還有波折,且往后看著。之后我們要打幽州,齊州是軍隊后方必須安穩。夏慶生為人謹慎認真,先讓他去齊州會會趙興,整頓他的兵馬,我隨后就去。”段胥放下趙興的信,吩咐沉英道。
沉英點點頭。
“紫微在齊州有可用之人麼?”
“姐姐說,趙興邊的參軍張遣是紫微的人,此前留意觀察過,此人可信。”
“好。讓夏慶生到齊州后和張遣聯絡,若是慶生也認為張遣可用,便將趙興的舊部銳到張遣手里。趙興赴南都封前,紫微要盯了他。”
沉英道:“是。”
段胥松了一口氣,突然調轉話題道:“你韓大哥現在怎麼樣了?”
這還是段胥這半個多月來第一次提到韓令秋。他一回來就把韓令秋丟進了監獄里關著,期間也沒怎麼問過,對外就找了個韓令秋沖撞主帥故而罰的說辭。
沉英之前四個月了韓令秋很多關照,眼見著韓令秋回來整個人都不一樣了,沉沉的一言不發。韓令秋和段胥之前的氣氛也非常奇怪,心里早就犯嘀咕,此刻聽到段胥提起韓令秋不由得一個激靈,心說三哥終于提起這茬了,急不可耐道:“還是老樣子……整天不說話,我跟他聊天他也不回應我。三哥,韓大哥到底是怎麼了?”
段胥長嘆一聲,笑道:“你他大哥,我三哥,我這輩分被你憑空喊小了。”
他從椅子上站起來懶腰,道:“走,我們去看看他,既然他自己想不清楚我就幫他想清楚。”
沉英納悶地跟著段胥一路到了監獄,段胥背著手閑庭信步走到欄桿前,轉過看著角落那個頭發散,神郁的人。半個月過去韓令秋上的傷已經愈合得差不多了,但是心上的傷顯然仍未痊愈。他和之前那個認真、誠懇又簡單的韓令秋判若兩人,仿佛有別人的靈魂被塞進了這個里。
Advertisement
不過他的遭遇也差不多是這樣。
天知曉為蒼神戰的年不能接大梁的將軍韓令秋。
保家衛國的韓令秋也不能接天知曉滿手鮮濫殺無辜的年。
他有兩段截然相反,互相為敵的過往。如今那些他在天知曉到的教育,曾經篤信的信念又回到了他的腦子里。他曾經信誓旦旦地說不論過去如何他只是大梁的韓令秋,如今看來這只是好而一廂愿的幻想。
段胥打開門鎖,門鎖打開的聲音在空闊的牢房里回響,他一邊開鎖一邊喚道:“韓令秋。”
韓令秋的目驀然轉向他,目里含著警惕和恨意,他冷冷地說道:“別我這個名字。”
“怎麼,這個名字又不是我給你起的,你現在還怪起我來了不?”段胥走到韓令秋的面前,他俯下去著韓令秋,笑道:“你要記得,你還掐過我的脖子。在那樣的場面下你對我手,我可以視作背叛。”
韓令秋眸了,繼而冷笑一聲說:“背叛?這不是你的拿手好戲。”
段胥直起來,他挲著手里的鑰匙低眸看著韓令秋片刻,繼而說道:“你用這樣的語氣對你的主帥說話,看來是完全不想做韓令秋了啊。你已經決定回丹支了?”
韓令秋卻咬著牙,一言不發了。
“令秋,要不要再和我來一場暝試?”段胥這樣說道,不出意外地看見了韓令秋驚詫的目,他補充道:“暝試便是你死我活,如果你贏了,可以殺死我。”
午后的云州草場上,淺淺的湖泊上波粼粼地映著明溫暖的,青的草長得很高,能夠淹沒人的腳踝。此時無風,一切安好。
段胥和韓令秋兩個人遙遙相對站在下湖泊邊,兩個人皆著黑,段胥戴著黑銀錯的抹額,便如他行走鬼界時那樣,看起來一點兒也不像是一軍統帥,仿佛只是個無憂無慮的年。
Advertisement
韓令秋遠遠地看著段胥,仿佛隔著了九年的歲月,看見了天知曉里那個優秀得讓人仰的對手。段胥比那時候更高大,骨骼生得更有棱角,除此之外和天知曉里那個他沒有太多區別。在天知曉的時候段胥就是這樣日里笑眼彎彎,好像沒有任何煩惱。
韓令秋恍惚地想他羨慕過段胥麼?好像有過的,或許是因為段胥的天賦、師父的偏、或者是因為段胥的快樂,他已經記不太清了。那個時候他們沒有名字,沒有朋友,段胥對他來說也只是個符號。
在那段漫長的歲月里,所有的一切都像是符號,什麼是正確的,什麼是錯誤的,什麼有價值,什麼沒有價值被一一標注整齊。簡單、確、統一、深固。
他此時非常混,在這半個月的時間里他時常覺得他要瘋了。無論是做韓令秋還是做天知曉的弟子,對他來說都像是背叛,他找不到自己,他不知道自己屬于哪里。
而這一切的始作俑者——段胥,好整以暇地站在他的面前。他看不懂這個人,過去是這樣,現在也是這樣。
遙遠的段胥在里微微一笑,他捧著黑布將眼睛遮好,然后對他說道:“韓將軍,要專心啊。”
韓令秋一邊將黑布蒙上眼睛,一邊想段胥要用天知曉的暝試和他比試,一邊又一直喊他韓將軍,這太矛盾了。或許在這里再一次輸給段胥,被段胥殺死是他最好的結局。
蒙上眼睛之后黑暗的世界里,其他的所有都敏銳了起來。韓令秋聽見沉英喊道開始,前方便傳來輕微而迅速的腳步聲,在他遲疑的瞬間劍風便至,他立刻閃躲避,在那一瞬間他意識到段胥是認真的。
他被帶進了段胥的節奏里,段胥的速度太快導致他只能步步退避防守,這麼多年里已經很有人能把他到這個地步。在刀劍撞聲中,深埋在骨髓里的記憶漸漸復蘇,他仿佛回到了和段胥搏殺的那些日子里,那些不斷迫自己突破極限,日沉溺于廝殺的記憶在黑暗的世界里鮮活起來。
Advertisement
那七年里,好像每一天他都在殺人。
他覺得暢快,人在他眼里不是人,而像是某種牲畜。他刀劍刺皮的聲音,他哀求與哭,他鮮橫飛,支離破碎。他以此為榮,以此為樂。
他存在于這世上的意義就在于此。
對于年的他來說,殺戮是這個世上最好之事。
但是這些鮮活的記憶讓韓令秋覺得恐懼。
不僅是恐懼,他還覺得惡心,他恨不得砍掉自己的手腳,砍掉那沾滿鮮的骯臟的手腳。他想跑回過去把那個因殺戮而喜不自的人摁在地上,他想封住那個人的,想要敲碎那個人的腦袋。
他想要求救。
誰來救救這個人,誰來救救他。
在他殺第一個人之前,如果有誰能阻止他就好了,就算是真的砍斷他的手也好,那樣他都會激涕零。
他絕地想要抓住誰去拯救那個惡鬼一般的自己,然而為時晚矣。
不僅如此腦海之中還有聲音在嘲笑他,對他說世界本當如此,那時候你不是很開心麼?你現在在絕些什麼?你只要選擇回到過去那條路上,那你就可以順利章地走下去。
你是蒼神榮耀的戰士,你所殺之人,只是必要的犧牲。放下你扼著自己嚨的手,不要掙扎了,回到過去罷。
“你怎麼不殺我呢?”
突如其來的聲音刺韓令秋一片黑暗的世界里,他愣了愣,意識到剛剛在他極度絕而瘋狂的況下,他幾乎全憑本能不要命地在攻擊段胥。
然后他好像贏了,他怎麼會贏的?
韓令秋把自己眼上的黑布扯下來,段胥坐在地上捂著自己的腹部,鮮從指間流出來,而韓令秋的劍正指著段胥的咽。段胥吐了一口,著自己的好整以暇道:“你不僅沒有荒廢,還進步不小啊。令秋,你怎麼不殺我呢?”
在黑暗中韓令秋失去了時間的概念,明明只覺得過去須臾,此刻卻已經夕西下,天地一片耀眼的通紅。他們邊的湖泊映著赤紅的晚霞與落日,仿佛是一潭沸騰的巖漿。
段胥抬頭坦然地著韓令秋,韓令秋從那眼神里看到一點悲憫。
他驀然想起來九年之前夕西下的擂臺上,他在與段胥開始瞑試之前,段胥看著他的眼神就是這樣。
他依稀記得,在之后模糊的混沌里,有人一直背著他,搖搖晃晃地走了很長的路。那個人對他說——去南方罷,去大梁,不要回來了。
韓令秋似乎再也不能忍,他低吼一聲,扔掉了劍拎起段胥的襟,他滿眼紅咬牙切齒地質問他:“你為什麼……你為什麼要救我?你別告訴我是什麼勞什子的惻之心,我們連三歲的孩子都殺過!你和我之間半點也沒有,你為什麼不殺我?”
段胥不閃不避地看著他,然后笑了起來,一笑便有從他的角流出,滴滴答答地落在韓令秋提著他襟的手上。
“唯一活下來的那個人會為十七,我不想做十七,所以不能讓你死。我不是為了救你,我是為了救自己。”
韓令秋怔住了。
“當然,就像你說的,我們三歲的孩子都殺過。我最后救了你能改變什麼?什麼都改變不了,這只是一個稚的念頭,安自己的理由。但是令秋,我是靠著這麼一個個稚的念頭支撐下來的。”
“你說我善于背叛,在我看來我從沒有背叛過。你現在所掙扎和思索的,我早就已經掙扎過了,從那之后我就只忠于我自己。但是你和我不一樣,我因為一己之私,罔顧你的意愿,擅自替你做了這樣的選擇。”
段胥握著韓令秋提著他襟的手,坦然地輕輕一笑:“令秋,我為我的自以為是,還有你臉上的疤向你道歉,對不起。”
韓令秋漸漸松了力氣,他低眸沉默了片刻,像是覺得荒唐一般扯了扯角,道:“你救了我,還要向我道歉。我總不至于這麼不識好歹。”
他抬起眼睛看向段胥,眼里映著赤紅的晚霞,瘋狂塵埃落定更沉重的傷痕,他說道:“段帥。”
猜你喜歡
-
完結521 章

一品女仵作
女法醫池時一朝穿越,成了仵作世家的九娘子。池時很滿意,管你哪一世,姑娘我隻想搞事業。 小王爺周羨我財貌雙全,你怎地不看我? 女仵作池時我隻聽亡者之苦,還冤者清白。想要眼神,公子何不先死上一死?
96.1萬字8.18 24943 -
完結132 章

國子監小食堂
孟桑胎穿,隨爹娘隱居在山林間,生活恣意快活。一朝來到長安尋找外祖父,奈何人沒找到,得先解決生計問題。陰差陽錯去到國子監,成了一位“平平無奇”小廚娘。國子監,可謂是天下學子向往的最高學府,什麼都好,就是膳食太難吃。菜淡、肉老、飯硬、湯苦,直吃…
66.7萬字8 17393 -
完結312 章

和離后,戰神王爺每天想破戒
穿越後,鳳卿九成了齊王府棄妃,原主上吊而死,渣男竟然要娶側妃,鳳卿九大鬧婚宴,踩着渣男賤女的臉提出和離。 渣男:想和離?誰會要你一個和離過的女子! 顧暮舟:九兒,別怕,本王這輩子認定你了! 鳳卿九:可我嫁過人! 顧暮舟:本王不在乎!這一生,本王只要你一個! 攜手顧暮舟,鳳卿九翻雲覆雨,憑藉自己高超的醫術,在京都名氣響亮,豔壓衆人。 渣男後悔,向她求愛。 渣男:以前都是我不對,過去的就讓他過去吧!我們重新開始好不好? 鳳卿九:不好意思,你長得太醜,我看不上! 渣男:我到底哪裏比不上他? 她冷冷地甩出一句話:家裏沒有鏡子,你總有尿吧!
55萬字8.18 124421 -
完結17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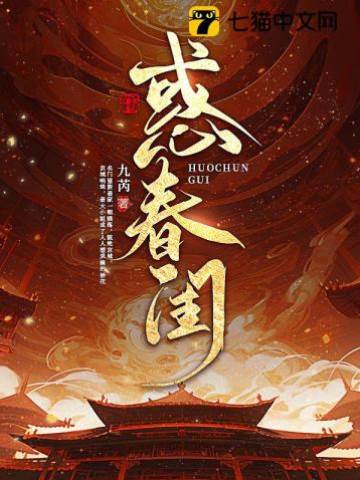
惑春閨
名門望族薑家一朝隕落,貌絕京城,京城明珠,薑大小姐成了人人想采摘的嬌花。麵對四麵楚歌,豺狼虎豹,薑梨滿果斷爬上了昔日未婚夫的馬車。退親的時候沒有想過,他會成為主宰的上位者,她卻淪為了掌中雀。以為他冷心無情是天生,直到看到他可以無條件對別人溫柔寵溺,薑梨滿才明白,他有溫情,隻是不再給她。既然再回去,那何必強求?薑梨滿心灰意冷打算離開,樓棄卻慌了……
31.5萬字8.18 857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