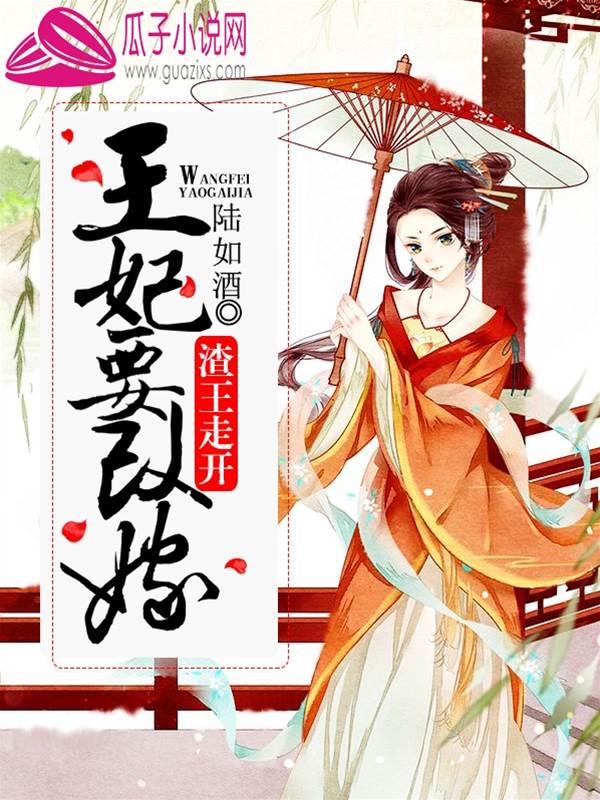《白日提燈》 第27章 契約
其實賀思慕只是試著喊一聲段胥,但他真的被喚醒了,僵立的子如急速融化的冰川般垮下去。他仿佛終于開始意識到疼一樣,力地坐倒在地上,急速地息著。
火時明時暗的映襯之下,這片荒原仿佛傳說中的地獄。段胥低著頭讓人看不清他的表,只能聽見他四平八穩而倦怠的聲音:“還有好長的路要走啊,可是我已經……很累了。”
他終于說他累了。
賀思慕想,還以為他是一個熱衷于把自己折騰得死去活來的家伙呢。原來他也是會累的。
在這番仿佛心灰意冷的發言之后,段胥卻突然抬起了眼睛,被染的眼睛凝聚著一疲憊的芒,竟然還是亮的。
他突然說道:“你想和我做易,想要我的五,又說會按時還給我。可那是因為你并沒有會過有五的,待你知道五、五味、六調、冷暖之后,你還能忍得而復失嗎?會不會終有一日,你拿走我所有,只最低限度地維持我的命,讓我變個活死人?”
難為他在此刻還能想起來這個易。
賀思慕沉默了片刻,淡淡道:“或許罷,算了,這易不做也罷。我看你再不趕回府城找大夫,就要死在這里了。”
段胥和對視了片刻,突然淺淺地笑了一下,那笑容安靜得沒有一點兒瘋狂的影子。他向賀思慕出手去,以一種玩笑的語氣說道:“你拉我一把罷,你拉我起來,我就答應你。”
賀思慕挑挑眉,心想這小將軍又在發什麼瘋,說:“十七……”
“我段胥。”
不明白他執著于這個假名字的意義何在,只道:“段胥,你還清醒嗎?”
“清醒得很,這多有趣啊。”
Advertisement
段胥的手懸在半空,他笑著緩慢道:“我賭那個’終有一日’到來之際,你會舍不得。”
一朵煙花在兩人之間的夜空中綻放,轟然作響。段胥沾滿的手被照亮,鮮紅熾烈地如同燃灼的火焰,指尖有一不易察覺的抖。
不知是興,還是恐懼。
賀思慕看了他半晌,看著這個凡人那雙向來清澈卻不見底的眼睛。
這個從來不計后果的,膽大包天的賭徒。
淡淡笑起來:“好。”
出手,的手蒼白,深紫的筋絡細細地在灰白的皮下蜿蜒著。這樣一雙冰冷而死寂的手握上段胥溫熱的帶的手,沾了他的,將他的手寸寸握。
結咒明珠飛出來,懸在兩人握的手上方,從兩人上各吸取了一滴融在一,匯進符咒紋路的凹槽里,即刻生效。
從此之后,這便是和命理相連之人。
賀思慕抬起手將段胥從地上拉起來,他還真的一點力氣也不使,懶懶地全由拽風箏似的拽著他,然后借著前沖的力量踉蹌地倚在了上。
他的個子比高,卻彎著腰把頭埋在的頸窩里,粘稠的鮮沾滿了的襟,額頭著脖子上的冰冷皮。
他把全的力量放在上,像是把自己的命系在的上。
“你這是做什麼?”賀思慕也不推開他,只是淡淡地問道。
“我是不是不正常。”段胥低聲說道。
賀思慕知道他在說什麼,便道:“殺紅了眼,也能算是不正常?”
殺人會讓段胥興。
直到剛剛賀思慕才意識到,曾在戰場中看到過段胥仿佛抑著什麼的眼神,他抑的正是這種興。
他似乎有過長年累月里大量殺人的經歷,以至于殺人對他變了興的因,使他陷從到神的狀態,難以自持。
Advertisement
或許從心底里他是殺戮的。
這種殺戮曾經取悅過他。
他在天知曉的漫長時間,他所經歷的一切已經融了他骨之中。
段胥沉默了一會兒,對說道:“剛剛十五師兄臨死前,對我說……你也是怪,你逃不掉。”
賀思慕沒有回答,寒風凜冽里,段胥的微微抖著,他慢慢說道:“有時候我不知道,我是偽裝瘋子的常人,還是偽裝常人的瘋子。”
賀思慕輕輕笑了一聲,有些不屑的意味。終于出手去放在他的后背上,不輕不重地拍了拍。
“你倚著全天下最不正常的家伙,說的是什麼鬼話呢?”
段胥安靜了片刻,突然輕輕地笑出聲來,他不知死活地出手去摟住賀思慕的后背,爽朗而安然地說:“說得是啊。”
賀思慕拍拍他的后背,好整以暇:“蹬鼻子上臉,放開我。”
“你不是想知道,我是誰麼?”
段胥并沒有聽話地放開,他整個人都松弛下來,仿佛打開了塵封的門扉一樣,他在的耳邊平靜地說道:“我做段胥,外祖父是有名的文豪,出生時他正在看春生班的戲,便就著戲文里的封狼居胥給我起了名。我的外祖母是前朝長公主,我家是三代翰林,南都段氏,我在南都長到七歲。”
又來了。
賀思慕皺著眉頭,正想打斷他的胡言,卻聽段胥笑著說道:“然后在我七歲這年,我被綁架了。”
賀思慕拍他后背作便停住了。
段胥繼續道:“胡契人綁架了我,以此威脅我父親與他們易報。當時黨爭正是最你死我活的時候,父親不僅沒有答應胡契人,甚至不能讓別人知道他有這樣一個把柄落在丹支手里。所以他對胡契人說,他們綁錯人了,他們綁走的本就不是段家三公子段胥。段家三公子被送回了岱州老家陪伴祖母。”
Advertisement
“那個被送回岱州的三公子,才是假的段胥。”
“胡契人被騙了過去,他們以為綁錯了人。我便趁機逃走,在丹支流落街頭……然后被外出挑選弟子的天知曉首領——我的師父挑中,進了天知曉。他們并不知道我的來歷,十四歲出師之后,我刺瞎我的師父逃回了大梁,認祖歸宗,得字舜息。父親安排了那一場從岱州回南都途中的‘被劫’,好讓假段胥消失,讓我回來。”
“這才是我,我就是段胥段舜息,我從來就沒有騙過你。你看這一次我又……逢兇化吉了。”
段胥說得很平靜,說道這里甚至俏皮地笑起來,仿佛得意的孩子。
賀思慕沉默著,無數魂燈從丹支的營帳中升起,如流行逆行般匯天際,朔州府城上空的煙火此起彼伏的絢麗著。一邊喜一邊悲,好一個荒唐又盛大的人間場景。
順著段胥的指尖滴落,他終于松開了抱著賀思慕后背的手,但這次賀思慕卻抱住了他。
——他正在往地上落,不抱住便要倒在地上了。
剛剛抱住賀思慕,已經用盡了段胥最后的一點力氣。
賀思慕抱著這個全無力倒在上的家伙,長嘆一聲,說道:“不僅是小狐貍,還是個小祖宗。”
最后賀思慕坐在的鬼王燈桿上,段胥坐在的側靠著的肩膀,由鬼王燈載著往朔州府城而去。段胥閉著眼睛,似乎睡著了又似乎還有一點神志,他含糊地問道:“鬼王殿下……你又什麼名字呢?”
賀思慕嘖嘖了兩聲,有一下沒一下地著燈桿下的鬼王燈。
通常不會告訴凡人的名字,便是惡鬼里,也只有左右丞敢的名字。
不過這個畢竟是要給五的結咒人。
Advertisement
“賀思慕,賀思慕的賀,思慕的思慕。”
這一番解讀讓段胥低低地笑了起來。
長夜將盡,天破曉,溫和如霧靄的晨融化了無邊無際的黑夜。
在金的中,段胥微啟干開裂的,慢慢地說道:“賀思慕,新年快樂,歲歲平安。”
賀思慕怔了怔,然后淡笑著回應道:“段胥,段小狐貍,你逢兇化吉,長命百歲。”
的目落在段胥腰間的破妄劍上,那劍鞘也染了,也不知是十五的還是段胥的。
十五是被破妄劍所殺,總歸能有個無怨氣的來生。
此前一直在想,破妄劍究竟為何會認段胥做主人,在這一刻終于想到了答案。段胥既非修士亦無靈力,縱然他是命格強悍,是天縱奇才,有常人難以企及的心,這也并非破妄劍選他的原因。
破妄劍選擇他,是因為想要救他。
這柄主仁慈的劍,殺人也渡人,它從柏清的手上來到這個年的手中,因為想要渡他所以認他為主。
渡他滿手鮮,滿風霜。
韓令秋和孟晚將段胥的計策告訴了吳盛六,在這一年的除夕夜里,在丹支軍營大火燒起來之時出兵攻擊。丹支軍隊群龍無首一片混,節節敗退,被踏白軍趕出百里之外,潰敗撤出朔州。
踏白府城之圍由此而解。
戰斗一直持續到早上,當吳盛六一行人率軍歸來時,便看見城墻上站著一個人。
那個年胡契人打扮,渾是傷被浸,他在晨下沖他們笑著招招手,然后從腰間的布袋子拿出一顆頭顱,掛在城門之上。
那是阿沃爾齊的頭顱。
他們的主將,深軍營放火燒營,刺殺主帥,讓他的士兵不至于和敵人戰到魚死網破,讓他的士兵大勝而歸,讓他后滿城的百姓渾然不覺地度過了一個熱鬧的春節。
吳盛六突然從馬上跳了下來,跪在地上。
他并沒有下達什麼命令,但是隨著他的作所有的校尉、千戶、百戶、士兵都下馬,次第單膝跪地,在晨中無數鐵甲泛著冷冽的銀,如同波濤涌過的海面。
段胥的眸閃了閃。
“踏白軍,恭迎主將。”吳盛六高聲喊道。
后那些士兵便隨著他齊聲喊起來,聲音排山倒海而來,涌向城頭的段胥。段胥扶住城墻,才勉強保持著自己能直地站著,他想剛剛再多吃點止痛的藥便好了。
然后他輕輕地笑起來。
賀思慕問過他為何要只犯險,他說因為這只踏白軍還并不是他的踏白。
到了這一刻,踏白軍,終于是他的踏白了。
猜你喜歡
-
連載341 章

新婚夜,王爺有讀心術后演技爆棚
【雙潔,甜寵,白切黑,歡喜冤家,1v1】云染堂堂閣主,醫毒蠱武,樣樣精通,日子快活似神仙,奈何一朝被雷劈,魂穿成尚書府飽受欺凌的大小姐,日子過的狗都不如……繼妹悔婚,直接命人將她打暈扔上花轎,嫁給那個傳聞中集眼疾腿疾隱疾于一身的男人****…
52.2萬字8 6910 -
完結1037 章
嬌嬌王妃駕到,撩撥王爺臉紅心跳
【甜寵日常】【先婚後愛】+【救贖】 水洛藍,開局被迫嫁給廢柴王爺! 王爺生活不能自理? 不怕,洛藍為他端屎端尿。 王爺癱瘓在床? 不怕,洛藍帶著手術室穿越,可以為他醫治。 在廢柴王爺臉恢復容貌的那一刻,洛藍被他那張舉世無雙,俊朗冷俏的臉徹底吸引,從此後她開始過上了整日親親/摸摸/抱抱,沒羞沒臊的寵夫生活。 畫面一轉 男人站起來那一刻,直接將她按倒在床,唇齒相遇的瞬間,附在她耳邊輕聲細語:小丫頭,你撩撥本王半年了,該換本王寵你了。 看著他那張完美無瑕,讓她百看不厭的臉,洛藍微閉雙眼,靜等著那動人心魄時刻的到來……
191萬字8.57 328874 -
完結1033 章

天命醫凰
【甜寵+虐渣+爽文+宅斗】 上一世,她用盡心力助渣男上位,卻落得個被剖腹取子、慘死水牢的下場。 重來一回,她早早遠離渣男,保護侯府、扶持幼弟,拼盡一身本事,只為讓愛她的親人們不再受到任何傷害!不過這位十三皇叔怎麼回事,為何纏著她就不放了?!
96.5萬字8 34140 -
連載52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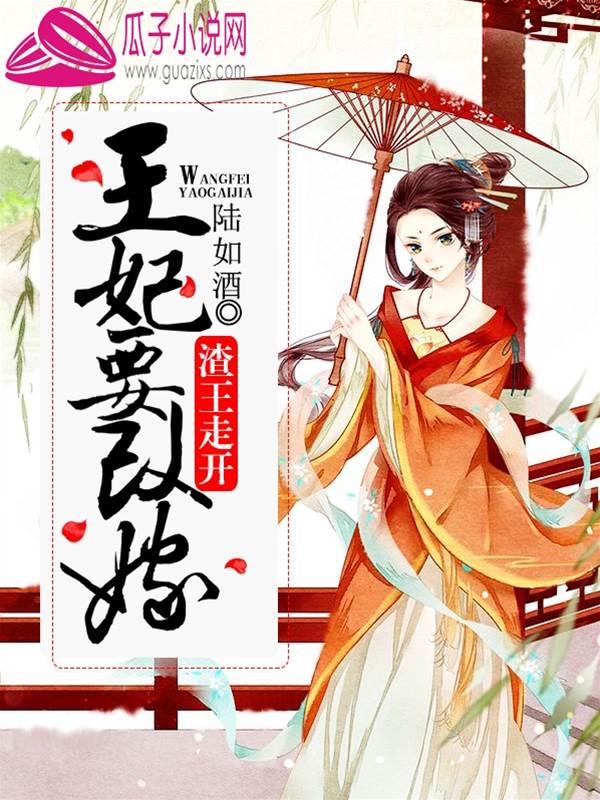
渣王走開:王妃要改嫁蘇妙妗季承翊
蘇妙,世界著名女總裁,好不容易擠出時間度個假,卻遭遇遊輪失事,一朝清醒成為了睿王府不受寵的傻王妃,頭破血流昏倒在地都沒有人管。世人皆知,相府嫡長女蘇妙妗,懦弱狹隘,除了一張臉,簡直是個毫無實處的廢物!蘇妙妗笑了:老娘天下最美!我有顏值我人性!“王妃,王爺今晚又宿在側妃那裏了!”“哦。”某人頭也不抬,清點著自己的小金庫。“王妃,您的庶妹聲稱懷了王爺的骨肉!”“知道了。”某人吹了吹新做的指甲,麵不改色。“王妃,王爺今晚宣您,已經往這邊過來啦!”“什麼!”某人大驚失色:“快,為我梳妝打扮,畫的越醜越好……”某王爺:……
99.7萬字8 1349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