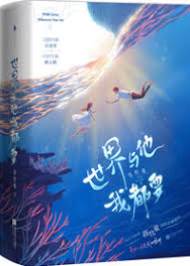《我是天降女主文里的小青梅》 第73章
茶茶現在只能忍辱負重,聽見什麼令人生氣的話都得當做沒聽見。
有時候想起來也會覺得夢幻,怎麼曾經那麼喜歡過的年會變得像現在這樣蠻不講理,森可怕呢。
幾分鐘后,沈執牽著到了他們幾年前住過的民宿,不曾出示份證辦理住,直接就帶去二樓的房間里,關好了門。
房門上鎖咔的一聲,茶茶心中一驚,有些不準他想做什麼。
如臨大敵,滿臉的不自在,摳著手指頭強不安,心里頭在撲通撲通在打鼓,他上前一步,就往后退一步,好像怕的要命,非要裝的很淡定。
沈執看見怕自己,也不是不難,他臉上表卻沒什麼變化,冷冷淡淡,眉眼神如常,他給房門上了鎖,往前兩步走。
茶茶跌坐在沙發上,手指用力著下的棉布,小臉蒼茫無措,磕地問:“你干什麼!”
沈執輕笑了聲,“不是想上廁所?”
茶茶愣了愣,還沒給出反應,沈執又說:“快去吧,不然還要我陪你一起去嗎?”
茶茶火速站起來,沒好氣道:“不用你。”
跑著進了洗手間,用力關門,砰的一聲發出巨響,生怕房間里另外一個人聽不見。
茶茶坐在馬桶上,腦子轉來轉去,十幾個逃跑的辦法在腦子里過了一遍,最后都一一作罷。
過了半個小時,茶茶還是沒打算出去。
沈執敲了敲門,耐告罄,“好了沒?”
茶茶沒好氣道:“沒有。”
沈執給氣笑了,“半個小時了,想到辦法了嗎?”
茶茶知道沈執聰明,心計過人,但從來都不知道他還能讀心,這麼會猜當年怎麼就沒看出來姜妙是個什麼人呢?
茶茶厚著臉皮回:“便。”
Advertisement
門把手上下錯位,擰門聲把里面的人嚇了一跳,幸虧鎖了門,不然沈執現在已經闖進來了。
又氣又火,“你能不能要點臉?”
沈執送開門把手,語氣平淡,“十分鐘,再給你十分鐘,不出來我就開門了。”
“滾。”
沈執挑了挑眉,他知道茶茶氣好,除非氣到極致,否則說滾字。
不過他也不介意,罵就罵吧。
他甚至能想到茶茶他滾的時候臉上的表一定特別生,臉蛋估計氣的紅通通。
又過了十分鐘,茶茶掐著點從廁所里出來,沈執上下掃了一眼,問了句:“舒服了?”
茶茶憋著氣,的懟了回去,“看不見你總歸是舒服的。”
沈執氣歸氣,但也不會讓看出來,他固執牽著的手,“既然舒服了,我就再帶你出去逛逛,總不能憋壞你。”
茶茶想著總要尋個機會報警。
沈執既然敢帶出來,就不會怕那些小作,他了的臉,“別折騰了,茶茶,我現在就能幫你把警察過來,你看看我會不會被抓進去。”
茶茶還不知道他竟然有這種本事,興師眾,就為了讓知道,現在跑不了。
茶茶很冷靜看著他問:“這件事,你籌劃了多久?”
謀算的如此縝,不像是臨時起意。
方方面面都做的滴水不。
不讓人抓到把柄。
沈執喜歡和多說說話,哪怕從里說出來的不是他聽的,他也不介意。
他太想聽聽的聲音。
也太久沒有和說過那麼多的話,雖然這機會是他強求來的,但是他一點都不在乎。
抓到自己手里的才是真的,放手祝好就真的什麼都沒有。
沈執也不介意告訴,“很久。”
Advertisement
從和于故在一起那天,他就想這麼做了,一直克制著,冷靜著,強迫自己當個正常人。
他們不該拿那張訂婚請柬挑釁他,不該用百年好合四個字來刺激他。
沈執邊牽著的手,一邊用低沉清冷的聲音和說:“車是你自愿上的,中途我就換了車,用了另一張份證,避開了所有有攝像頭的地方,借用了朋友的私人飛機,我知道你父親你哥哥都不是等閑之輩,但是國這麼大,他們想找到你,談何容易?沒個一年半載,別想有你的消息,到時候也許我們倆的孩子都快出生了。”
他心甚好,連帶著話也變得多了起來,著的手指頭,慢悠悠地說:“何況我故意用你的份證在網上買了許多張,飛往不同地方的機票,每一張都是迷霧計,茶茶,所以我說你死了他們找到你這份心,不期待也就不會失,你我認識多年,你該知道我是多縝的一個人,不會留任何的蛛馬跡給他們。”
茶茶確實了解他。
沈執做任何事都很細心。
茶茶說:“你去死。”
沈執寧肯聽氣話也不要不理他,“死了也要帶上你。”
茶茶搞不懂神經病的想法,更搞不懂好端端一個人為何要這樣。
做的那個夢,對一點幫助都沒有。
早知道……
沒有早知道。
茶茶捫心自問自己后悔嗎?重來一次,大概還是會喜歡上沈執。
于而言,沈執就是那個驚艷了青春的年。
那年正好,風過林捎,心也是遲早的事。
茶茶不愿意毀掉僅剩的那些好,然而沈執偏偏要毀給看。
民宿客棧似乎被沈執訂下來了,客棧里除了他們就沒有別的客人,老板娘也換了人,不再是他們上次來過時的那個。
Advertisement
客棧的院子種滿鮮花,團團簇簇,爭奇斗艷。
窗外的天空湛藍如洗,刺眼。
茶茶穿著白小子,頭發被綁兩小麻花,清純的不得了,說:“沈執,連老板娘都換人了。”
很多事都變了。
他想回到過去,但人這輩子,只能往前走。
沈執握的手,“那又怎麼樣呢?”
茶茶用平靜的口吻說:“我就算穿著高中時的校服,也已經不是高中生了,不再那麼執拗的喜歡你,我二十二了,不是十六,我們已經分手三年了。”
用平鋪直敘的語氣,說出這段話。
沈執低垂腦袋,抿了抿,說出來的還是那句話,“那又怎麼樣呢?”
進死胡同的人,是無論如何都說不通的。
就像當年的,飛蛾撲火奔赴他邊,被他上冰刀做的火灼燒的無完,遍鱗傷的疼痛都不能讓回頭。
茶茶盡可能讓自己的語氣聽起來不那麼像怨恨,說:“就算回到過去,回到我們十五六歲的時候,又能改變什麼呢?你那個時候喜歡的是姜妙。”
其實和他之間的問題,從來都不是姜妙。
歸結底,是沈執,沒那麼。
或者是,十七歲的沈執,答應了告白的那個年,同時喜歡上了兩個人。
一個是熱開朗的紅玫瑰。
一個是清純斂的白山茶。
他更紅玫瑰,卻也放不下白山茶。
沈執被堵住嚨,別的事,他都能為自己辯解,唯獨這一點,他無法再撒謊,再欺騙。
茶茶著花園里盛開的正艷的鮮花,說:“放我回去吧,求求你了。”
好想于故啊。
才短短兩天,思念疾。
想快點回到他邊,躲在他的懷抱里,無所顧忌的大哭一場。
Advertisement
茶茶就是很難過,不愿意沈執變現在這個面目全非的樣子。
沈執看著發紅的眼眶都沒有心,偏執倔強帶逛完了后山人跡罕至的景點,待到夕落下,才將困得不行的抱回他們曾經住過的客棧里。
顯然,這間客棧已經被他買下來了。
老板娘不在,也沒有別的店員。
外面被屬于他的人看管的如銅墻鐵壁。
茶茶回去就睡了一覺,做了個很漫長的夢。
夢里面有沈執,還有。
無憂無慮的年紀,每天需要苦惱的事屈指可數。
煙雨時節,總能看見穿著白襯衫把自己整理的一不茍的年。
他高冷、漂亮、聰明、理智,天生有種疏離,線折下的茶瞳孔朝看過來,眼睛深藏著一抹,他撐著雨傘,“上車。”
茶茶聽見那兩個字,鼻子發酸,很想哭,特別想哭。
最初喜歡上的那個人,就是這個樣子。
好看冷淡,但是對卻是愿意親近的,也是很好的,又溫。
一陣急促的雨聲驚擾了這個畫面,茶茶流著淚醒過來,發現自己的頭很疼,沉沉的,特別不舒服。
還是想睡覺,于是,抱著被子就又睡了。
茶茶睡著后又做了夢,夢里面還是沈執。
四五歲的沈執、十六七歲的沈執、二十歲的沈執……
頭疼,眼睛也疼,酸的淚水往外溢。
為什麼要讓再在夢里經歷一遍呢?為什麼要讓再回憶一遍當初?
心再到心死的過程真的好痛好痛啊。
不要再做夢了。
不要再想起那些事。
茶茶掙扎著醒來,的手牢牢抓著床邊的男人,滿頭的冷汗,心里被刀子割過一般,水珠模糊了眼前的視線。
沈執的額頭,“你發燒了。”
茶茶這會兒意識不太清醒,一個勁的重復,“我好想于故啊。”
“我好想他。”
“讓他帶我走吧。”
完全沒看見,眼前的男人臉有多白。
猜你喜歡
-
完結147 章

程太太今天又作妖了
海城內人人都不看好林、程兩大世家的聯姻。程時宴為人陰鬱涼薄,林亦笙又是出了名的矯情任性,被媒體授予海城第一作精的稱號。有人私下打賭,程時宴受不了林亦笙的脾氣,一年之內絕對離婚,其餘眾人紛紛看戲。一年兩年過去。兩人聯姻依舊穩固。晚宴上,眾人翹首以盼夫妻不和,林亦笙單獨赴宴的場景。姍姍來遲的林亦笙挽著程時宴的臂膀,趴在男人胸膛低聲嬌嗔:“老公~給點麵子配合一下。”程時宴懶散斂眸,將女人壓進懷裏,垂首在她耳畔邪氣低喃:“昨天晚上你可沒配合,嗯?”涼薄繾綣的聲線在耳邊縈繞,林亦笙明豔的臉一紅。心中暗罵不已,表麵乖巧道:“今天肯定配合。”
26.1萬字8 14098 -
完結294 章

夫君新喪,小叔奪我入羅帳
【1V1雙潔+望門寡嫂嫂+陰鷙瘋批男主+巧取豪奪+男主加持便霸氣起飛的女主】 江琯清是百年書香門第之女,因雙胞胎早產而體弱,不滿週歲就幾次差點夭折。與世交葉家大公子定親,才靠著他的福佑好好的長大。本以爲她會嫁給夜葉煦辰,相夫教子一世恩愛。卻不想葉煦辰戰死沙場,她才十二歲就變成望門寡,更是要爲英雄陪葬的。那夜,她不肯入棺與粉身碎骨的夫君合葬。她抱著小叔葉寒崢的腿,求他救下自己。三年後,她成年了。當初她主動招惹的小叔,就化身成一條毒蛇。白天教唆她反抗,夜裏引誘她犯錯。從此她中了他的毒,活成自己一直不敢想的樣子,也成了這個壓迫女人的時代的異類。男人都恨她,女人都崇拜她。而她想要的,也不過只他一人而已。
53.4萬字8.18 4401 -
完結340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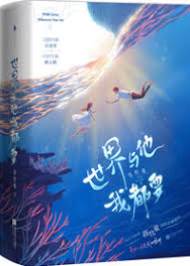
這世界與他,我都要
溫牧寒是葉颯小舅舅的朋友,讓她喊自己叔叔時,她死活不張嘴。 偶爾高興才軟軟地喊一聲哥哥。 聽到這個稱呼,溫牧寒眉梢輕挑透着一絲似笑非笑:“你是不是想幫你舅舅佔我便宜啊?” 葉颯繃着一張小臉就是不說話。 直到許多年後,她單手托腮坐在男人旁邊,眼神直勾勾地望着他說:“其實,是我想佔你便宜。” ——只叫哥哥,是因爲她對他見色起意了。 聚會裏面有人好奇溫牧寒和葉颯的關係,他坐在吧檯邊上,手指間轉着盛着酒的玻璃杯,透着一股兒冷淡慵懶 的勁兒:“能有什麼關係,她啊,小孩一個。” 誰知過了會兒外面泳池傳來落水聲。 溫牧寒跳進去撈人的時候,本來佯裝抽筋的小姑娘一下子攀住他。 小姑娘身體緊貼着他的胸膛,等兩人從水裏出來的時候,葉颯貼着他耳邊,輕輕吹氣:“哥哥,我還是小孩嗎?” 溫牧寒:“……” _ 許久之後,溫牧寒萬年不更新的朋友圈,突然放出一張打着點滴的照片。 溫牧寒:你們嫂子親自給我打的針。 衆人:?? 於是一向穩重的老男人親自在評論裏@葉颯,表示:介紹一下,這就是我媳婦。 這是一個一時拒絕一時爽,最後追妻火葬場的故事,連秀恩愛的方式都如此硬核的男人
52.7萬字8.18 8147 -
完結147 章

春日當思
長黎十八年,折皦(jiao)玉三歲。彼時北方被侵,衣冠南渡。 她在這場災難裏跟將軍爹走散,成了小啞巴,被人販子賣進了蜀王府。 在蜀王府長到六歲,又被選去伺候花圃。 十六歲的蜀王殿下愛花。彼時,他歪在廊下看書,她揹着紫藤蘿編織的小簍子在院子裏忙活着採花。 他偶然瞧見,賜了名:“叫阿蘿吧。” 自此養在身邊,悉心教導。 一直長到十六歲,她得了風寒去世,結束了平淡的一生。 ——唯一不平淡的應當是她臨死前,他突然說:“阿蘿,我歡喜於你,是男女之情,夫妻之意。” …… 再睜開眼,折皦玉回到了跟將軍爹離失之前。 屋子錦繡繁華,她成了主子,再不是那個種花的奴婢。 好像上輩子恍然一夢,都是虛影。 能做主子,誰願意做奴婢。 她忘卻蜀王,歡歡喜喜過自己的好日子。 只是偶爾會想,他那樣的人,怎麼會喜歡上她。 六歲時,她跟着阿孃進皇都,又見到了蜀王殿下。 彼時兄長淘氣,在家帶着她劃小舟採蓮蓬,船剛靠岸,她頭頂大大的蓮葉,一擡眸便見到了岸邊的他。 他低下頭,溫和問她,“你叫什麼名字?” 折皦玉怔怔道了一句,“阿蘿。” …… 齊觀南最近總是做夢。夢裏,他不是現在這般的溫潤如玉模樣,而是個殺人不眨眼的瘋子。 他唯一的溫柔,給了爲他養花的阿蘿。
22.1萬字8 290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