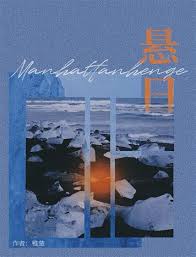《穿到明朝考科舉》 第33章
詩會之上, 生員儒爭展詩才之際, 這些作主人的、考的,還有眾所歸的遷安第一才子, 竟扔下詩文不管, 討論起了畫箋?
還是什麼人箋?
別的名字過過耳朵也就沒了, “人箋”這香艷的名號卻極是刺激士子們的心。湯寧三兩下寫完了詩,也扔下筆湊到首席, 想看看那人箋究竟是什麼樣的。
未看之前, 他心里先預勾畫出了一副人圖,準備給那箋挑病;看到之后, 他心中的人便是消散得了無痕跡, 唯有畫箋上濃墨重彩的佳人深深印他的心里。
世上怎麼有如此活生香, 婉妍的人!
他恨不能搶一張走,卻又顧忌著份和滿座才子的目,忍了又忍,只問了一句:“公子這畫上的是什麼人?”
崔燮也看著畫中人, 邊逸起一點溫的笑意:“本名阿婉, 是一名狐, 但天純真溫,因為看中夜宿古寺的書生方寧之才華,就贈金贈銀送他上京考試。待他中式而歸后,卻自覺為妖類,配不上進士,又費盡心思替他娶了一門佳婦。最后取了方寧名中的寧字綴在自己的名字后, 獨自歸棲山野,終懷念方寧。”
他說話時語帶憐惜,完全就像是在說一位真正存在于世的可妖的故事。湯寧也當作真事一般聽著,嘆道:“我亦名為寧,怎麼就沒有福氣遇到這樣一位佳人。”
他心緒浮,抬眼看著崔燮說:“崔世弟能否送我一張畫箋,讓我為婉寧作詩一首,以彰佳人之德?”
崔燮角的微笑慢慢綻開,從匣里出幾張畫箋,珍重地遞給他,答道:“世兄能與我一樣喜婉寧,崔燮心中喜不自勝,區區幾張畫箋又值得什麼。”
Advertisement
湯寧抱著畫箋回去,也舍不得在上面寫,先拿普通箋紙打了底稿。他旁邊的書生借機了一張過去,展開畫紙,頓時也被畫中人折服。
這一天的重宴已經沒幾個人還能有心思賞,能將詩題在崔燮的人箋上,也了比被傳唱更為榮耀之事。連那幾個請來的兒都可以不要秀才給們題詩,只求一張人箋。
崔燮帶了幾十張畫箋,重詩會上卻只有子六七人,冠者十余人,真要按人頭分配,一人一張足有富余,而且這些人還肯給他寫詩作詞打廣告。可他在這種況下還把持得住理智,記得搞營銷。
哪怕是給這群可能為代言人的,也要抻著他們,不能輕易給!
他歉然笑道:“這些畫箋是說好了要記下會上佳作的,回去給趙世兄看的。諸位前輩與同窗若是想要,等我回家后再教工匠們印來相送可行?將來我也會再畫另外三篇小說中佳人的箋紙與大家作補償,愿各位勿怪我今日鏗吝。”
不怪不怪……只是這樣的好箋,若題上一般的詩就太可惜了。
林先生挑了又挑,選了又選,才挑中了三篇值得題在畫箋上的詩,剩下的就讓他用普通稿紙抄了,珍惜地說:“你那些畫箋是稀世珍品,題上平庸的詩就是暴殄天了。”
前三的詩中最好的仍是郭鏞,其次是個作王溥的年生員,再次是個老學究趙養粹。湯寧那篇匆匆而就的詩作沒有選,但他得了足有三張畫箋,簡直羨煞旁人。
有幾位特別畫之人甚至按捺不住地效仿湯寧,愿為狐寫詩作文,以換得一張箋紙。此濫觴一開,其他人也開始放下架子以詩文換紙,崔燮滿面喜,一一滿足他們,還很憾地說:“只恨我不會說話,無法將那四位奇子的故事講得如原作萬一之彩,倘直接背書又太僵,反傷了原作音辭之。回頭我家書坊把書印出來,諸位前輩兄長就能親眼看到那些佳人的故事。”
Advertisement
他又是畫箋又是故事地勾了半天,會上的才子和們都涌起一買書的沖。就連林先生都不開始回憶看過的樣稿,回想那套書是否真的有那麼人。
難道是那天他看的時間太短?還是忙著修改了,沒走心細看?
=====================================
評詩結束后,前三名的佳作被抄在畫箋上還給作者,剩下的自有校書撥弦度曲,細細彈唱。生詩中沒甚好的可以寫在畫箋上的,卻也挑了頭名,讓詩唱出來佐酒。
眾人宴后還到山里登高遠、佩茱萸、吃重糕,飲花酒,盡了重的風俗,過了午時才散席。
秀才們晚上還有一席,儒們卻是要回家住的,要早一點下山。沈諍早早安排人套了車,崔源父子吃過午飯也回來等他了,此時正好一并接著他們回去。
臨別之時,還有不人殷殷叮囑他早些印出更多的畫箋,他們回去就使人去買。崔燮十分痛快地應承了,只跟他們提了一個要求:“這畫箋印得慢些,以后或有供不上的時候,各位不必到店里催促,就到我家說一聲,等工匠印出來,我便讓家仆給各位送去。”
這樣的箋,比畫出來還慢也是應該的。
眾人都沒有毫異議,湯寧還嘆道:“崔公子是深之人,深之人往往重義,才是可往之人,湯某往后難免要常去你家叨擾了。”
郭鏞也笑道:“雖然秋試在即,我恐怕也不能不于此用心一二了。”
有這兩位才子帶頭,其他書生也不在意他連縣試都沒試過,愿意把他當個能談論詩書的小友,而不僅僅是個書坊主人來往。
Advertisement
林先生這個得意弟子人接納,比自己結了好友還要高興,代他謝過眾人看重,臨分別時又忍不住教訓了幾句,讓他不要沉迷小說,也別浪費太多時間在畫畫制箋上,還是要以功課為重。
崔燮老老實實地教,低著頭答道:“先生放心,我都是做完了功課才敢做別的。”
“嗯,那就是課業還不夠。”林先生捻了捻胡須:“既然你還學有余力,放假回來就跟我學做承題、原題吧。”
……要是不說學完了才畫,是不是就不那麼急著加新課了?
不過這念頭只一晃而逝,他也并不是真的不想學習。這些日子他已經做了不大題,也背了幾十本縣、府、道試的小題,什麼截上、截下、有搭、無搭也都掌握了思路,該是學著往下寫的時候了。
承題、原題之下才是起講,起講之后還有題、八比、大結……若不快點往下學,剩下這五百余天里,又怎麼能夠寫出足以通過縣試的文章?
在讀書人中間的聲也要刷,自己的學問也要抓。兩手都要,才更容易通過這三關幾乎全由考本人喜好決定的生試。
他笑了笑,懇切地對林先生說:“是,多謝先生重。”
林先生心里熨帖得很,點了點頭說:“難得你懂事。”
幾位被罰了抄《大學》的師兄不可思議地看著他,坐上車之后還悄聲議論著:崔師弟居然這麼好學?他一個大家公子,年紀小小憑畫箋就能折服一縣文生的人,要這麼拼命讀書做什麼?二十再考生員也不晚哪!
而被他們當作志學典范的崔燮一回到家就把學習拋到腦后,詩稿扔給捧硯謄抄,自己轉就鉆進后院工作室里開會。
Advertisement
書坊的印刷匠人們也都期待著東家去詩會推銷的結果,連計掌柜都在這兒等著,進門便問他:“公子,那畫箋反響如何?”
崔燮到了這里終于不用再裝,笑道:“好,極好,非常好。今日在這里的都有數,每人三兩獎金,張大和趙石兩位大師傅多加二兩,月底就和工銀一道發。”
匠人們簡直喜不自勝。
雖然崔燮一開始就設了獎金,可最后能把畫箋印這樣,大半功勞在他自己畫的人圖上,另外小半功勞里也有他提點之功。那些只做備版、備料、染箋等工作的雜工們更是喜出外,口中千菩薩萬菩薩地念著,恨不能去廟里替他上香。
崔燮擺了擺手說:“別忙著謝,今天起你們就要加班加點地印箋了。我也趁著有工夫再畫幾張彩圖,大家準備制箋——當然那頭一張更要放在前頭印。”
布置完工匠的任務,他又特地了計掌柜過來,私下問道:“我知道你在外頭認得的書坊多,版工多,可知有哪個肯接私活的?”
計掌柜頓時額頭微汗,臉頰發熱,賭咒發誓地說:“小老兒再不敢做那事了,當初老兒匠人們出去接活也是一時糊涂。若早知道東家這麼快回鄉,我等一定守著清貧等待你回來啊!”
崔燮微微搖頭,安道:“我不是找你翻舊帳的。是我之前從詩會上弄來了許多才子詩,咱們出一本沈園詩集,夾上彩圖,趁熱先賣一陣,讓書生們別忘了咱們。那四本小說若是都刻不過來,咱們坊里就主攻彩圖,招短工過來刻文字版。”
計掌柜這才定下心,沉著說:“匠戶市那里倒有個方瘸子會雕刻,也不主家的版,他兒子也能當個小工。東家若看得上他們……”
崔燮擺了擺手:“這些我都不管,你看著弄就是了。你和計伙計、方伙計你們是管店鋪的,誰賣出一套我給他們提三分銀子,他們倆賣的也給你提一分,若能賣到外地,又有別的分。但若有人提前印了咱們的稿子,我肯定要去報,你們也要負連帶責任。”
計掌柜聽著分銀子,心就跟要從口跳出來似的。這樣的畫箋即便在遷安也肯定有人肯買,要是能運去京城和南方,賣出幾千幾萬套也不在話下!
他甚至為自己想象中的場景激得微微出汗,了額頭,揚眉地說:“東家放心,老兒必定會為你持好店鋪!”
崔燮深深看了他一眼:“我信你。這些日子讓黃嫂多做些食,你們忙歸忙,也別熬壞了子。”
安排好了這些工作,他也就能安心忙自己的了。崔燮回去便馬不停蹄地問捧硯要了另三篇文里最好的詩,在桌上先鋪上氈墊,上了一層膠礬,閉上眼翻開小黃片,找出與詩中人相應的角來畫。
四篇文稿的主角分別是神、仙、妖、鬼,妖參考了已滅絕生,其余三種則是在古代香港-民俗傳說/意識形態兩個文件夾里翻找出來的。
神頭戴九釵,穿大紅牡丹紋罩袍,拖八幅湘,腰間系描金尾,高貴端麗,令人不敢視。仙則是黃衫紫,頭梳凌云髻,腳下有云霧遮護,長長的披帛凌空飄拂,神清冷,不染塵俗。鬼則是一素白衫,頭上只斜簪一朵白曇花,細眉微蹙,材纖瘦,凄清中又帶些惹人憐惜的之。
一個妖,一個姐,一個高冷,一個萌妹,集全了后宮漫提純多年的萌點,足以網羅盡所有潛在顧客了!
趁著重節先生要留宿沈園,轉天早上也放假,他連畫了整整兩套七張彩圖。圖中基本都是主角單人,偶爾畫個男主的背影、角,方便讀者代。
畫完兩套圖,整個上午就差不多過去了。他看看天,便撂下筆,帶了幾張畫箋和自己抄下的詩稿去隔壁趙高鄰家哄孩子。趙應麟本來也不是真的怪他,得了詩稿和畫箋,更是沒別的心思了,喜不自勝地說:“我先留著他,回頭做了好詩文再用這寫,我現在的字跡和文章還有點配不上這箋……崔世兄,我能把這箋給我兄長一張嗎?”
崔燮笑著應道:“已經送你的東西,自然任你置。這畫箋也就是現在剛開始印,印的,將來多了再送你幾匣,不必那麼舍不得。”
猜你喜歡
-
完結139 章

穿書后成了萬人迷
喬墨沉穿進了一本萬人迷耽美文。 文中主角愛慕者眾多,他只是其中的癡漢炮灰攻,出場三章就領盒飯。 為保狗命,喬墨沉努力降低存在感,遠離主角。 出新歌,參與紀錄片拍攝,編古典舞,為文明復原古地球的文化,沉迷事業不可自拔。 等到他回過神來注意劇情的時候卻發現原文劇情已經崩得不能再崩了。 萬人迷主角和原情敵紛紛表示愛上了他,為他爭風吃醋。 喬墨沉:???
36.5萬字8.18 6977 -
完結10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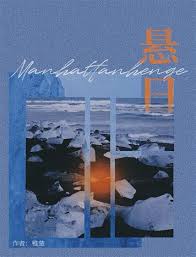
懸日
寧一宵以為這輩子不會再見到蘇洄。直到酒店弄錯房卡,開門進去,撞見戴著眼罩的他獨自躺在床上,喊著另一個人的名字,“這麼快就回來了……”衝動扯下了蘇洄的眼罩,可一對視就後悔。 一別六年,重逢應該再體面一點。 · -“至少在第42街的天橋,一無所有的我們曾擁有懸日,哪怕只有15分20秒。”
47.2萬字8.18 161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