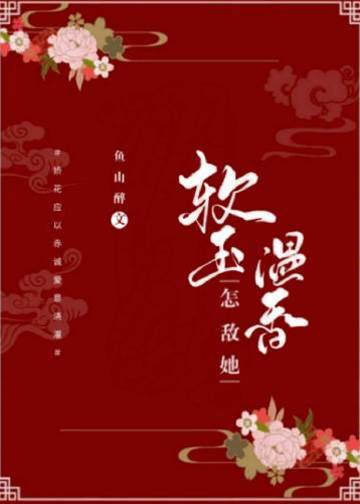《穿到大佬黑化前》 第16章
夜幕很快降臨,周植是個自來的,一小時不到就悉了新宿舍的生活,此時正在和傅云深在科打諢,然而傅云深并沒有搭理他。
時暮正坐在床上看著手機,付完學費,雜七雜八東西買完后,銀行卡余額已所剩無幾,估計還能支撐三個月不到,時暮眉頭皺起,既然和家人斷絕了關系,就算死也不能再回去,除了上學和傅云深拉近關系,也要想辦法賺錢糊口。
原來的直播肯定是不能做了,一來電腦和各種直播工太過費錢,二來時間和力不太允許,想想也只能閑來去給人做家教,但是……錢來的太慢了。
長呼口氣,心里有些煩躁。
“深哥,暮哥,你們洗澡嗎?”
……洗澡。
時暮一僵,這才意識到自己有兩天沒有洗澡了,然而一想到房間里可能有四個男鬼,就不太淡定了。
“你先去洗吧。”傅云深埋頭做著筆記,表專注。
“那我先去啦~”
周植傻白甜一笑,當著兩人的面了上襯衫和子,只留下一條四角底,時暮角一,匆忙移開了視線。
忍不住說:“周植,你能不能去浴室。”
“啊?”周植一愣,低頭看了眼,又看了看床上稱得上是小的時暮,他眉頭一擰,目逐漸同,“暮哥,你放心,等過幾年,你也會和我一樣有的。”
“……”
不,就算是過上一百萬年都不會有這玩意的。
看著時暮,周植不嘆了口氣,心里愈發敬佩起時暮來,想弱的,竟然還能驅鬼,想來小時候是了不苦,等他以后有了好東西,肯定要和這兩人分。
周植覺得自己的形象也高大上起來,里哼著歌,轉進了浴室。
Advertisement
過了會兒后,他半開起房門:“暮哥,你能幫我取一條嗎?我剛忘記拿了。”
……?
時暮手一抖,手機差點砸臉。
周植似乎也意識到了不妥,很快又說:“算了算了,我出來穿。”
咯吱。
浴室門開了。
周植赤,毫不掩飾的出現在了兩人眼前。
時暮倒吸口涼氣,倏地下瞪大了眼。
除了在GV里看過回歸本原的男人外,這是時暮第一次……在現實里看到禿禿的男孩子。
時暮表示……有點刺激。
坐在書桌前的傅云深斜睨一眼,扯起掛在椅背上的T恤就丟了過去,“遮住點,難看。”
周植條件反的接住T恤捂住部,等他看清那T恤是自己最喜歡的牌子貨后,表頓時糾結:“這是我明天要穿的……”
傅云深余瞥過:“你快點穿上服,難看。”
一連兩個難看讓周植立馬不樂意了,“男人那玩意能有多好看啊,大就行了,有本事你把你服了,我們比比誰好看?”
話鋒一轉:“暮哥,你說呢?”
“……”時暮不由夾了,并且用手了下自己最小碼的假丁丁。
“你快穿服。”傅云深語氣已經變得不耐,周植努努,不敢回,踱步走了過來。
看著那愈來愈近的男,時暮倒吸口涼氣,急忙往旁邊退了退。
周植背過子,正對時暮一個油亮發的屁,他踮起腳尖,從床上撈下了,然后丟掉T恤,彎腰往上套。
時暮定定看著,表格外震驚。
注意到這個畫面的傅云深一聲哼笑,邊的弧度滿是促狹:“周植,你可要小心點時暮。”
“啊?”周植抬頭,一臉天真。
傅云深眸閃爍,“世風日下的。”
Advertisement
這麼深奧的意思,周植自然聽不太懂。
可是時暮懂了。
世風日下是《睡了上鋪的兄弟》那本漫畫書的容,小對一條新聞慨世風日下,世道不公,沒想小攻直接說“我是世風……”,然后就是一段不可描述。
不過……
傅云深竟然背著看了這本書!
沒想到他是這種大佬!
時暮捂臉:“傅云深你別說話。”
傅云深挑眉,適當轉移了話題:“你先去洗澡吧,我還要做這份練習冊。”
時暮支支吾吾:“我、我明天洗,你先去吧。”
不確定那四只鬼還在不在,不在最好,要是在,被看到可就麻煩了,保險起見,時暮決定多觀察幾天。
傅云深臉立馬沉下:“你從搬進來就沒有洗過澡,尤其你還……”
吃了他繼母。
想到周植還在,傅云深打住,轉而道:“去洗。”
他神執意,時暮癟癟,放下手機,拿著換洗服不不愿進了浴室,想了想,又折出來,取了一道辟邪符在了門上。
正頭發的周植眼神崇拜:“暮哥想的可真周到。”
傅云深沒有說話。
進浴室的時暮把四周檢查了個遍,確定沒有邪的東西敢出來后,才放心的下了服。
那個假丁丁戴了幾天,如今松開,覺得整個人都解放了。時暮先接了一盆水把假丁丁清洗干凈,隨之放在浴室干燥晾曬。
水龍頭打開,沐浴在熱水下的時暮舒服的嘆息一聲。
鏡子里,看到自己還是蒼白瘦小的模樣,雖然連續喝了幾天牛,但個子并沒有長多,時暮了平坦的,又看了看自己的,表若有所思。
過些天天氣變得愈發炎熱,育課和平常都會換上運衫,作為一個男孩子,時暮自然避不開打籃球踢足球這種活,到時候一服一抬手,別人看到上的,鐵定會追問。
Advertisement
這天生發淺,胳膊上和上連個孔都看不見,就連某都算得上,至于腋下那稀疏的腋……早就被原主刮干凈了。
不行,其他地方不長可以找借口糊弄過去,腋必須要留著,不然一點男子氣概都沒有!!傅云深肯定會懷疑的!!
連腋都不長的男孩子,怎麼配和大佬做兄弟!
洗完澡,時暮翻出刮胡刀,裝模作樣在臉上劃拉了兩下。
這款刮胡刀聲音有些吵,著門,特意讓外面那倆個人聽清楚了。
隨后,時暮重新穿戴上假丁丁,神清氣爽出了浴室。
周植趴在床上,一臉艷羨的看:“暮哥,你都開始刮胡子了呀?”
時暮著臉,神驕傲:“沒辦法,發育的有些快。”
周植更加羨慕:“真好,我哥幾個都開始長胡子了,就我不長。”
時暮安著他說:“放心放心,你以后會長出來的。”
嘚瑟極了,就差沒直接在臉上寫“囂張”和“膨脹”這四個字。
此時傅云深已做完了習題,他放下筆,微微活了兩下關節,好看細長的眼眸錯落在時暮上,角向上一揚,“時暮。”
時暮后背一僵,“干、干嘛。”
“沒什麼。”他笑意深了深,“就是提醒你,下次去買個泡沫,那樣刮不扎臉。”
說完,傅云深起去了浴室。
“……”
這年頭男人刮胡子,還要泡沫的???
時暮覺得自己還是對男人了解的太了。
晚點熄燈后,剛搬進來的周植激的怎麼也睡不著。
他在上鋪翻來滾去,發出的聲音擾的時暮和傅云深都難以睡。
傅云深忍無可忍,抬腳踹了下上鋪床板,冷著聲兒:“別。”
Advertisement
“我睡不著啊……”周植看著頭頂的天花板和旁空空的位置,心里有些慫。
他把被子往上拉了拉,翻說;“你們知道415發生的那個事兒嗎?”
傅云深沒說話,時暮倒是來了興致。
睜開眼:“什麼事兒?”
得到人應和后,周植格外激:“就是……原來住在這里的四個人集自殺,可邪乎呢?”
時暮一聽,也來了興致:“那你講講。”
周植低聲,一字一句慢悠悠道:“那是冬天,周六,學生們都回了家,只留下這四個高三畢業生在學校。等次日舍管老師查房時,看到415房門閉,覺得不對,就強行開了門,結果你們知道他看到了什麼嗎?”
時暮努努,配合的問:“看到了什麼?”
“屋子中間放著一個炭火盆,兩邊是酒杯,四個人躺在各自床上,和睡著一樣。他們啊……燒炭自殺了,你說說,邪乎不邪乎,自從這事兒發生后,學校再也不允許學生在休息天留校了。”
時暮閉上眼,要是以前,肯定覺得這故事邪乎,可是現在……不得那四個男鬼都過來,一個油炸,一個紅燒,一個冰鎮,一個干鍋。
咕嚕。
不說了,開始了。
這吃鬼就像是嫖娼,第一次覺得惡心,完了又想著第二次。
“暮哥,深哥,你們都睡了嗎?”
良久沒有得到回話,周植鼓了下腮幫,拉起被子也閉上了眼。
聽著耳邊傳來的均勻呼吸,傅云深翻了個,了無睡意。
那四個人哪是什麼自殺。
冬天冷,趕上停電和暖氣故障,再想到馬上分別,幾人心里都不好起來,于是他們帶來一盆炭火和兩瓶干白,準備暖著子就著小酒慶祝下畢業,沒想到幾人喝高,炭火又沒有完全滅掉,其中一個缺心眼的還關嚴了窗戶,就這樣,四個人在酒醉中全部悶死。
傅云深剛住進來時,那四個人一直抱怨說,他們本來想慶祝離別,沒想到再也沒離過。
但是,傅云深并不準備把這件事告訴上面那個傻子。
他想不通的事,自從時暮來后,那四個鬼都神奇般的消失了……
作者有話要說: 四個男鬼:談笑風生間打出GG_(:з」∠)_。
猜你喜歡
-
完結72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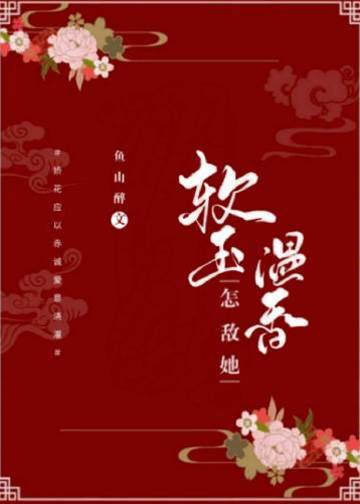
怎敵她軟玉溫香
提起喬沅,上京諸人無不羨慕她的好命。出生鐘鳴鼎食之家,才貌都是拔尖兒,嫁的男人是大霽最有權勢的侯爺,眼見一輩子都要在錦繡窩里打滾。喬沅也是這麼認為的,直到她做了個夢。夢里她被下降頭似的愛上了一個野男人,拋夫棄子,為他洗手作羹湯,結果還被拋棄…
21.9萬字8 11801 -
完結187 章

吻刺
清冷帶刺VS懶痞情種+【大學到都市丨破鏡重圓】 【正文完結,番外更新中】圈裏一幫公子哥的聚會。 方慈作爲宋裕澤的“妞”被帶去。 他倆早有聯姻之約,方家有求於宋家,想借聯姻穩固地位,在圈裏也不是什麼祕密。 由此,一貫清冷高傲的方慈,倒也識時務,成日裏扮乖巧,與宋裕澤出雙入對。 酒酣耳熱,玩玩遊戲。 方慈中頭獎。 她被要求選一個在場的異性,親吻一分鐘。 衆人起鬨看向宋裕澤。 在衆目睽睽中,方慈面無表情起身。 而後吻上了角落裏沒有參與遊戲、亦沒人敢惹的那一位。 - 聞之宴。 富了不知道多少代的頂豪聞家唯一繼承人。 偏又生得一幅讓人過目不忘的漂亮臉蛋兒。 性子痞壞得要命,眼裏又總帶着一股無所吊謂的野性和淡然。 他極散漫地張臂往沙發裏一靠,脣角一抹懶笑,仰臉接了方慈這個吻。 遊戲之後,好事的人打趣:阿慈跟聞少什麼時候這麼合得來了? 方慈:遊戲而已,我們不熟,更算不上合得來。 一門之隔。 聞言,聞之宴低眼意味莫名笑一聲。 - 當晚,無人知曉的舊別墅。 聞之宴同樣的姿勢靠在沙發裏,以一種暴露所有弱點的姿態,高仰起下頜。 喉結凸起,上方一條水墨蛇形紋身,被汗珠和水漬泅染,魅惑至極。 方慈在那蛇上狠咬了一口。 聞之宴吃痛地嘶聲,啞笑道,“你也就在老子這兒橫。” 片刻後。 他的聲音撞入耳膜,“你管這叫合不來?”
37.7萬字8.18 32879 -
完結257 章

嬌養王妹
從前,他是她含霜覆雪,清心寡慾的王兄。後來的每一夜,他俯身啄吻她的脣,燭火徹夜未休。 郗珣少年襲爵,歸藩途中撿了一個小糰子。 小饕餮的肚子永遠喂不飽。她會半夜狗狗祟祟爬床,睜着圓溜溜的眼睛朝他討要糕點。 就這般帶回家養着養着,養成了一個嬌俏玲瓏的小姑娘。 瓏月做了十多年權傾朝野的燕王幼妹,他的掌上明珠。 直到那一日,她真正的血脈親人尋上門來——瓏月頂着衆人嘲笑同情,灰溜溜地迴歸本家。 那自己走丟後被充作嫡女養的長姐時常憐憫她,“妹妹生的這般好,本該嫁個舉世無雙的世家公子,奈何這般名聲,日後不知婚姻大事何去何從......” “父親母親還是快些替妹妹挑個普通人家嫁出去,日後也好不受欺負。” * 那夜朦朧細雨,瓏月醉酒,醒來之後簡直欲哭無淚。 床榻之內竟躺着那位不近女色,清心寡慾的王兄!她當即倉促掩着衣衫妄想逃離。 榻上之人睜開雙眸,生平頭一次朝着小姑娘發狠,攥回那盈白細腰,將其囚犯回方寸之地。 “你這般驕縱的脾氣,除了爲兄,誰能忍你?”
40.9萬字8 28983 -
完結122 章

霍律師,我愿意
霍燃一直知道,他和蘇予是兩個世界的人。她是千金大小姐、成績斐然、溫柔善良;而他是嫌疑犯的兒子、家境貧寒、冷漠寡言。但從他見到蘇予站在臺上,宣讀入學誓詞的那一刻起,他就想將她據爲己有。四年相戀,四年分離,從窮學生到知名大律師,他所有的努力,都是爲了走到她身邊。久別重逢,他把她逼在牆角,揚脣輕笑,他說:“這一次,案子與你,我都要。”與你相遇,是不可抗力。贏了再難的案子,都不如贏得你的心。
19.1萬字8.18 466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