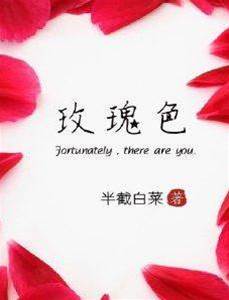《虐文女主只想煉丹》 第22章
蘇毓已經對這長袖善舞、左右逢源的爐鼎說不出話來。
繼假人之后,竟然連人都不放過!
他再怎麼自以為是,也不會以為蔣寒秋此舉只是為了膈應他——這鐵公一不拔,萬壑松可不是破銅爛鐵。
他把小爐鼎打量了一番,深邃的黑眸像是結了冰:“倒是小覷了你。”
薄一彎,譏嘲道:“莫非你又想去當蔣寒秋的爐鼎?”也不看看有沒有這功能!
小頂認真他這麼一說,又搖起來,稚川仙子雖說沒有圓臉圓肚子,可對真的特別好。
不但送劍,還請吃西疆帶來的杏脯,用角端和流沙釀的,皮薄,甜中帶著香。還從沒吃過這麼香甜的東西呢!
了腰間的鼓囊囊,眨眨眼睛:“仙子,也缺爐鼎嗎?”
蘇毓一噎,這爐鼎分明是故意氣他,這是找到了靠山,有恃無恐了?
他臉沉得能滴下水:“不缺。”就算缺也不是你這一款。
小頂有些失:“哦……”
同時暗暗松了一口氣,還是舍不得金道長的。
“你,別忘了跟,金道長說啊。”趁機提醒連山君。
這人壞得很,到時候沒準翻臉不認賬。
蘇毓:“……”肝疼!
……
自從稚川仙子回來,三日就有一堂劍法課——這間隔主要是用來給他們養傷的。
新弟子們苦不堪言,只覺墮煉獄,云中子卻很欣:“寒秋此次回來,中庸平和了許多。”最近都沒有人斷手斷腳了呢。
蔣寒秋:“妹妹還小,嚇著就不好了。”
云中子:“……”
小頂不但從來不挨打,蔣寒秋還變著法子給塞好吃的,棗子吃膩了,還有蒼兕干,奇香谷出產的清風冰丸,登龍山的千年神松子……
Advertisement
這些東西大部分都是能增長修為的天才地寶,隨便拿出一把都能讓普通修士大打出手,都被小頂當了打牙祭的零。
難為小頂,吃了這麼多好東西也沒把養刁,仍舊對歸藏廚子的手藝甘之如飴。
這些東西進肚子的時候,便有一氣息、味道、澤各不相同的“氣”融的經脈,如涓涓細流,匯肚子里的小鼎中——即使吃的是夾生焦飯和視,也有類似的效果,只是那“氣”微弱稀薄得多。
小頂只道誰吃飯都是這樣,便也沒有放在心上。
只有一件事讓十分苦惱——這幾天幾乎就沒停過,但肚子還是癟癟的,一點也不見長。
非但是肚子,臉也是原封不,倒是口的兩個圓丘似乎又高了些。
該長的不長,不該長的瞎長。
漸漸明白自己的眼和一般人不一樣,要不連山君那樣的貨怎麼在十洲男榜上排第一,金道長卻連三百名都不進去呢?
經常有人夸好看,別人也就算了,碧茶是從不騙人的——可是那又怎麼樣?好看不是給自己看,好看又有什麼用?
不管別人怎麼看,就是想要圓臉圓肚子,
……
轉眼之間,新弟子門已經半個月了,云中子的心法課終于開始教授引氣。
筑基即筑氣,引氣是修仙繞不開的基礎,不過每個門派學習引氣的方法都不一樣。
有的靠定觀,有的通過刻符寫篆,也有的門派借助法外。
歸藏的訓練法別一格,乃是疊紙鶴。
云中子讓人把一疊注了靈的雪白宣紙發下去,笑瞇瞇地道:“諸位可知,我歸藏為何以疊紙鶴練習引氣?”
他看了一眼沈碧茶:“沈小友請稍等片刻。”
Advertisement
沈碧茶聞言把一口氣憋回去,捂住。
云中子掃了眼舉手的學生,點了一個:“西門小友,你來說說看。”
西門馥搖了搖折扇,若有所思道:“小可以為,鶴乃羽族中之君子高士,品高逸,象我歸藏門人超逸拔俗的凌云之志。”
云中子了下,尷尬地笑了笑:“西門小友的想法,很有見地……”
沈碧茶憋得面紅耳赤,終于忍不住:“嗯,發人深省……噗哈哈哈,當然是因為摳啊!”
紙鶴是如今十洲通行的騎乘工。像歸藏這樣有頭有臉的大門派,不但要給門下弟子包食宿,包四季裳,也要包紙鶴。
一只紙鶴大約用一個月,一只紙鶴市價三十塊靈石,歸藏三千弟子,若是從外頭采購,一年便是上百萬靈石。
沈碧茶接著嘲諷:“假靈腦袋瓜有坑,怎麼不磕點靈丹治治,哦對,蠢病沒藥醫……”
西門馥額角青筋直跳,“啪”地收起折扇,握住腰間劍柄。
云中子為了避免同門相殘,只能向沈碧茶扔了個隔音罩打圓場:“稍安勿躁,兩位說的都不無道理,咳咳……”
他清了清嗓子道:“紙鶴雖是細,但修士居家出行都離不開它,騎乘、送信、打探消息……”
小頂聽到“送信”兩字,雙眼倏地一亮。
掌門接著道:“我們歸藏的紙鶴,馳名十洲,譽滿三界,素來十分搶手。諸位將來若是修仙修不出什麼名堂,憑著這門手藝也足以養家糊口。”
眾弟子:“……”好歹是三大宗門之一,掌門這麼勵志真的好嗎。
云中子給弟子們灌完湯,開始講解疊紙鶴的訣竅。
這活計看著不難,實則不容易。
一來手要巧——歸藏的紙鶴構造和外面的大路貨不一樣,足有三十六步,合天罡之數。
Advertisement
二來,手的同時需要在心中存想真鶴的模樣和姿態。
三來,同時還要吸納天地靈氣,同時將氣海中的靈氣經由經脈,導引到指尖,這樣疊出的鶴才能化生。
疊紙鶴也是件耗費靈力的事,筑基期的修士疊三只紙鶴便會把氣海空。
這些新弟子大部分還未筑基,疊個四五步,氣海便接近干涸。
若是一不小心空了,那滋味不比斷手斷腳好。
不一會兒,便有弟子用氣過猛,臉煞白癱在地,被傀儡人抬到醫館去。
小頂卻沒有這個困擾,如今最不缺的便是靈氣——整塊河圖石的靈氣都在里,就算不停歇地疊,也可以疊到天荒地老。
沒多久,就把第一只紙鶴搗鼓出來了。
按著云中子教的法子對著紙鶴的,“呼”地輕輕吹了一口氣。
只聽“噗”一聲,小小的紙鶴膨脹了一只……難以形容的東西。
它生著圓球似的子,胖得幾乎沒了脖子,一對小黑豆似的圓眼賊亮賊亮,短短的翅膀在側,幾乎看不見。
那東西一落地就“嘰嘰嘰”著,像個球一樣滿地打滾。
與其說是鶴,倒更像只母。
小頂眉花眼笑,拍拍它的屁:“快飛呀。”
眾弟子:“……”這也太強所難了。
這倒也有幾分志氣,拼命撲打短的小翅膀,差點沒把小眼珠都瞪出來,終于晃晃悠悠地升騰起一尺來高,然后“撲通”栽倒在地,“噗”一聲,又變回了紙鶴。
小頂有些失落,輕輕“啊”了一聲。
云中子給了一疊紙,安道:“第一次疊已經很不錯了,明日旬休,回去多練練便是。”
……
翌日清晨,蘇毓在東軒打坐,忽聽院子里傳來一陣“嘰嘰”、“咯咯”的嘈雜聲響。
Advertisement
他起往窗外一看,只見一院子的母滿地竄,時不時有幾只努力撲騰翅膀飛到半空,又栽倒在地,一眼去,說有四五十只。
那爐鼎趴在樹下的石棋坪上,一臉認真地疊著,傀儡人捧著臉在一旁看。
蘇毓眉頭一皺,這心機爐鼎,為了吸引他的注意竟然想出這種辦法,真是無所不用其極。
他打起竹簾,走到院中,正要開口訓斥一番,忽有一只不長眼的朝他狂奔過來,一頭撞在他上,原地打了個轉兒。
沒等他作,接著又有一只拍打著翅膀躥到他腳邊,屁一撅,“噗”地拉出一個紙團。
連山君何曾過此等奇恥大辱,便即沉下臉,袖子一揮,滿院的頓時變回紙鶴,然后紛紛自燃起來。
不等小頂回過神,疊了一早上的紙鶴便燒了灰,被風一卷,像一群黑蝴蝶飛走了。
呆呆地看著靜悄悄、空落落的院子,然后轉頭看向蘇毓,一雙黑葡萄似的眼睛里滿是委屈和難以置信。
張了張,到底什麼都沒說,雙地抿起來,默默垂下眼簾,又拿起一張紙繼續疊。
蘇毓清楚地看到的眼眶和鼻尖慢慢紅起來,心里莫名煩躁,一言不發地轉回了屋里。
他闔上雙目,繼續打坐,準備來個眼不見為凈,但是剛才那一幕卻在眼前揮之不去。
他了眉心,屈了屈手指,隔壁書房架子上便有一飛向院中。
片刻后,便聽傀儡人道:“我的回來啦。呃,你別太難過了,我們道君沒有心的。起碼腦袋還在,對不對?”
那小爐鼎不像往常那麼健談,只是吸了吸鼻子,甕聲甕氣地“嗯”了一聲。
傀儡人又道:“你疊那麼多紙鶴做什麼啊?”
爐鼎輕聲答道:“送信……”
“送給爹娘嗎?”
爐鼎道“我沒有,爹娘。”
傀儡人:“啊呀,那你是怎麼來的?”
不等回答,又問:“那你有別的親人嗎?”
爐鼎似乎有些猶疑,半晌才“嗯”了一聲:“我,就想給他,送信。”
蘇毓不覺起走到窗邊,著那神懨懨的小爐鼎。
“他住哪兒啊?也不一定要用鶴,讓誰幫你傳個音就是了。”傀儡人又問。
小爐鼎指指天:“在,那里。”
傀儡人一臉莫能助:“紙鶴飛不到那麼高的啊。”
話音剛落,那小爐鼎手一頓,剛疊完的落到地上,“咯咯咯”歡快地跑開了。
一垂頭,便有兩串淚珠落了下來。
蘇毓背過去,哪有人會笨到以為紙鶴能給死人送信,那爐鼎定是在扮可憐。
雖是這麼想著,他卻說服不了自己。
這戲做得未免也太真了。
蘇毓了額角,不打算再去理會,但一閉上眼,眼前便浮現起那爐鼎抿著“啪嗒啪嗒”無聲掉淚的模樣,心中的煩悶毫不減,反而愈演愈烈。
半刻鐘后,他還是忍不住站起,拿出一張裁好的白紙,開始疊紙鶴——疊一只紙鶴,一天的靈力就白吸了。
他自認倒霉,疊完紙鶴,起門簾,三步兩步走到爐鼎跟前,把紙鶴往棋枰上一撂,挑眉道:“哭什麼,賠你便是。”
那小爐鼎抬起頭,皺著眉頭,含淚的眼眸中滿是戒備和厭惡。
蘇毓到心口有些發堵,竟然管這爐鼎的閑事,他真是越活越回去了。
正要轉回屋,忽見那爐鼎臉一白,雙眉蹙,抱著肚子慢慢蹲到地上,轉頭對傀儡人道:“阿亥,我好像,要生了……”
猜你喜歡
-
完結81 章

天生撩人
梅幼舒生得嫵媚動人,在旁人眼中:心術不正+狐貍精+禍水+勾勾搭搭=不要碧蓮! 然而事實上,梅幼舒膽子極小,只想努力做個守禮清白的庶女,希望可以被嫡母分派一個好人家去過活一世。有一日君楚瑾(偷)看到她白嫩嫩的腳,最終認定了這位美豔動人的小姑娘果然如傳聞中那般品性不堪,並且冷臉上門將她納為了妾室。 梅幼舒驚恐狀(聲若蚊吟):「求求你……我不要你負責。」 君楚瑾內心os:欲迎還拒?果然是個高段位的小妖精。梅幼舒:QAQ 婚後每天都被夫君當做黑心x做作x惡毒白蓮花疼愛,梅幼舒表示:我TM是真的聖母白蓮花啊! 精短版本:小嬌花默默過著婚前被一群人欺負,婚後被一個人欺負日子,只是不知不覺那些曾經欺負過她的人,都漸漸地匍匐在她腳旁被迫要仰視著她,然而幾乎所有人都在心底等待著一句話的應驗—— 以色侍君王,色衰而愛弛! 瑟瑟發抖小兔嘰vs衣冠楚楚大惡狼 其他作品:無
25.8萬字8.25 26644 -
完結136 章

枷鎖
永昌二十年,林苑成婚的第五年,鎮南王反了。鎮南王世子晉滁為叛軍主帥,率百萬大軍一路北上,直逼京師。同年,京師破,天子亡,鎮南王登基,改元建武。建武二年,太子爺頻繁出入教坊司,每次會在同一個房間待上一兩個時辰不等,之后面色如常的整冠而出。他走…
43萬字8.33 24101 -
完結169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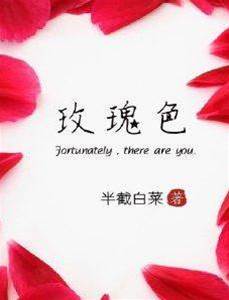
玫瑰色
總有一個人來愛你。 依舊熟女文,甜文。 第一次寫甜文。 儘量不膩歪。
22.4萬字8 9834 -
完結160 章

炙熱吻痕
【爆甜蘇撩?暗戀?校園?救贖?偏執甜寵】【蘇撩痞欲腹黑粘人狂??嬌軟嬌野人間甜妹】榕中人人都知道風雲人物霍馳,桀驁張揚,陰晴不定,人狠路子野,最不能招惹。一不小心和乖戾少年同班。初來乍到的薑荔不想成為被欺負的目標。秉著有錢就能解決一切的原則,她決定雇請眼前高大俊美的大佬保護自己。“他們都說哥哥很厲害。”薑荔笑容乖軟無害:“所以我可以請你保護我嗎?”大佬目光玩味,好整以暇看著她:“怎樣保護?24小時貼身這種?”結果一回校。大佬竟然跟霍馳長的一模一樣。薑荔:?—所有人都不相信薑荔能降伏像霍馳這樣桀驁的男人,背地裏都在打賭他們很快就分手。卻在一場賽車盛典頒獎的後臺上。看到剛在賽道上意氣風發的男人將一個漂亮的女孩抵在門前,親著她的紅唇,半討好半誘哄道:“荔荔乖,不玩獎牌好不好?”“早點讓哥哥成為你的男人,讓你玩個夠?”
31.1萬字8 14715 -
完結179 章

近我者甜
裴家小小姐裴恬週歲宴抓週時,承載着家族的殷切希望,周身圍了一圈的筆墨紙硯。 頂着衆人的期待目光,小小姐不動如山,兩隻眼睛笑如彎月,咿咿呀呀地看向前方的小少年,“要,要他。” 不遠處,年僅五歲的陸家小少爺咬碎口中的水果糖,怔在原地。 從此,陸池舟的整個青蔥時代,都背上了個小拖油瓶。 可後來,沒人再提這樁津津樂道了許多年的笑談。 原因無他,不合適。 二十五歲的陸池舟心思深沉,手段狠戾,乾脆利落地剷除異己,順利執掌整個陸氏。 而彼時的裴恬,依舊是裴家泡在蜜罐里長大的寶貝,最大的煩惱不過在於嗑的cp是假的。 所有人都極有默契地認定這倆be了,連裴恬也這麼認爲。 直到一次宴會,衆人看到,醉了酒的裴恬把陸池舟按在沙發上親。 而一向禁慾冷淡,等閒不能近身的陸池舟笑得像個妖孽,他指着自己的脣,緩聲誘哄:“親這兒。” 酒醒後的裴恬得知自己的罪行後,數了數身家,連夜逃跑,卻被陸池舟逮住。 男人笑容斯文,金絲邊眼鏡反射出薄涼的弧度:“想跑?不負責?”“怎麼負責?” 陸池舟指着被咬破的脣,低聲暗示:“白被你佔了這麼多年名分了?” 裴恬委屈地抽了抽鼻子,“你現在太貴了,我招不起。” 男人吻下來,嗓音低啞:“我可以倒貼。”
30.9萬字8 1904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