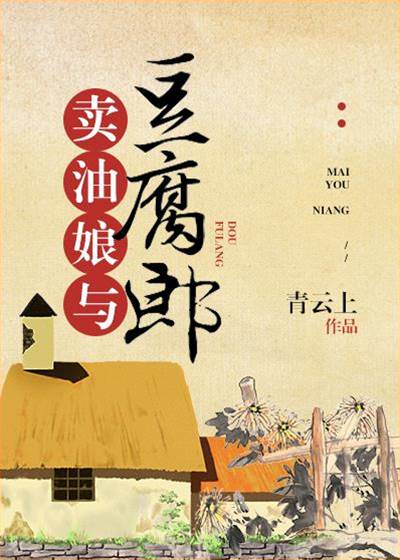《我在東宮當伴讀》 第80章 第 80 章
太子在殿議事,曹公公進殿時,朝臣都忍不住將目齊齊去。
這是發生了什麼天大的事?竟然曹公公都有膽子打斷朝議?
等聽完曹公公的話,才知道原來是死了個人,盛家的三小姐。
他們也沒怎麼聽說過,這是太子的未婚妻?好像也不是。那怎值得曹公公特意來稟?
曹緣抬不起頭,平生頭一回不敢去看太子的臉,頭頂朝他來的冷猶如利箭,他巍巍又說:“半個時辰前,人斷氣了。”
衛璟心里空了空,看著有些骨瘦嶙峋的雙手驟然案桌,他慢慢彎下腰,好像逐漸才反應過來曹緣說了什麼。
他彎著腰,張了張想說話,嚨里涌出劇烈的咳嗽,臉被咳得通紅,聲音像是從肺腑里出來的,聽著格外痛苦。
衛璟咳的幾乎不過氣來,撐著案桌的雙臂約約看得出來在發抖,手腕撐不起力道,麻木的鈍痛他一時半會兒直不起腰。
男人逐漸緩過氣,面罩冷霜,冷煞白,毫無,他克制著聲音里的抖,維持表面的平靜,吐氣道:“去盛家。”
已經是深夜。
時辰真的不能算早。
曹緣試著勸了勸,“殿下,已經……”
后半句被生生斷在嚨李,太子的冷眼朝他橫了過來,又劇烈的咳嗽,“備馬。”
曹緣想攔但是攔不住,急匆匆跟了上去。
-
盛府已經了套,先是云煙發現不對勁。
喊了兩聲姑娘沒有人應,床上的看起來和睡著了沒什麼兩樣。云煙的兩條都在打,跌跌撞撞走上前,還踉蹌了兩步,一下子跪坐在床邊,抬起手,輕輕推了推姑娘的肩,低喊了幾聲名字,依舊沒有回應。
Advertisement
云煙心里往下沉了沉,臉發白,用拇指去探的鼻息,已經沒氣了。
腦子里嗡的一聲,整個人往后坐倒。
門外的人忽然聽見一聲痛哭,才連忙推門而。
三小姐安安靜靜睡著了,邊的丫鬟哭的淚眼朦朧,站都站不起來了。
盛夫人被人扶進屋,聽見云煙的哭聲,頭暈目眩,眼前發黑,被人攙扶著才有力氣往前走,抖著嗓子喚的皎皎。
盛夫人走近了瞧見兒蒼白的臉,再也撐不住,昏倒了過去。
盛暄得到下人來遞的死訊時,恍然覺得還在夢中,他倒比妻子鎮定,還沒暈倒,至人還能站得住。
他也不敢信前不久還好好的人,怎麼說沒就沒了呢?
雖說大夫這兩天都有用委婉的言辭他們提前準備后事,但他心底還是存著能治好的僥幸,畢竟起初不是多大的病。
只不過是場風寒。
家中出了如此大的變故,府里需要可能撐事的人。
盛暄看著仿佛一下子老了十幾歲,鬢發花白,微弓著背,神萎靡,他不忍去看床上已經沒了聲息的人,一個字都說不出。
喜事變喪事,任誰都接不了。
其余二房的幾個妹妹半夜都被這件事驚醒,聽見敲梆的聲音,也聽見了東院傳來的呼聲。
就連住的很遠的盛清寧都聽見了靜,他睡眠本來就淺,被吵醒后點了燭燈,起披了件單薄的外衫,打開房門隨口問了值守的小廝,“外頭是怎麼了?”
小廝說:“三小姐……人沒了。”
盛清寧沉默一陣才想起來三小姐是誰,這個姐姐對他來說是陌生的。從小到大都沒有見過幾次,只記得后院有這樣一位連過年都不面的姐姐。
Advertisement
盛清寧先前只知道生病了,不知道這回竟然病的這樣重,“不是馬上都要親了嗎?”
“誰說不是呢。”大房和三房走不多,小廝才敢這樣說話,“三小姐也是福薄,眼看著都要嫁到侯府里去了。”
府里的幾位小姐,就屬三小姐嫁的最好。
這即將要過門去當世子妃,人竟然病死了。
府里依次點了燈,漆黑黑的府邸逐漸明亮了起來。
今晚恐怕是沒人睡得著。
盛清寧換了素白的裳,簡單洗漱后去了東院,那邊已經是一片哭聲。
屋子里已經站滿了人,沒有他落腳的地方。
回廊下的紅燈籠將漆黑的深夜照的亮,屋子里線不明,千工拔步床外層層床幔擋住了些視線。燭臺上的蠟燭已經燃盡,搖曳的火作著淺淺的煙霧。
盛清寧站在屋外遙遙相,看見癱坐在地已經哭腫了眼睛的云煙。
他蹙眉,心中奇怪。
云煙不是他二哥院里的通房嗎?
怎麼三小姐死了,也這樣的傷心,像是被人走了魂魄。
盛清寧聽著哭聲卻沒有什麼覺,他對這個姐姐沒什麼,心里也想到了別,他那個虛弱的哥哥知道了這件事肯定會很難過。
弱不風,格弱,一定會哭。
畢竟是一母同胞的親妹妹。
盛清寧的目在屋子里掃了兩圈,卻沒有看見他的哥哥。
于是,他更加覺得奇怪了。
“二爺呢?”
“二爺也病了,先前是被管家推著椅過來看了看。”
“嗯。”
盛清寧有些驚詫,他竟然難過的連站都站不起來。
他認真思考著,等到明日還是去看看他的兄長,安兩句,人死不能復生,也好他不要太難過了。
Advertisement
盛清寧又開始胡思想,如果是他死了,哥哥會這樣傷心嗎?
恐怕不會。
哥哥這麼討厭他。
盛清寧并未多留,實在是太吵了。
哭聲落在他耳邊,讓他覺得頭疼。
天邊已經泛起微白,天都快要亮了。
盛清寧正打算回去休息時,府門外一陣馬蹄疾聲。
太子騎著馬匆匆趕來,男人下馬隨手將馬鞭扔給邊的人,他的面如覆寒霜,利刃般的視線一寸寸掃過,命令親衛將盛府里里外外都圍了起來,一只蒼蠅都不許飛出去。
衛璟還是覺得是使的謀詭計。
一定是不愿意嫁人,才想用假死的法子。
說不定現在躺在床上已經被梁換柱,換了別人。
衛璟來的路上就在想要怎麼懲罰,怎麼能用自己的命開玩笑?
這人就是欺怕,記吃不記打。
就是不能對太好。
就是不能為的眼淚心。
不能一次次被拿了肋,用通紅的眼睛看著你,再說兩句楚楚可憐的話就放過了。
既然不想親,那大婚就作罷。
衛璟一定會親手將綁回東宮,將捆在床上哪兒都去不,現在還不喜歡自己不要,關上幾個月,朝夕相對,培養。
他還要改掉挑食的病,一定會盯著好好吃飯。
不吃的藥膳,也得一口不剩全部都灌下去。
不僅要鎖門,還要將窗戶都封死。
的太弱了,不就生病。
風不能吹,雨不能淋。
當金雀細滋養在籠中才能活得長久
不是喜歡做?也不能再讓去做。
不會懶,留在場只會日日被人欺負。
衛璟想了很多懲罰的法子,等真到了盛府,腦子里只剩下一個念頭——
Advertisement
要將帶回東宮關起來。
哪里都不讓去,誰也不讓見,先養好再談條件。
嗚咽的哭聲從不遠傳到男人的耳里,他俊秀的眉頭打了結,男人面無表看著屋子里已經跪了一地的人,“跪什麼?”
沒人敢搭話。
甚至他們都不知道太子怎麼會突然出現在這里。
云煙還趴在床邊痛哭,嗓子早就已經哭啞了。
衛璟認得,“你起來。”
嗓音低啞,沉寂幽冷。
云煙的眼睫還掛著新鮮的淚珠,不控制的噎。慢慢站起來,眼淚依然順著臉頰往下流淌。
太子盯著的眼睛里有濃郁的殺氣,漆黑瞳仁悄聲無息看著,扯起角,聲音極冷,仿佛從地獄而來,泛著幽幽寒意,“把眼淚給孤忍回去,閉。”
“敢發出一丁點聲音,孤就殺了你。”
云煙忍著哽咽聲,捂住不敢再哭。
衛璟看著很鎮定,靜無波瀾,他屋子里的其他人都滾出去,不許他們發出任何聲音。
門外的小廝已經掛好了白皤,白燈籠、白蠟燭夜都已從庫房里拿了出來,小心翼翼換上。
盛暄他們去布置靈堂,說完這句話他也沒了力氣,跌坐在地,讓人扶回房間休息。
衛璟抬起腳步,緩慢走到床邊。
他手將礙事的床幔掛回金鉤,面容祥和睡在枕被里,圓潤致的下藏在被中。
除了臉比常人白皙,并沒有其他的不同。
很安靜,很乖巧。如綢的長發枕在的前,濃烏黑的睫落在眼底打出一片青影,只是睡著了。
衛璟的眼睛只盯著的臉,無聲無息用目描繪的廓,五都漂亮。
他握住的手,有點涼。
不過好在他的掌心是溫熱的,很快就能將捂暖。
衛璟輕掐著的下,“不要睡了。”
他蹙眉,嗓子深出來的聲音有些難聽,“我不信你。”
的手掌好像怎麼捂都捂不熱。
衛璟攥著手,“你睜眼,孤就不計較今晚這場鬧劇。”
依然是無人理會。
過了很久。
男人抬起手指輕輕落在的鼻尖,沒有呼吸。
的口也沒有起伏,沒有脈搏。
也冷冰冰的。
只剩下最后一點余溫。
衛璟覺得自己沒事,除了心頭空,他并沒有任何的不適。
他了角,還想再說什麼,沙啞的嚨忽然溢出鮮。
他若無其事將發腥的咽了回去,又用帕子不慌不忙干凈邊的跡。
裝的如何像樣都沒用,拭跡的拇指是抖的,男人眼前忽然浮現前不久在夢中看見的深黑檀木所刻的牌位。
死氣沉沉的牌位上寫著的名字。
衛璟沒能住嚨深的痛楚,弓著腰咳出了鮮。
前的襟,濺著深紅的。
猜你喜歡
-
完結491 章

鳳花錦
仵作女兒花蕎,身世成謎,為何屢屢付出人命代價? 養父穿越而來,因知歷史,如何逃過重重追捕回歸? 生父尊貴無比,一朝暴斃,緣何長兄堂兄皆有嫌疑? 從共同斷案到謀逆造反,因身份反目; 從親如朋友到互撕敵人,為立場成仇。 富貴既如草芥, 何不快意江湖?
90萬字8 10797 -
完結536 章

傾城醫妃不好惹
一朝穿越,成了不受寵的秦王妃,人人可以欺辱,以為本王妃是吃素的嗎?“竟敢對本王下藥,休想讓本王碰你....”“不是,這一切都是陰謀....”
97.2萬字8 114618 -
完結492 章
穿越醫妃不好惹
穿越前,她是又颯又爽的女軍醫,穿越后,她竟成了沒人疼的小白菜,從棺材里爬出來,斗后媽,氣渣爹。夫婿要悔婚?太好了!說她是妖孽?你再說一個試試?說她不配為后?那我做妃總可以了吧。只是到了晚上,某皇帝眨巴著眼睛跪在搓衣板上,一字一頓地說天下無后是怎麼回事?
88.1萬字8 19611 -
完結14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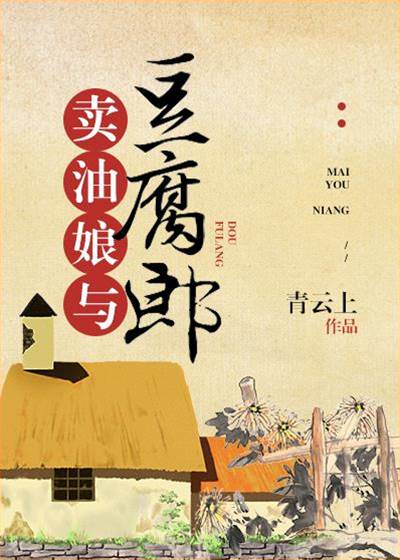
賣油娘與豆腐郎
每天早上6點準時更新,風雨無阻~ 失父之後,梅香不再整日龜縮在家做飯繡花,開始下田地、管油坊,打退了許多想來占便宜的豺狼。 威名大盛的梅香,從此活得痛快敞亮,也因此被長舌婦們說三道四,最終和未婚夫大路朝天、各走一邊。 豆腐郎黃茂林搓搓手,梅香,嫁給我好不好,我就缺個你這樣潑辣能幹的婆娘,跟我一起防備我那一肚子心眼的後娘。 梅香:我才不要天天跟你吃豆腐渣! 茂林:不不不
77.7萬字8 12093 -
完結257 章

春水搖
赫崢厭惡雲映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 她是雲家失而復得的唯一嫡女,是這顯赫世家裏說一不二的掌上明珠。 她一回來便處處纏着他,後來又因爲一場精心設計的“意外”,雲赫兩家就這樣草率的結了親。 她貌美,溫柔,配合他的所有的惡趣味,不管他說出怎樣的羞辱之言,她都會溫和應下,然後仰頭吻他,輕聲道:“小玉哥哥,別生氣。” 赫崢表字祈玉,她未經允許,從一開始就這樣叫他,讓赫崢不滿了很久。 他以爲他跟雲映會互相折磨到底。 直到一日宮宴,不久前一舉成名的新科進士立於臺下,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包括雲映,她脊背挺直,定定的看他,連赫崢叫她她都沒聽見。 赫崢看向那位新晉榜首。 與他七分相似。 聽說他姓寧,單名一個遇。
38.5萬字8.18 468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