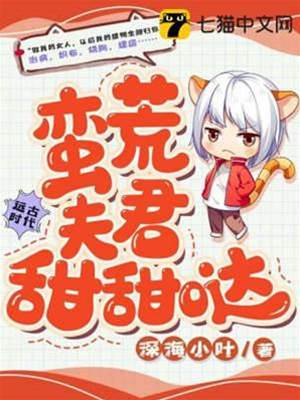《春日宴》 第61章 我什麼也不期待
正說著話呢就被人打斷,陸景行側頭,微微皺眉:“不是說可以停留三炷香?”
要是紫君沒來,別說三炷香了,五炷香都可以。但……一想到君上那眼神,獄卒一邊發抖一邊搖頭:“您還是先請吧。”
察覺到不對,陸景行頓了頓,看著李懷玉道:“有什麼想吃的?下回我帶來給你。”
懷玉吧砸了一下,說:“想吃梅子。”
“好。”寵溺地點頭,陸景行道:“等著我。”
懷玉沒抬眼看他,只乖乖地點頭,心里七八糟的,沒個頭緒。
陸景行走了,銀雪袍消失在漆黑的天牢里,怔愣地抓著柵欄,忍不住嘆了口氣。
想娶嗎?要是在遇見江玄瑾之前遇見他,他早些說這句話,指不定丹長公主就真的有駙馬了。
緣分真是個會捉弄人的東西。
“很舍不得?”佛香繚繞的聲音在不遠響起。
李懷玉一驚,猛地抬起頭往外看,就見江玄瑾面無表地往這邊走了過來。
幾天沒見而已,恍惚間卻好像都要不記得他的模樣,眼下再看,覺還真是陌生,那雙墨的瞳子看著,里頭的東西好像不太友善。
沒注意他問的是什麼,只抿抿,退后兩步喊了一聲:“君上。”
陸景行來,就高興地同人嬉笑打罵,他來,就變這副冷淡疏離的模樣?江玄瑾嗤笑,在柵欄面前站定,朝旁邊的獄卒指了指鎖:“打開。”
懷玉瞪大眼,一路退回那竹床邊,了拳頭。
鎖鏈“嘩啦”一聲落下,牢門推開,江玄瑾步進去,盯著床邊那人,眼神幽暗。
“君上還有什麼想問的?”懷玉不安地皺眉。
“沒有要問的,就不能來?”
Advertisement
“……”都到如今這個境地了,若是沒有要問的,他為什麼要來?懷玉茫然,抓著床上的被子,想問他兩句什麼,又咽了回去。
目往下,落在手里拿著的東西上。江玄瑾手,緩慢地將它拿起來。
“很喜歡?”打量著這方手帕,江玄瑾眼里滿是譏誚。
懷玉一愣,下意識地想搶,冰冷的手指上他的,又了回去。
這就是陸景行給手用的,談什麼喜歡不喜歡?李懷玉抿,低著頭不吭聲。
心虛嗎?眼里更深,江玄瑾俯,手撐在坐著的床邊,在耳邊道:“你喜歡的東西,我都不會讓你得到的。”
像尖銳的針,倏地扎在心口上,李懷玉低哼一聲,垂了眼別開頭。努力假裝自己聽不見他說話。
江玄瑾是有些惱的,以前是有說不完的話,他只用聽就知道在想什麼。可現在這張臉,冷淡得像是不想再與他有毫牽扯,不管他說什麼,都沒有反應。
像是徹底不要他了一樣。
下頷繃,江玄瑾手,住的下,強迫抬頭看著自己。
“君上!”旁邊的徐仙嚇著了,連忙開口,“您別殿下,子不好!”
略帶戾氣地看他一眼,江玄瑾喊了一聲:“乘虛。”
乘虛會意,讓獄卒打開牢門,朝著徐仙拱手道:“大人這邊請。”
“你們想干什麼?”徐仙搖頭,“君上,殿下真的……”
“很吵。”江玄瑾打斷他。
乘虛皮子一,不敢再耽擱,與獄卒一左一右架起徐仙就走。
李懷玉皺眉:“他上還有傷。”
“與我何干?”
冷的態度,像是生了天大的氣,薄都抿著,眼里一點溫度也沒有。
懷玉閉了,苦笑。
Advertisement
的確是與他一點關系也沒有了,不管是徐仙還是,都是站在他的對立面、十惡不赦的罪人罷了。
這表有些刺眼,江玄瑾忍不住手,將的角按住。
有些干裂,還有不結痂的口子,看起來憔悴得很。白珠璣的子弱,比不得原來的丹。在這種地方呆著,怕是不用等重節,就要形神俱滅了。
“我臉上臟。”懷玉低聲道,“君上向來干凈,還是放開吧。”
陸景行得,他不得?江玄瑾冷笑,手順著的臉頰往后,直接扣住的后頸,往自己的方向一拉——
干燥糙的被人含住,李懷玉驚得睜開了眼。
江玄瑾那雙墨瞳近在咫尺,上的梵香味將這滿牢房的腥都住了,輾轉在的上,他輕輕挲過那些口子,然后著舌尖,一點一點地,溫地安它們。
濡麻的覺,從瓣上傳到了心口。
懷玉打了個寒戰,眼睛的反應比腦子更快,洶涌而上的眼淚頃刻模糊了視線。
這是……干什麼?
想推開他問問,然而這一推,好像更加惹惱了他,扣著后頸的手用的力氣更大,完全沒有要放開的意思。
是……覺得可以原諒了嗎?懷玉傻傻地想,江玄瑾這種有潔癖的人,還愿意吻,難道是消氣了?
然而,片刻之后,江玄瑾自己松了手。
他的眼神依舊沒什麼溫度,表里還帶了兩分譏諷:“殿下在期待什麼?”
一盆涼水從頭淋到腳,懷玉怔愣地看著他的臉。等明白過來自己是被耍了之后,緩緩抬手,把眼里多余的水珠都抹了。
江玄瑾的確是跟學壞了,都會這樣戲弄人了。
低低地笑了一聲,懷玉搖頭:“我什麼也不期待。”
Advertisement
“是嗎?”抬手替拭去一點的淚花,江玄瑾勾,“微臣看見的好像不是這樣。”
這個人,就是來報復的,想像之前一樣,用來做最狠的報復。
不起的。
輕吸一口氣,懷玉恢復了以前那吊兒郎當的模樣,勾笑:“君上弄著本宮的傷口了,疼得出了眼淚,能說明個什麼?”
冰涼的水珠抹在指尖,沒一會兒就干了,江玄瑾就著帕子了手,慢條斯理地問:“殿下這意思是,對微臣的逢場作戲結束,再無半分?”
“君上還想與本宮有?”笑,“不怕再被本宮騙一次嗎?”
心里有火,江玄瑾面上卻越發鎮定,看著的臉,低聲問:“殿下騙人的時候,一貫喜歡連自己一起騙?”
什麼意思?懷玉不解。
江玄瑾捻著佛珠,捻一顆念一個名字:“就梧、白皚、清弦、赤金。”
梧皚弦金,吾玄瑾。
一向與紫君不對盤的長公主,卻是老早就將自己的心意寫在了自己面首的名字里。惡名昭彰的禍害,上的卻是清如明月的忠臣。
這是何等的荒謬,何等的妄想,何等的可笑?
李懷玉的臉“刷”地就白了,怔然地看著面前這人,了許久才吐出話來:“誰告訴你的?”
轉念一想,也不會有別人了。
懷麟。
地了兩口氣,手抓了前的料,又急又怒。
藏了那麼多年的心事,在任何時機被揭穿都沒關系,可為什麼偏偏是在這個時候,這種場景?
眼前這人眸子里的輕蔑實在太傷人,想避開,卻是無可避。
“你這種人,是不是慣會假裝一往深,然后風流,留?”江玄瑾道,“這個字,你也配說嗎?”
Advertisement
十幾個面首,加一個形影不離的陸景行。飛云宮里夜夜笙歌、靡不堪,憑什麼,到底是憑什麼在說他?
臉越來越蒼白,懷玉僵地坐在竹床上,小腹墜疼得厲害。
“我……”咬牙,額頭的冷汗也慢慢冒了出來,“我不配說什麼喜歡不喜歡,不,所以你且當那只是個巧合。”
怒意更甚,江玄瑾抬眼看向,凌厲的眼神像是打算把釘穿。
然而,目及這張慘白無比的臉,他嚇了一跳,下意識地就要手上去探的額頭。
李懷玉一把將他的手揮開,勉強笑道:“落得這下場。也是我罪有應得,你不欠我命了,我也不欠你什麼,君上,往后你我二人,真的可以各不相干了。”
“你先閉!”意識到好像不太對,江玄瑾將雙手疊,一手鉗制住,強地用手背了的額心。
分明在出冷汗,也白得嚇人,但這額頭卻是滾燙,人也虛弱得像是要坐不住。
“乘虛!”他回頭,“去請個醫來!”
李懷玉慢慢撐著床躺下去,閉眼道:“不必麻煩了,我睡一覺就好。”
這副模樣。睡一覺當真能好?江玄瑾臉很難看,揮手讓風去,自己站在床邊,死死地盯著。
懷玉淡聲道:“你請人來我也不會診的。”
“不是你自己的子,就當真不惜了?”江玄瑾聲道,“可我還要給白史一個代,斷不能讓你死在這牢里。”
這樣啊,懷玉輕笑:“那我就更不會診了,君上,我最喜歡的事,就是與你作對,你忘記了?”
昔日紫君進飛云宮教禮儀,讓坐有坐相,偏翹起二郎,讓走路姿態端莊。偏學男兒家的八字步,嬉皮笑臉上躥下跳,就是不肯聽他的話。
江玄瑾自然是記得丹有多可惡,黑著臉問:“這樣做對你有什麼好?”
“沒有好啊。”勾,聲音卻越來越小,“就是喜歡看你生氣而已……”
“已”字都沒說出來,牢房里就已經歸于了寂靜。
“李懷玉?”江玄瑾微驚,手想去握的手,可低眼看過去才發現,這人兩只手握住手腕,竟是將脈搏護了個嚴實。
怎麼會有這樣的人?江玄瑾氣極反笑,試著掰了掰,發現得實在是,強行掰開,怕是要傷著。
一向冷靜自持的紫君。眼下突然暴躁得像一頭獅子。
醫來了,診不了脈,頂著君上冰冷的眼神,戰戰兢兢地道:“這位姑娘應該只是底子差了,不住牢里的環境。”
要是別的都還好說,不住牢里的環境要怎麼辦?風聽著都很為難,抬眼看過去,他家主子的臉更不好看。
“你留在這兒看著。”江玄瑾道,“需要什麼藥,讓風去準備。”
醫惶恐地看著他:“君上,這……”
這兒可是死牢啊!
“有問題?”他回頭問,聲音冷得像是剛從冰窟里撈出來。
醫不敢說話了,抖著子低下了頭。
死牢里的人早晚都是要死的,實在不明白有什麼醫治的必要。
江府,韶華院。
江深一邊看奴仆收拾東西。一邊用余打量坐在旁邊的徐初釀,已經很多天沒同他說話了,見面除了行禮就是沉默,眼簾垂著,也不知道在想什麼。
輕咳兩聲,他抿道:“你還有什麼東西要收拾?別等出了門才發現了。”
徐初釀在走神,沒聽見他說話,一雙眼盯著屋角放著的花瓶,直愣愣的,沒個焦距。
江深微惱:“聾了?”
這一聲幾乎是吼出來的,徐初釀驚了一跳,睫了半晌,低頭問:“您說什麼?”
氣不打一來,江深怒道:“我說不帶你走了,你自個兒留在京都吧!”
重節將至。江家的人都有登高遠的習慣,恰逢京都有,老太爺便決定舉家去爬臨江山,除了江玄瑾,府里的人都去。
徐初釀作為他的夫人,自然也是要去的,他說這個只不過是氣話。
然而,旁邊這人聽著,竟點了點頭:“好。”
江深一噎,覺自己早晚得被氣死:“好什麼好?”
徐仙獄,要不是在江府,早就被一并牽連了,眼下帶出去避風頭,還不識趣?
莫名其妙地看他一眼,徐初釀道:“您說不帶我去,又氣個什麼?”
“我……”江深咬牙。
自從上回回了娘家,兩人之間和諧的狀態就被打破了,他知道自己當時說話過分了,后來一直想彌補一二,但這個人油鹽不進,不給他機會。
猜你喜歡
-
完結1385 章
腹黑小萌妃:皇叔,吃上癮
“皇叔,夠了,今晚夠了。”“不夠..”俊美的男人在她耳邊喘著粗氣,聲音磁性而又沙啞,“今晚再戰十次都可以。”葉桃安,華夏商業霸主更是有名的醫師,一朝穿越,變成了人人欺辱的王府大小姐。曾經的輝煌已經成爲過去?廢物,算計,屈辱?不,那具身體裡早已換了強大的靈魂!天生神體,契約神獸,靈丹無數,就連神器她都不缺.
124.9萬字8.08 512816 -
完結227 章
腹黑王爺俏醫妃
她是二十一世界的外科醫生,在香港境內頗有名氣,擁有"金刀"的稱號,是香港"醫者愛心基金會"的形象大使,被世人稱"天使的化身".這是她給人在屏幕的印象,然而在現實生活中她活潑俏皮,清爽明朗.這樣她在獲得一塊玉蘭花玉墜時,穿越了,穿越了還好,竟穿越到全是男人的地方,迫使她不得不女扮男裝,卻碰上冷峻腹黑的王爺,然而她卻是皇上欽點的皇后,左相的愛女…
34.1萬字8.18 60380 -
完結369 章

一胎三寶:神醫狂妃,太難寵
自爆身亡,沒想到穿越到了低階大陸的廢柴小姐身上,什麼?穿一送三,她懷裡還有三個絕世逆天的小寶寶! 既然重活一世,那她就帶她的三個崽子!將這個世界攪的翻天覆地! 曾經傷害過自己和三寶的人,都統統給我洗好了等著抹脖! 某男,“娘子,今晚輪到相公陪了吧?相公新學的按摩技術一流,你可得好好試試!” 某女嫌棄臉,“你先問問大寶二寶三寶同不同意?” 某男把三寶揍服之後,“娘子,現在可以了吧?” 某女不耐煩的指了指肚子,“你再問問懷裡的四寶五寶六寶同不同意?” “什麼?!”某男崩潰臉,“又要喜當爹了!
67.7萬字8 148327 -
完結228 章
東宮有福
福兒六歲進宮,本打算窩在尚食局混日子,混到二十五就出宮,誰知被挑給太子當引導人事的司寢宮女。宮女們都說:“福兒這下要飛上枝頭了!”福兒確實飛上了枝頭,可沒幾天叛王奪了位,太子也不是太子了,而成了廢太子。…
75.9萬字8.23 133049 -
完結66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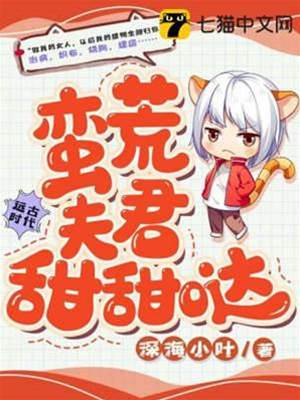
蠻荒夫君甜甜噠
薛瑤一覺醒來竟穿越到了遠古時代,面前還有一群穿著獸皮的原始人想要偷她! 還好有個帥野人突然出來救了她,還要把她帶回家。 帥野人:“做我的女人,以后我的獵物全部歸你!” 薛瑤:“……”她能拒絕嗎? 本以為原始生活會很凄涼,沒想到野人老公每天都對她寵寵寵! 治病,織布,燒陶,建房…… 薛瑤不但收獲了一個帥氣的野人老公,一不小心還創造了原始部落的新文明。
117.6萬字8 36849 -
完結119 章
掌上嬌卿
別名:和離后嫁給前任他爹 沈嫣與鎮北王世子謝斐成婚三年,因自己口不能言,身有缺陷,壹直小意討好。 可謝斐素來風流成性,毫無已有家室的自覺,呼朋喚友,夜夜笙歌。 沈嫣總以爲,只要自己再聽話懂事些,總有壹日能讓他收心,直到她做了壹個夢。 夢裏她身中劇毒,壹屍兩命,而凶手恰恰是她夫君養在別苑的外室。 夢醒之後,沈嫣望著空床冷枕,徹底寒了心。 - 後來,那鎮守邊關數年、鎮北王府真正的主人謝危樓班師回朝。 面對跪在自己腳下,執意求去的沈嫣,謝危樓扣在圈椅上的手緊了又緊。 良久,他喉嚨微不可察地滾動了下, “鎮北王府欠妳的,本王來還。” - 謝危樓手握重兵,權傾天下,卻是冷心禁欲,從不近女色,多年來身畔尤空。 當年凱旋回京,他不知打哪兒帶回個孩子,請封爲世子。隨著謝斐壹日日長大,形貌越來越不似他。 坊間議論紛紛,謝危樓面不改色。 唯獨面對沈嫣,他才頭壹回解釋:“本王身邊,除妳之外,從無旁人。” 【小劇場】 謝斐曾以爲,沈家幺女性情溫婉,亦愛慘了他,即便他做了什麽過分的事,隨意哄壹哄,她還是會乖乖回到他身邊來。 只是沒想到有壹日,她會親手遞上壹封和離書,眼裏清明澄澈,壹如當年初遇。 而她的目光,再也不會爲他停留。 謝斐悔不當初,爲了追回沈嫣,抛卻自尊,向她低頭:“阿嫣,不要離開好不好?” 話音未落,壹只大手伸來,把沈嫣壹把扯遠,男人居高臨下,冷嗤:“晚了。” 謝斐望著沈嫣被男人攬在懷裏,羞澀歡喜的模樣,心髒猶如刀絞。 這壹瞬他終于意識到,他那乖乖順順的小嬌妻,再也不會回來了。 【劇場二】 謝家這場鬧劇,許多人都在看笑話,只是礙于鎮北王威嚴,不敢光明正大議論。 沈嫣對此假作不知,心中亦有些難堪。 宮宴這日,謝危樓卻大大方方牽過她的手,將她介紹給所有人—— “這是鎮北王妃,本王愛妻沈嫣。” 目光銳冷如電,壹壹掃過衆人。 很快,流言銷聲匿迹,世上再無人敢言。 回到府中,謝危樓輕握沈嫣柔荑,眯眼耐心地哄,“今日怎麽不喚夫君了?” * 她做過世子妃又如何? 壹日是他鎮北王府的人,便終身都是。 他若要她,天底下誰敢說個不字? 看文指南: 1、應該是男二上位的梗,但作者心中謝危樓才是男主,前夫男二; 2、男女主有前世今生梗,這壹世相愛在女主和離之後,關系存續期間不會有任何感情暧昧; 3、女f男c,男二非親生; 4、女主啞疾有原因,會好; 5、年齡差16(18·34); 6、作者本人xp,不喜點叉。
37.5萬字8 1517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