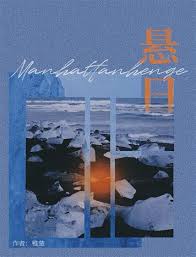《願以山河聘》 第86章 劫數
姬越看著衛斂毫不猶豫地將那藥撒地面,神一怔。
“……阿斂。”
衛斂半蹲在他前,雙眸泛紅,令人心憐的模樣讓姬越都忍不住想要抱一抱他。
可剛抬起手,目及臂上那駭人的,就又了回去。
……太髒了。
一的與塵灰。
阿斂這麼乾淨,不會喜歡的。
姬越剛收回手,就被青年輕輕抱住。
他子一僵,下意識別過頭:“阿斂,別看我。”
“我都不怕你。”衛斂問,“你又在怕什麼?”
“姬越,你是是醜,我不嫌棄,是強是弱,我不在意,是貴是賤,我更不關心。但是你不可以丟下我。”衛斂哽咽道,“你是我夫君,我們本該生死與共。可你總自己擔著,你什麼都不說,擅自做了這樣的決定,你想過我嗎?”
“你是在為我好嗎?”衛斂說著就緒崩了,低頭哭得厲害,“你準備得那麼周全,可我不需要……姬越……我不需要!你付出這麼大的代價,為的就是讓衛斂一輩子痛苦地活著麼?你就這麼恨我?”
姬越一時慌了,手忙腳地安他:“阿斂,別哭。你這樣……”
讓他也很難。
“你也會心痛嗎?”衛斂質問,“你連這一時心痛都忍不了,你怎麼敢我忍一世?”
姬越:“……”
姬越是真的慌了。
他從未見過衛斂哭得這麼厲害。青年是忍斂到骨子裡的人,以往最失控也不過是無聲落幾滴淚,何曾如此悲慟過。
肝腸寸斷,傷心絕。
他令衛斂這樣難過。
衛斂哭得說不出話。他兩個月來沒有流過一滴淚,終於在此刻盡數宣泄出來,趴在姬越肩上輕輕抖,上氣不接下氣,微弱的泣音聽得姬越心尖泛疼。
Advertisement
……他真的後悔了。
可怎麼辦?我更不能不救你。
“是誰在欺負我小徒弟啊?”忽然,一道清越如仙音的男聲傳來,霎時連天都似乎敞亮幾分。
姬越抬眼去,只見一名謫仙之姿的青男子一手拉著淨塵,一手拽著張旭文,一進來就將被綁粽子的張旭文扔在地上。
衛斂一頓,轉過,眼睫還沾著淚,目驚訝:“……師傅?”
驚了,他八百年不出現一回隻活在回憶中的師傅竟然面了。
“真是稀奇,有生之年竟能見我這小徒弟哭這樣。”君竹了下,對姬越讚賞道,“難得啊難得,你小子是個人才,令我這沒心沒肺的徒兒撕心裂肺的。”
衛斂:“……”
姬越怔住:“前輩?”
衛斂的師傅,他應該稱一聲前輩的。
只是沒想過衛斂的師傅會這麼年輕。衛斂時遇見他時,君竹便是二十多歲的青年模樣。如今這麼多年過去,他依然容未老,不知是駐有還是另有神通。
淨塵見到姬越容貌盡毀的模樣,雙手合十,念了一句:“阿彌陀佛,善哉善哉。”
“你這小和尚,也別張閉阿彌陀佛的。”君竹毫不客氣地拆臺,“我把你抓來時,你還躲著啃呢。”
淨塵:“……貧僧這是酒穿腸過,佛祖心中留。”
他好不容易吃一隻,突然就出現這麼一位神高人,二話不說抓著他地寸神行千裡,眨眼之間便到江州境,很嚇人的好嗎!
但他敢怒不敢言。
如此大的本事,想必是世外之人了。惹不起。
衛斂神一:“師傅,您有沒有辦法救他?”
“玉芝真是,有了夫君忘了師傅。”君竹佯裝不滿,“見了我也不關心關心師傅近況,開口就是讓我救別人。我怎麼教出你這麼個不孝徒弟來。”
Advertisement
姬越忍不住道:“阿斂遠赴秦國時,您並未出現。”
這個師傅當的其實也是不怎麼稱職的。不負責的師傅跟不孝順的徒弟,半斤八兩吧。
君竹瞥他:“我和玉芝說話,你別。”
姬越:“……”
衛斂垂眼,跪下道:“求師傅救他。”
君竹立刻扶他起來。
“九歲拜師禮後,你再未跪過我。”君竹輕歎,“如今倒為了這個男人……他果真是你的劫。”
“劫?”衛斂和姬越異口同聲。
“是啊。”君竹道,“還記得為師給你的預言嗎?”
“自然記得。”衛斂低聲,“及冠前需韜養晦,否則便有死劫。”
“為師千叮嚀萬囑咐。”君竹恨鐵不鋼道,“你還是在二十歲生辰前兩月鋒芒畢,功虧一簣。”
衛斂抿。
“我且問你,你是否將還魂丹給了他?而你,更是從那時起確定我家小徒兒本事不小?”君竹看向姬越。
姬越一頓,點了點頭。
他雖早對衛斂有所懷疑,可真正篤定時,卻是因為衛斂解去他毒的那日。
“這就是了,一顆還魂丹,害得玉芝鋒芒畢,十九年忍悉數白費。”君竹歎氣,“還魂丹可解百毒,治百病,保人日後一生康健,何等珍貴之。我這小徒兒本可用來解自己的毒,偏卻給了你,反暴了自己。”
姬越眸一變。
他竟不知……衛斂付出了這麼多。
衛斂不想多提此事:“師傅,我如今沒事,有事的是他……”
“你當然沒事。”君竹輕哼一聲,“他替了你的劫,你自然再不會有事。”
衛斂忽然啞聲。
君竹淡淡道:“你可知,今日染上這所謂瘟疫的,原本該是你。”
衛斂茫然。
Advertisement
君竹懶得再解釋,將淨塵推出來:“說清楚。別再話隻說一半,騙我小徒弟。”
淨塵:“……”
兩個月前,甘泉寺。
“姬施主不必多慮,那位施主是俗世中人,且命格本應極貴。”淨塵用了“本應”這個詞,讓姬越心下一沉。
什麼本應?
淨塵繼續道,“他上沾了仙氣……大概是得了機遇,曾被哪位世外之人授予本領,恰好能在此劫中派上用場。也只有他,能化解這場劫數。”
“那他可否平安?”
淨塵搖頭:“貧僧看到……死劫纏,兇多吉。”
姬越瞳孔一。
良久,姬越才問:“那又該如何化解?”
淨塵道:“施主可化。”
“正所謂一山不容二虎,一朝不容二龍。施主與那位施主同為真龍命格,按歷代慣例,勢必要鬥出個你死我活。只是兩位施主似乎是個例外……貧僧只見過雙龍相爭,也從未見過雙龍相。”
“姬施主已稱王多年,龍氣旺盛。那位卻尚在長,較為弱小,方有死相。這世上唯有施主與他命格相同,能夠代替他的命運。”
“此東南一行,禍起清平。若那位施主獨自前去,必死無疑,倘若姬施主一道前去,或有一線轉機。”淨塵道,“貧僧道行淺薄,只能推演出地點,並不能推算出究竟發生何事。但倘若姬施主前往,極大可能會將死劫轉至您上。您龍氣更盛,或許能平安度過,可更有可能一龍隕落。您為君王,您三思。”
姬越靜默片刻,道:“孤知道了。”
他已有了決定。
“孤的阿斂,舍命化蒼生之劫,那孤便以命換命,化他一人之劫。”
他渡蒼生,孤救他一人。
姬越要走時,淨塵卻又住他:“姬施主給那位施主下了毒?”
Advertisement
姬越一頓,心知淨塵神通廣大大,倒也不意外:“是,我正打算同他坦白,將解藥給他。”
淨塵說:“先別急著給。”
姬越凝眉:“為何?難道與他劫數有關?”
“時機未到。”淨塵道,“等到了災厄發生之地,時機,您再將解藥給他罷。”
原來衛斂的命格是那樣解釋的麼?
一朝不容二龍。他死了,衛斂便可登位。
衛斂是天命君王,一定能在接手這座江山後收服人心……而他,大概便是要死的。
從甘泉寺回來後的姬越就變得不對勁起來。
他愈發黏著衛斂,連榻上都不再憐惜。
他把每天都當生命最後一天來過,不是衛斂的最後一天,而是他自己的最後一天。
他開始有意無意將政務轉給衛斂理,讓衛斂了解秦國的朝政,好讓衛斂日後接手時不那麼辛苦。
他在大臣面前弄出那一場鬧劇,得群臣跪請他收回命,而後讓衛斂好好在眾人面前刷了一把聲與好。他從那時起就在為衛斂鋪路,讓衛斂不至於走得那麼舉步維艱。
衛斂闖書房,主請命那天,姬越早已寫好的欽差詔令下,著更早寫好的禪位詔。
他留在永平,七日不眠不休,竭盡所能為衛斂打點好一切。而後在某一個黃昏騎上烏雲踏雪馬,消失在黑夜。
再見是夕。
而當我來找你的時候,我便已選擇了死路。
義無反顧。
姬越來到江州後,一直按捺不。
淨塵說禍起清平,他必須得去清平縣一趟。不然災難隨時都會降臨在衛斂上,那便為時已晚。
他那段日子借著許多由頭,送了衛斂許多東西,實則每樣都有自己的寓意。
青瓶解藥救人命,是他選擇放手。
兵符令牌贈人權柄,是他出權力。
唯有那最最稚的三生石與姻緣線,是他的一點私心。
他是真的想和衛斂下輩子也還在一起。
做完這一切,姬越在一個衛斂睡去的夜晚,輕輕吻了吻他的額頭。
而後轉,隻踏清平。
衛斂低眸靜靜聽著這一切。
他想起姬越那日擁抱著他,淚水滴在他肩頭,說的那聲對不起。
對不起什麼?
不是對不起傷了他。
更不是放棄了他。
是……是對不起拋下了他。
對不起將他一個人留在世上。
原來從始至終,姬越沒有放棄衛斂。
也不曾辜負百姓。
姬越放棄了他自己。
猜你喜歡
-
完結102 章

為什麼這種A也能有O
養O日記 某位帥哥醫生連做了18小時的手術猝死在手術臺上,醒來發現自己穿到了一個alpha身上。 床邊趴著一只可憐兮兮的omega,見到他醒來,一張小臉簡直是白上加白! 蔣云書:我以前對你很不好? 白糖哆哆嗦嗦,不敢說話。 蔣云書:…… 蔣云書:以后不會了。 蔣云書發現白糖身上布滿淤青,左臂還有骨裂。 蔣云書:我以前打你? 白糖臉色慘白,嗚咽道:沒有…… 蔣云書:…… 蔣云書:以后不會了。 蔣云書發現,白糖在家,不敢上桌吃飯,因為原主不讓。 不能吃肉,因為原主說會有味。 不能睡床,因為原主不喜歡他。 蔣云書還tm發現白糖的被弄出了問題,腺體全是傷。 蔣云書:…… 幾乎不說粗口的蔣云書:草。 后來蔣云書也才知道,每次原主虐待家暴完白糖,都會說同一句話“以后不會了”,但下次只會打得更狠。 蔣云書:…… 蔣云書:畜生!!! 但很慶幸,蔣云書很有耐心,而作為一名醫生,他也可以慢慢把這只漂亮卻殘破的omega養回來。 甚至,他用了一輩子來告訴白糖,什麼叫做以后不會了。 ps: 1、受會明確知道攻換人了。 2、攻前期單向救贖受。 3、不是爽文也不屬于小甜文,心理創傷非常難治愈。 標簽:ABO 年上 溫馨 雙向救贖 HE 換攻 先婚后愛
26.3萬字8 6993 -
完結176 章

穿成重生男主前男友
宋暄和穿進了一本叫做《總裁和他的七個男友》的書裡,變成了總裁的砲灰前男友宋暄和。 書裡的宋暄和:身高一米八,顏值碾壓一眾一線明星,祖上三代經商,妥妥的富三代。 任誰穿到這樣一個人身上都不虧,然而,這是一本重生文。 書裡的宋暄和作為虐了男主八百遍,並且間接害死男主的兇手,面對重生後直接黑化的男主, 最後的結局可想而知——不但名聲掃地,而且還死無全屍。 現在,他成了這個注定要死無全屍的砲灰前男友。- 系統:你有沒有覺得最近男主有點奇怪?像是在暗中計劃什麼。 宋暄和:計劃著怎麼殺我? 總裁:不,計劃怎麼吃你。 躺在床上的腰酸背痛腿抽筋的宋暄和將系統罵了八百遍——說好的男主是總受呢!
60萬字8 11599 -
完結10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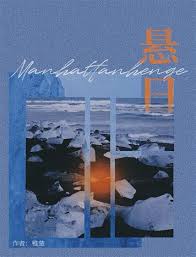
懸日
寧一宵以為這輩子不會再見到蘇洄。直到酒店弄錯房卡,開門進去,撞見戴著眼罩的他獨自躺在床上,喊著另一個人的名字,“這麼快就回來了……”衝動扯下了蘇洄的眼罩,可一對視就後悔。 一別六年,重逢應該再體面一點。 · -“至少在第42街的天橋,一無所有的我們曾擁有懸日,哪怕只有15分20秒。”
47.2萬字8.18 143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