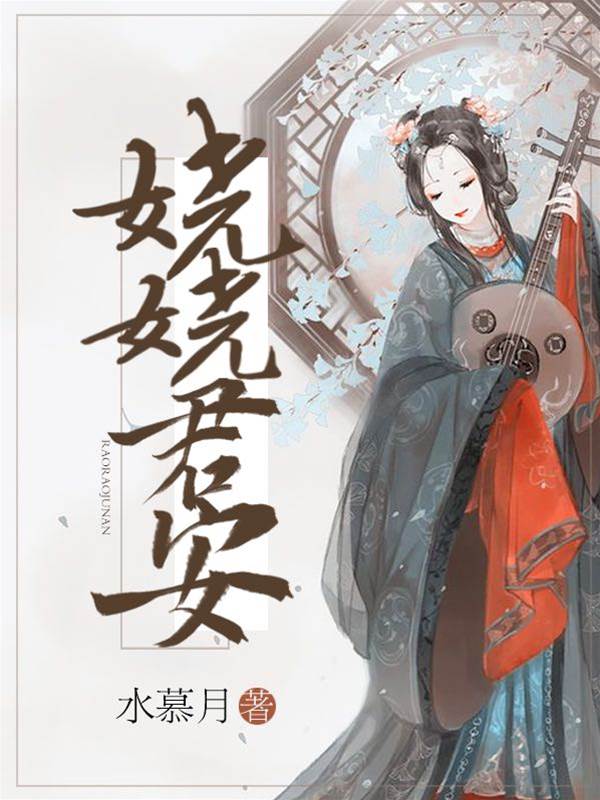《盛寵之下》 ☆、第 54 章
? 梅茹從來沒騎過這麼癲狂的馬。那馬吃痛,縱得極高,又發了狠勁的跑。知道若是現在被顛下來,不死也要半殘。梅茹只能死死攥著韁繩,整個人盡量在馬背上。這馬瘋的要命,馬蹄子撅,徹底驚起林中的大片飛鳥。
黑的一大片,從頭頂飛過,梅茹渾發麻,又覺得森。
這一路早就被顛的難,手上、上力道已經松去許多,整個人只能堪堪掛住這匹瘋馬。偏偏馬速不減,越跑越深,越跑越遠,一條道往前,枝葉茂盛,連都不進多,越發冷。
屋偏逢連夜雨,這林深不知誰放了捕的夾子,那疾馳的馬蹄子直接踩中,那瘋馬痛苦哀嚎一聲,前蹄抬起狠狠往后一仰,梅茹再也抓不住,一下子從馬背上摔了下來。
那地上是石子堆,尖銳還。梅茹重重摔下來,不知磕了哪兒,一瞬間頭暈眼花,整個人腦袋里嗡嗡嗡響,久久彈不得。
這匹瘋馬前蹄被夾住了,后蹄子中了箭,到了這時已差不多疲力盡,痛得原地轉著圈兒的踢。梅茹跌在那兒,無端端挨了幾下,痛得齜牙咧,人卻稍稍清醒了一點。
強撐著要站起來,可是剛剛一,就疼得冒冷汗,尤其是靴子里頭的一只腳痛得不行,只怕不是腫了就是折了,這會兒實在是不了了。梅茹勉強往旁邊挪了一些,勉強離那匹馬遠一點,再抬頭四下觀。
這兒是林深,離大營實在太遠,連個人影都沒有,這回真是天天不應,地地不靈!
穩了穩心神,梅茹知道定會有侍衛來找,地上的馬蹄印子都在,那些人定會尋過來。也不,安安分分在原地待著,只求那該死的太子千萬別跟著過來。
Advertisement
不過歇了小半晌,不遠就有急促的馬蹄聲。梅茹心頭一喜。的馬瘋,竄得肯定快,沒想到還有人追的也這麼快。抬眼過去——
就見一人急急忙忙跳下馬,快步走過來:“三姑娘!”
這林子線頗暗,那人逆著,形象清癯,看不清模樣,但這聲音就足夠讓梅茹渾發冷!
正是最先追過來的太子。
真是怕什麼來什麼,“殿下!”梅茹連忙喝止住他。
太子腳下一頓,旋即還是起擺走過來,問道:“三姑娘,你沒事吧?”枝椏錯間落下幾道,這人停在梅茹面前,擋住了一道。
梅茹彈不得,只能被迫仰頭看他。那人目毫不掩飾的悉數落在上,從頭到腳細細打量著,不放過任何一。落在這人審視又玩味的視線里,梅茹極不自在,上不停的打著冷戰,寒直豎。若不是現在不了,定要跟這個人拼命!
心里惡心又難至極,面上卻還是冷冷道:“臣無妨,不勞殿下費心。”
“別這麼見外啊,三姑娘傷哪兒了?”太子溫言,又俯下。他的目自的腰間往下,最后落在姑娘家纖細的上。又問:“可是傷到腳了?”他說著手就要去捉梅茹的馬靴,梅茹往旁邊一躲,手里起一個又堅又的石頭就要砸下去——
“皇兄!”有人沉聲喚道。
梅茹心頭一跳,循聲過去。
這林子暗,只能看到一個瘦瘦高高的影,渾泛著寒意,立在不遠。
就算看不清面容,梅茹也能認出來這人來。
傅錚!
太子亦認出來,他直起道:“七弟你怎麼會來?”他過去的眼神冷冷的打量著,審視著。理了理袖口,他又意味深長的笑:“這林子深得很,七弟來的倒是快……”
Advertisement
傅錚恭敬道:“原是父皇急著要召見梅姑娘,所以皇弟才著追過來,未想到皇兄已經在了。”
這一回太子一愣,“父皇要召見?所謂何事?”他指著梅茹問,是不是也太巧了?
傅錚回道:“梅姑娘乃是平先生高徒,聰敏伶俐,通曉各邦文字。昨日北遼諸部公主到此,無人作陪,父皇不想太失禮數,便要召見梅姑娘。”頓了頓,他又道:“皇兄,父皇正亦著急找你,說是要與你商議回屠一事。”
太子冷笑:“回屠一事父皇不都給你的麼?怎麼突然要找本宮?”
傅錚面淡淡的,看不出任何異樣,仍是恭敬應對:“皇弟上回不過是在平涼恰好遇上,國之大事,如今自然還是要給皇兄。”
今日雖然不能香,但將傅錚的功勞握在手里,太子也極其滿意。他走過去,吩咐道:“既然是父皇急召,本宮先去了,七弟你將梅姑娘帶回去。”
“是。”傅錚道。
太子騎著馬走了。
傅錚立在那兒,等這人不見了,才松開攥著的手,走上前。
他影沉沉的,踏著遍地寒意,愈發顯得面容鷙。
對著傅錚總比對著太子強,梅茹確實是這麼想的,至這人對是不會有任何.的。梅茹抬頭看他。
傅錚面不善的蹲下來,冷冷道:“明明知道被他看中了,還往上湊!”
聽他兇自己,梅茹極不服氣,口一火蹭蹭蹭往腦袋上冒,不滿嗆道:“還不是因為殿下那位……”
“本王什麼?”傅錚反問。
梅茹一字一頓道:“殿下的青梅竹馬!”
周素卿肯定知道太子的心思,所以自己裝病,將梅茹舉薦給皇后,不就是想撮合和太子?
Advertisement
梅茹冷笑,這人真是如意算盤。
聽出話里的譏誚,傅錚頓了頓,解釋道:“本王心里沒有。”
梅茹還是冷笑:“心里可是只有殿下呢。”又故意問他:“殿下,你是不是識人不清?”
“是。”傅錚承認的很快,又沉聲道,“這事本王絕不會忘。”
如此一來,梅茹倒不好再說什麼。還跌坐在地上,這人還蹲在他旁邊,兩個人這樣杵著也不是個辦法,扶著旁邊的樹就要起來,傅錚問道:“你傷的如何?”
梅茹試著了傷,剛一,的汗就沁出來,咬著,才不哼出來。
傅錚見狀,默了默,手過去要扶。
梅茹避如蛇蝎,避之不及,連忙往后躲,一雙眼只戒備的死死盯著他,直盯得傅錚的手尷尬的了回去,梅茹才冷冷道:“勞煩殿下給我找個點的樹枝。”
這人真是倔的要命。
傅錚沉著臉,去旁邊撿了一個手腕細的樹枝丟給梅茹。梅茹還是盯著他,傅錚別開眼,真是不想再理這人。他自顧去檢查那匹瘋馬的箭傷。
這匹馬的馬掌中箭。那支箭的力道極重,傷口的深而且扎的狠,不是寶慧這樣的小丫頭能有的力道。傅錚眸更冷了一點,仄仄的,會嗜。
傅錚再回頭的時候,就見梅茹一手扶著樹,一手撐著那樹枝站了起來,可明顯有一只腳傷了,都不敢到地上,一張臉痛得全無,還在逞強。
他冷哼一聲,道:“你準備這樣走回去?”
梅茹騎的那匹瘋馬已經徹底廢了,所以,這會兒氣的“嗯”了一聲。
還是倔的要命。
傅錚冷笑:“這條不要了?”
梅茹道:“那殿下把馬讓給我?”
Advertisement
傅錚一言不發,只是將他的馬牽過來,冷冷對梅茹道:“你上的去就歸你!”
梅茹看了他一眼,單腳往前跳了幾步,手夠住馬韁,那只傷腳踩著馬磴子,稍稍一用力正要往上,這一回卻痛得淚花兒都出來了。一雙眼努力睜著眨了又眨,忍了又忍,眼底還是水盈盈一片,眼圈兒紅紅的,莫名讓人憐。
下一瞬,傅錚虛扶著的腰,稍稍一用力,將送到了馬背上。
梅茹怔住。
那被他扶過的腰肢,僵的厲害。
見傅錚也要翻上馬,梅茹回過神,連忙拿樹枝他:“你走開!”
那樹枝手腕細,到人臉上也是蠻疼的。
傅錚黑著臉道:“現在就一匹馬,你還傷著,如何騎?本王如何回去?”
“反正你走開!”梅茹騎在馬上,難得垂眸俯視他,那雙眼冷的可怕。
傅錚攥了攥手,走到前面扯過韁繩,哼道:“本王難得替人牽馬墜蹬。”
走了幾步,他回頭道:“三姑娘,先前扶了你,本王……”
梅茹連忙拿恭維的話堵他:“燕王殿下俠肝義膽,臣謝過殿下照拂還有救命之恩。”
傅錚被一噎,冷冷回過頭。
這一路極長,枝葉層層疊疊的隙中才偶爾下一道,兩個人都安靜。
直到不遠能看到侍衛的影,傅錚方停下來,他著梅茹,叮囑了一句:“你在父皇跟前好好的,他才不會你。”
梅茹心頭一跳。先前還奇怪呢,傅錚突然在太子面前將自己夸得天花墜,什麼聰敏伶俐,又好端端的被陛下召見,要去陪什麼北遼公主……所以,這些都是傅錚安排的麼?
看著傅錚,傅錚垂眸。
梅茹心里頭忽然又升起好幾個疑問,可沒來得及問,大片侍衛已經近到跟前,領頭的居然是傅釗。傅釗嚇道:“梅三姑娘,你沒事吧?”在外人面前,這人終于收斂了些。梅茹應道:“還好,謝殿下關心。”傅釗拂了眼旁邊負手而立的七哥,又沖梅茹悄悄眨眼,故意道:“你二姐姐擔心的不得了,正在林子外頭等著呢!”
梅茹只覺得好笑,附和道:“咱們快去。”
傅錚沉著臉,真想將這人丟回到那林子里頭,先前還不如不去救呢!
一群人往林外去,梅蒨果然候在林子旁邊,還有孟蘊蘭和萍姐兒等人。
見到梅茹平安回來,眾人長舒一口氣,連忙手忙腳迎著先回營帳給太醫治傷,再去拜見陛下。待走得稍遠一點,梅茹才悄悄回頭。
就見二姐姐福了福,不知在對傅錚說著什麼,銀白團花暗紋青領對襟褙子,玉煙籠梅花百水,影窈窕,容傾城,傅錚一襲玄束腰闊袖長袍,蕭蕭肅肅。二人立在一,他像料峭的山,似的水……
該來的,總會來。
梅茹扭回頭,只看著前面。
猜你喜歡
-
完結389 章

農門姐弟不簡單
穿越而來,倒霉透頂,原身爹爹戰亂而死,送書信回家後,身懷六甲的娘親一聽原地發作,立即生產,結果難產大出血而亡。 謝繁星看著一個個餓的瘦骨嶙峋還有嗷嗷待哺的小弟,她擼起袖子就是乾,看著滿山遍野沒人吃的菜,有這些東西吃,還會餓肚子、會瘦成這樣? 本以為她這是要帶著弟妹努力過活,改變生活過上好日子的,結果,弟妹沒一個簡單的。 本文又名《弟妹不簡單》《弟妹養成記》《弟妹都是大佬》《全家都是吃貨》
70.4萬字8.18 36045 -
完結10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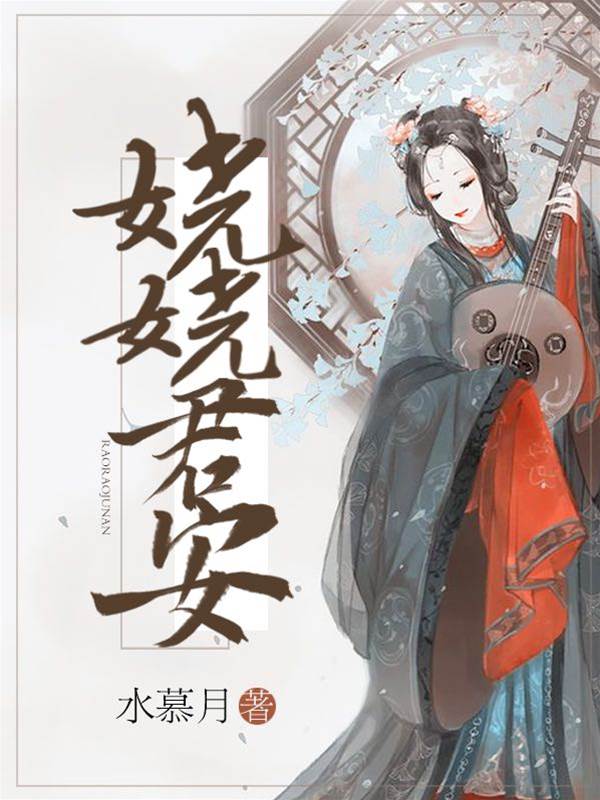
嬈嬈君安
原想著今生再無瓜葛,可那驚馬的剎那芳華間,一切又回到了起點,今生他耍了點小心機,在守護她的道路上,先插了隊,江山要,她也絕不放棄。說好的太子斷袖呢!怎麼動不動就要把自己撲倒?說好的太子殘暴呢!這整天獻溫情的又是誰?誰說東宮的鏡臺不好,那些美男子可賞心悅目了,什麼?東宮還可以在外麵開府,殿下求你了,臣妾可舍不得鏡臺了。
16.6萬字8 14000 -
完結171 章

錯撿瘋犬后
病嬌太子(齊褚)VS聰慧嬌女(許念),堰都新帝齊褚,生得一張美面,卻心狠手辣,陰鷙暴虐,殺兄弒父登上高位。一生無所懼,亦無德所制,瘋得毫無人性。虞王齊玹,他的孿生兄長,皎皎如月,最是溫潤良善之人。只因相貌相似,就被他毀之容貌,折磨致死。為求活命,虞王妃許念被迫委身于他。不過幾年,便香消玉殞。一朝重生,許念仍是國公府嬌女,她不知道齊褚在何處,卻先遇到前世短命夫君虞王齊玹。他流落在外,滿身血污,被人套上鎖鏈,按于泥污之中,奮力掙扎。想到他前世儒雅溫良風貌,若是成君,必能好過泯滅人性,大開殺戒的齊褚。許念把他撿回府中,噓寒問暖,百般照料,他也聽話乖巧,恰到好處地長成了許念希望的樣子。可那雙朗目卻始終透不進光,幽深攝人,教著教著,事情也越發詭異起來,嗜血冰冷的眼神,怎麼那麼像未來暴君齊褚呢?群狼環伺,野狗欺辱時,齊褚遇到了許念,她伸出手,擦干凈他指尖的血污,讓他嘗到了世間的第一份好。他用著齊玹的名頭,精準偽裝成許念最喜歡的樣子。血腥臟晦藏在假皮之下,他愿意一直裝下去。可有一天,真正的齊玹來了,許念嚴詞厲色地趕他走。天光暗了,陰郁的狼張開獠牙。齊褚沉著眸伸出手:“念念,過來!”
26萬字8 7046 -
完結232 章

陛下輕點罰,宮女她說懷了你的崽
為了活命,我爬上龍床。皇上不喜,但念在肌膚之親,勉強保了我一條性命。他每回瞧我,都是冷冷淡淡,嘲弄地斥一聲“蠢死了。”我垂頭不語,謹記自己的身份,從不僭越。堂堂九五至尊,又怎會在意低賤的宮婢呢?
43.7萬字8.18 516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