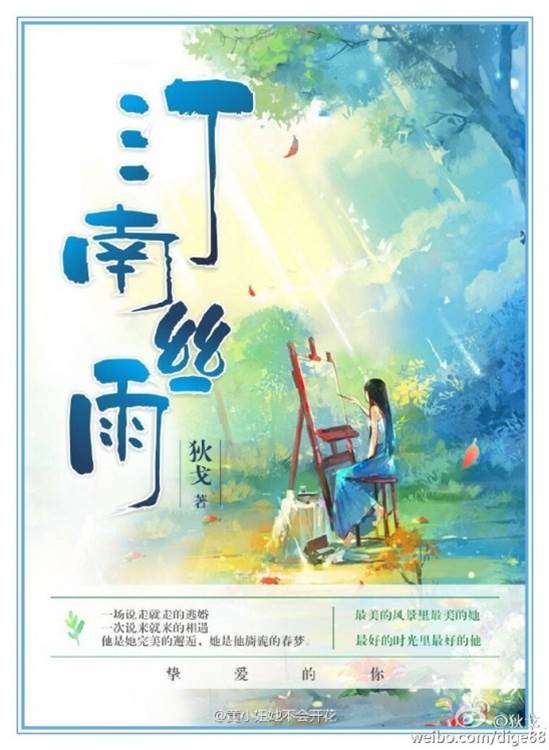《狙擊蝴蝶》 第47章 第四十七次振翅(物歸原處)
年的話好似當頭一棒,岑矜當場懵住,顱滾水般嗡鳴起來,以至于整張臉都變得灼燙。
啞口無言,手按在被子上,一不,難以消化李霧這段話所給帶來的強烈沖擊。
對面也悄無聲息,似乎在耐心等候的狂風驟雨。
須臾,岑矜找回知覺,竭盡全力讓自己聽起來是沉穩的:“還有轉圜的余地嗎,我不用你這麼早還錢。”
李霧說:“合同昨天下午就簽過了。招生辦老師還接我去F大看了一圈。”
岑矜心口一窒:“你問過我了?”
李霧說:“你沒回來,我以為你不想知道。”
岑矜瞳孔放大,難以置信:“你什麼意思,現在是要鉚足了勁跟我作對是嗎?我讓你往東所以你非要往西?你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嗎,用你的前途來綁架我報復我?你以為我會因為這個覺得對不起你?還是說被你打?明明可以去更好的學校為什麼非要留在這?”
李霧好似料定反應那般,聲線毫無起伏:“是我自己的選擇,跟你沒關系。”
岑矜手搭頭,側眸向嚴實的窗簾,覺得自己也像這扇窗一樣,被牢牢堵死了,徹底喪失反駁能力。
最后只能放狠話:“行,我明確告訴你,不管你在哪,我都不想再看到你。”
李霧說:“你放心,我馬上走,之后你別再委屈自己住外面了。”
岑矜一愣:“你要去哪。”
李霧沒回答,只條理清晰道:“來宜中之后吃穿住行的花銷賬目我都擺書房桌上了,你回去可以查下,你給我買的那些東西,知道價格的我都算進去了,還有給我姑姑的那三萬,加起來我不知道十萬夠不夠,如果不夠你告訴我還差多,這個暑假我會想辦法還清。”
Advertisement
他筆筆清算的字句如在岑矜心頭扎刺,人不自覺眼圈泛紅,氣極反笑:“好啊,我知道了。”
岑矜不清楚自己費了多大勁,才讓這六個字聽起來毫無重量。
年沉默片刻,忽而鄭重,好似在做最后道別:“姐姐,謝謝你這一年多來的照顧。”
也是這聲“姐姐”,兩個字,忽而就讓岑矜涌出淚花。
握著手機,只字未言,僵持著原本坐姿,任淚水在臉上肆無忌憚地淌。
一滴水珠墜到純白被面上,洇出小片深水漬。
岑矜才如初醒般,用手指拭去下瀝,而后掛斷通話。
岑矜很久沒有過這種覺了,糟糕,混,無計可施,好像被關進一間滿目狼藉的房間,坐在中央的木椅上,環顧四下,看著那些橫七豎八的件,完全不知道要怎麼下手。多虧李霧為收拾好一切,他有條不紊地查點收納,歸原,干干凈凈,清清楚楚。
不用再管了。
真好。
理應到慶幸與輕松,可岑矜卻覺得心頭豁開了一道微小的口,涼風汩汩直竄,還難以修補。
岑矜滿皮疙瘩地退了房,走出酒店。
今天休假,擔心李霧還在收拾,兩人會上面,岑矜也沒回自己房子,而是去了趟父母那。
剛一進門,就看到了院里假山旁喂魚的母親,后者瞄見兒,也有些驚訝,但馬上綻開笑容:“你怎麼回來了?”
岑矜收起傘,小臉回到日里,頓時白得脹眼,也笑了下:“今天休息,就想回來看看媽媽。”
“我看你只想回來看你老爸吧,”岑母將手里魚食一起撒了,金紅錦鯉登時攢聚哄搶。岑母收眼,又打量起岑矜,“怎麼,心不好?”
Advertisement
岑矜心服口服:“媽,你怎麼跟緒雷達似的。”
岑母乜:“你這笑得沒打采的,還以為我們你回來一樣。”
岑矜雙手環住胳膊,聲:“哪有,就是工作忙,沒休息好。”
說完又把頭往媽媽肩頭靠,岑母豎起一手指,嫌棄地抵了兩下,怎麼都推不開,索由著,笑意還更濃了。
母相攜著走進雕花大門。
岑矜家是間獨棟洋樓,風格為純中式,一個旋轉木梯承上啟下,巨大的云岫山水畫懸于高墻,家私皆是紅木,隨可見的瑩凈,仿若民國時期的家居所。
進了家,冷氣撲面而來,岑矜立馬撇開老媽,四仰八叉癱去沙發,似終于得到紓解般吁了口氣。
岑母招呼家里阿姨給倒杯果,岑矜只說句不用,問有沒有冰的。
阿姨心領神會,去冰箱取來來一盒冰淇淋,到岑矜手里。
岑母則取出茶幾上金線眼鏡盒的老花鏡,戴上,穿針引線,繼續自己的十字繡大業。
氣定神閑地繡,岑矜一勺一勺地挖,相安無事。
眼瞅著見底了,岑矜瞥媽媽一眼:“我爸呢。”
“去公司了,”
岑矜問:“這陣子忙嗎?”
岑母說:“哪天不忙?”
岑矜又問:“中午回來吃嗎?”
岑母說:“說回來的,我一會給他打個電話,要知道你回來了,人在國外都馬上打飛的回家。”
說起這茬,岑母扶了下鏡架,奇怪:“怎麼就你一個人,小霧呢。”
又想起什麼,瞪眼問:“高考分不是出來了?他考怎麼樣啊。”
哪壺不開提哪壺,岑矜手一頓,角下墜,又急速挽起:“很好啊。”
“很好也得有個分啊。”
岑矜沉默,還真不知道多,只能拐彎抹角:“已經簽F大了。”
Advertisement
“啊?這麼快啊?”岑母驚異:“那分得很高吧,昨天才出分就被F大搶了啊。”
岑矜冷哼:“誰知道他。”
岑母瞅:“我怎麼看你一點都不替人家高興啊。”
岑矜回:“我能高興嗎,能去清北的分,非得賴在這。”
岑母不解:“F大不也很好嗎?你自己都那畢業的,怎麼現在還嫌棄起來了。”
“你懂什麼。”
岑母笑了:“我不懂?那會你說想學新傳,你爸琢磨著把你弄人大去,你也不樂意去北京,不想離家遠,怎麼人家不想去你就不讓了?”
岑矜無語兩秒:“他能跟我一樣嗎?”
“有什麼不一樣,”岑母說:“你管人家選什麼,定下來就行,你又不是他親媽,你還要養他一輩子啊?”
岑矜無法反駁。
岑母火眼金睛,悟出當中因由:“哦――因為志愿跟那小孩鬧矛盾了?”
岑矜嘆了一聲:“算吧。”
“沒那當媽的命還沾了當媽的病。”岑母搖頭,接著針,可惜:“難怪小霧不跟你一起回來,就今年過年見了次,我還怪想他的,比你聽話多了。”
岑矜氣不打一來,全糾結在前一句上:“你能不能別這麼刻薄,你怎麼知道那會就是我的問題?”
“到底是不是也得跟旁人試了才知道,”岑母小聲嘀咕,又揚臉:“你也離這麼久了,人家小孩也送出頭了,沒想再找個?你三姨跟我說好幾次了,你這個條件,一婚的都源源不斷有人來問。”
“打住。”岑矜有警告。
“現在公司也沒有看著順眼的?”
岑矜筋弦裂,雙手捂耳:“我對男人已經徹底失了,死心了,余生就想一個人好好過。”
岑母從鏡片后瞧,有趣得很,不由干笑兩聲。
Advertisement
中午,岑父歸家,一見兒就大喜過,噓寒問暖。
飯桌上難免問起李霧高考況,岑矜也只能依靠早上那通電話得知的信息應付了事。
不知為何,父母都很歡喜,唯獨憾李霧人不在場。
父親還頗有儀式地開了瓶香檳,也不管不顧下午是否還要開車工作。
岑矜只得敷衍地與老爸一次又一次杯,為一個并不在場,且基本走出生活的人歡慶。
不產生自我懷疑,怎麼看下來,全世界好像只有一個人悒悒不樂,忿忿不平。
但無論如何,都已經跟這個白眼狼一拍兩散了。
那就祝他前程似錦吧。
岑矜沉默而心不在焉地坐著,自酌一杯。
―
當晚,岑矜回到自己那里。懶得去巡視跟檢查房子里是否還殘留著李霧的氣息,再判斷他搬得是否足夠干凈。
洗完澡,岑矜去了趟書房,翻看起年留下的賬本,沒看幾頁,忽然就被一種微綿的難過裹纏住了,仿佛又回到那個灰的繭蛹里。這種緒與目睹吳復的離婚協議時有幾分相似,不僅是因為要接一個悉的人徹底告離的生命,還有所經歷的每一段真心付出的關系,最后都會淪為毫無溫度的清場,無一例外。
不明白為什麼會這樣。
就因為不夠?不會示弱?不再合乎他們心意?
太可笑了。
岑矜呵一口氣,出桌肚的垃圾桶,摁開蓋子,嘩啦啦把賬本全撥進去,再關上,踢回去,眼不見為凈。
這個夜晚,岑矜再度失眠了。
打開手機,找到宜中微信公眾號最新發布的高考捷報,在里面,終于知曉了李霧的分數,還有他的排名。
擰亮臺燈,就著晦暗的下床,翻出斗柜第二層的手賬本。
這個手賬本是專門拿來記錄李霧轉來宜中后每一次考試績的。
準備將它放在畢業禮當中贈送給他,視作他這個階段的人生徽章,希他可以喜歡。
這是一道單獨為他設立的階梯,在下方目送他矜矜業業,且全心全意地拾階而上,直至攀登頂端。
可惜臺階的主人做了最沒勁的選擇。
岑矜惋嘆地坐回床尾,掀開紙頁,回顧細數起李霧轉來宜中后的每一次績,每一個他與共的歡欣鼓舞的瞬間。
無奈的是,最該記錄的一張還是空白。
岑矜起,從筆筒里摘出一支黑的馬克筆,把他的高考總分謄抄上去,給這一切畫上句號。
―
6月26號,李霧返校取材料。與睿在樓道口分開后,他走向高三(1)班。
教室已經來了不人,同學一見他來,紛紛涌上前來道賀。
李霧抿笑,眼底并無波地應付著。
從講臺后的齊老師手里接過材料,李霧道了聲謝。
齊思賢看他兩眼,似有惋惜:“聽說你要去F大啊?”
李霧頷首。
齊思賢嘖了下,意味深長,卻未置評,只說:“走之前去我辦公室一趟,有你的東西寄我這來了,讓我轉給你,我沒拆。”
李霧詫了下,沒問是什麼,只點了點頭。
李霧去往二樓辦公室,最先見到的是張老師。
年出出分這些天來第一個真心實意的笑容,并與分了自己的每門績,尤其是理綜。
張老師得意得合不攏。聽說了他的最終選擇,張老師也未有抱憾之,依舊如去年那般含笑鼓勵:孩子,大膽走,只要不放棄信念,不放棄學習。
寒暄完,李霧走去齊老師辦公桌,看到了他桌上的快遞盒。
瞥見地址,年眸一頓,直接出一旁筆筒里的工刀,手忙腳地將它拆開。
繞開層層疊疊的泡沫紙,里面裹放著一本頗質的筆記本,棕皮質書。
斂目揭開第一頁,李霧整個人就愣住了。
映眼簾的,是他來宜中后第一次月考的績條,被小心而規整地橫向黏在整頁正中。
上方記錄著時間,下方則寫著一些針對每門績的分析與鼓勵,簡短卻準。
他認得是誰的字跡。
年接著往后翻,氣息變得深而急。
越往后,點評越來越,變俏皮的,不可置信的,難掩興的嘆號,問號,“bravo!!”
直至最后一頁:
黑而的三個數字,他的高考分數,被寫得力紙背――
718。
李霧盯著這三個數字許久,許久……目偏移,及紙張右下角時,他周一僵,心痛裂。
那是兩行小字:
“你的努力
我也還你了”
猜你喜歡
-
完結638 章
買一送一:首席萌寶俏媽咪
盛安然被同父異母的姐姐陷害,和陌生男人過夜,還懷了孕! 她去醫院,卻告知有人下命,不準她流掉。 十月懷胎,盛安然生孩子九死一生,最後卻眼睜睜看著孩子被抱走。 數年後她回國,手裡牽著漂亮的小男孩,冇想到卻遇到了正版。 男人拽著她的手臂,怒道:“你竟然敢偷走我的孩子?” 小男孩一把將男人推開,冷冷道:“不準你碰我媽咪,她是我的!”
116.1萬字8.18 310839 -
完結75 章

一見到你呀
1. 向歌當年追周行衍時,曾絞盡腦汁。 快追到手的時候,她拍屁股走人了。 時隔多年,兩個人久別重逢。 蒼天饒過誰,周行衍把她忘了。 2. 向歌愛吃垃圾食品,周行衍作為一個養生派自然向來是不讓她吃的。 終于某天晚上,兩人因為炸雞外賣發生了一次爭吵。 周行衍長睫斂著,語氣微沉:“你要是想氣死我,你就點。” 向歌聞言面上一喜,毫不猶豫直接就掏出手機來,打開APP迅速下單。 “叮鈴”一聲輕脆聲響回蕩在客廳里,支付完畢。 周行衍:“……” * 囂張骨妖艷賤貨x假正經高嶺之花 本文tag—— #十八線小模特逆襲之路##醫生大大你如此欺騙我感情為哪般##不是不報時候未到##那些年你造過的孽將來都是要還的##我就承認了我爭寵爭不過炸雞好吧# “一見到你呀。” ——我就想托馬斯全旋側身旋轉三周半接720度轉體后空翻劈著叉跟你接個吻。
21萬字8 9512 -
完結43 章

我的愛生生不息
雲知新想這輩子就算沒有白耀楠的愛,有一個酷似他的孩子也好。也不枉自己愛了他二十年。來
4.3萬字8 13074 -
完結60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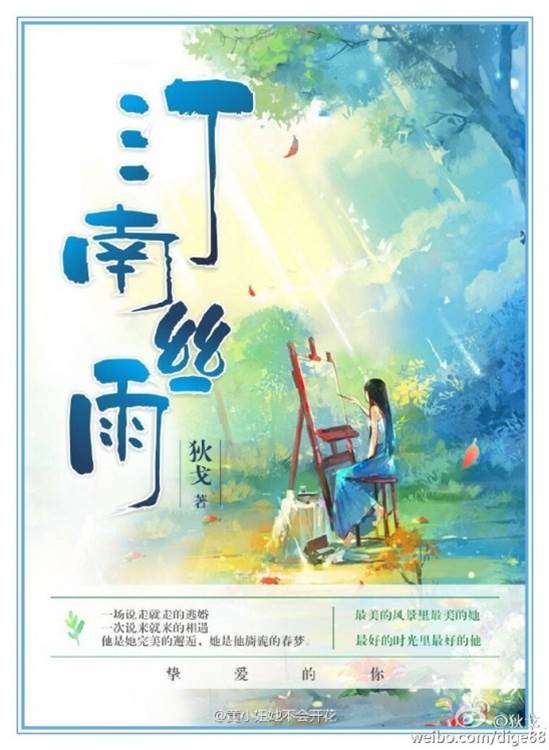
汀南絲雨
通俗文案: 故事從印象派油畫大師安潯偶遇醫學系高才生沈司羽開始。 他們互相成就了彼此的一夜成名。 初識,安潯說,可否請你當我的模特?不過我有個特殊要求…… 婚後,沈醫生拿了套護士服回家,他說,我也有個特殊要求…… 文藝文案: 最美的風景裡最美的她; 最好的時光裡最好的他。 摯愛的你。 閱讀指南: 1.無虐。 2.SC。
16.9萬字8 9132 -
完結222 章

退婚后被殘疾大佬嬌養了
真千金回來之後,楚知意這位假千金就像是蚊子血,處處招人煩。 爲了自己打算,楚知意盯上了某位暴戾大佬。 “請和我結婚。” 楚知意捧上自己所有積蓄到宴驚庭面前,“就算只結婚一年也行。” 原本做好了被拒絕的準備,哪知,宴驚庭竟然同意了。 結婚一年,各取所需。 一個假千金竟然嫁給了宴驚庭! 所有人都等着看楚知意被拋棄的好戲。 哪知…… 三個月過去了,網曝宴驚庭將卡給楚知意,她一天花了幾千萬! 六個月過去了,有人看到楚知意生氣指責宴驚庭。 宴驚庭非但沒有生氣,反而在楚知意麪前伏低做小! 一年過去了,宴驚庭摸着楚知意的肚子,問道,“還離婚嗎?” 楚知意咬緊牙,“離!” 宴驚庭淡笑,“想得美。” *她是我觸不可及高掛的明月。 可我偏要將月亮摘下來。 哪怕不擇手段。 —宴驚庭
60.5萬字8 3342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