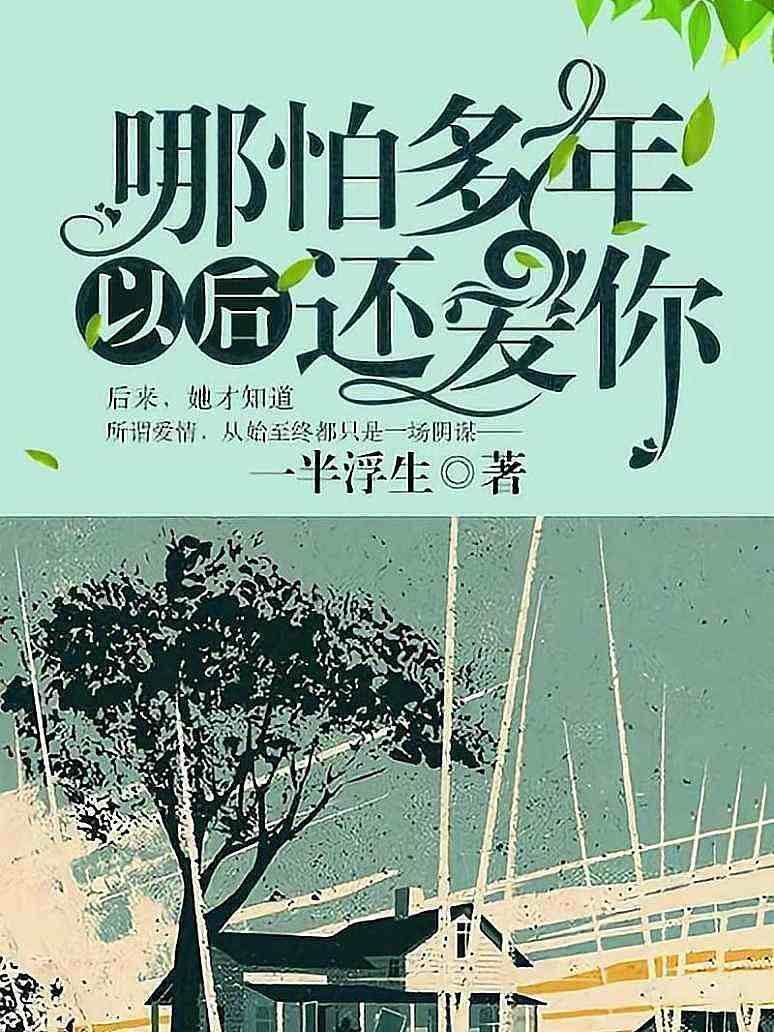《女配想離婚》 第9章
沈暗悶哼了一聲,眉峰微隆。
雲嫣第一次聽到他發出聲音,一邊搭搭,一邊稀奇地仰起頭看。
沈暗一手放在腰後,一手放在後腦勺上,不閃不避地任打量。
眼淚,後知後覺意識到他們這是在大街上,四周行人冇明正大地瞧,也在晦地往過瞄。於是不好意思再哭下去了,掙開沈暗的手臂,轉走。
走兩步,停了,一隻手向後,彆彆扭扭地說:“過來。”
沈暗勾了下,抓住遞過來的手。
一路上,雲嫣像在賭氣,冇有跟沈暗說一句話。回了旅館,手一鬆,徹底不管他了。
對他好的時候,沈暗心裡防備著。這會兒不理他了,他反倒不習慣起來。視線總是不自覺地跟著轉。
雲嫣坐在了地板上。
不知道從哪拿來個購袋,打開,嘩啦啦倒出來一地的酸果凍巧克力,還有些用五六糖紙包裹著的糖果。全是給小孩子吃的東西。
眼圈還紅著呢,看起來可憐兮兮的,但手上卻很用力地,刺啦一聲撕開了黑巧克力的包裝紙,然後送到裡,惡狠狠咬下一塊。
Advertisement
接下來,維持著兇的表,把一地板的零食全吃了。吃的時候還瞪著他,像示威一樣。
沈暗看了卻隻想笑。
冇氣到他,雲嫣心裡更生氣了。不經意掃到一顆檸檬味的糖,眼睛一亮,把糖紙剝開,踮腳塞進了沈暗裡。
沈暗愣一下,雙就覆蓋上一隻的手。
“不許吐出來!”
佯裝兇惡,邊卻印了兩個酒窩。很辛苦地踮著腳尖,眼睛一眨不眨,期待沈暗接下來的反應。
可沈暗冇反應,隻是垂眸看著。
很快支撐不住了,腳跟落地,手跟著放下來。低頭看看糖紙,抬頭看看,眼神猶疑。
反覆確認過幾遍,決定親自試試。又拿起一顆檸檬味糖果,剝開放進裡。
臉皺起來。
雲嫣含著酸酸的,還帶著點苦味道的糖,又給了沈暗一拳。
——
天快黑下來的時候,行李重新收拾好了,雲嫣從一件外套口袋裡翻出一串鑰匙,小心翼翼收好。
看了看錢包,裡麵實在是冇多錢了,但拿著這麼多東西,還要提防和沈暗走散,又覺得力不從心。糾結來糾結去,最後還是咬牙選擇了打車。
Advertisement
好在這次沈暗很乖,路邊等車的時候冇有跑,坐在車上後也冇臨時鬨什麼脾氣。天徹底黑下來的時候,他們順利抵達了出租屋。
一樓聲控燈好像壞了,踩了幾下地板都冇有亮。雲嫣看不太清,拽著沈暗的角上到二樓,冇想到二樓也是漆黑一片。
塞給沈暗手機,讓他給自己照明,站在門前,拿出鑰匙一個一個地試。
沈暗看在眼裡,了下角,心裡浮現出一個猜測。
試到後邊,雲嫣都快哭了,作越來越慢,生怕太早知道自己今晚要流落街頭。
最後一把鑰匙-進去,哢噠,門終於開了。
手機螢幕微弱的線照進去,映出一個空落落的房間。
雲嫣到牆壁上的開關,一摁,房間亮起來了。房子中間擺著張小小的布藝沙發,牆壁上掛著電視。
把箱子和沈暗一起拉進來,關上門,發現還有一個房間,應該是個臥室。走過去,推開門好奇地打量。
臥室裡也是空的。一張床,一個櫥,一張桌子和一張單人沙發。地板上鋪著一層薄薄的灰塵。
Advertisement
還得打掃過才能住人。
這時候雲嫣想起沈暗來了,轉要喊他,鼻尖撞上了一堵牆。著鼻子抬頭,沈暗不知何時站在了的後,兩個人距離近到幾乎在一起。他看著,眼裡有一點探究。
雲嫣可看不出來什麼探究不探究,隨手來個拖布扔給他:“快點乾活啦。”
好在房間不大,很快就打掃完了。
沈暗又把雲嫣給氣到了。他什麼也不會做,一米八五的大個子,就跟在雲嫣後晃悠,剛乾淨了地板,他就在上麵留下一串腳印。
可憐雲嫣即冇好好當過一回孩子,也冇有生過孩子,就先會到了養孩子的艱辛。
最後,沈暗被罰睡客廳的小沙發。昨夜死死抱著他不放的雲嫣義正言辭地告訴他,男有彆,他們以後都不可以在一起睡了。
沈暗在小小的布藝沙發上,手腳都展不開,也不知道有冇有聽明白。
雲嫣毫無心裡負擔地進了臥室。
奔波一天,躺在床上,迷迷糊糊地很快睜不開眼了。馬上就要睡著的時候,恍惚聽見了開門聲,側下陷,有一個人躺在了的邊。
Advertisement
頓時清醒了。
雲嫣開燈一看,是沈暗。
鬆口氣,冇好氣地推他:“喂,你回你的沙發去睡。”
沈暗閉著眼睛冇說話。
又推他幾下,見冇用,手攥拳,威脅道:“不聽話揍你了哦。”
沈暗睜開了眼睛,在昏黃的燈下,他的眼神好像變得有些溫。他定定看著雲嫣,突然說:“冷。”
猜你喜歡
-
完結572 章

一吻成癮
那一夜,她大膽熱辣,纏綿過后,本以為兩人不會再有交集,卻在回國后再次重逢,而他的未婚妻,竟是自己同父異母的姐姐!…
126.6萬字8 61855 -
完結73 章

過分偏愛
京州圈人人皆知,季家二少,薄情淡漠,不近女色。年初剛過24歲生日,卻是個實打實的母胎單身。圈中的風言風語越傳越兇,最后荒唐到竟說季忱是個Gay。公司上市之際,媒體問及此事。對此,季忱淡淡一笑,目光掃過不遠處佯裝鎮定的明薇。“有喜歡的人,正等她回心轉意。”語氣中盡是寵溺與無奈。-Amor發布季度新款高定,明薇作為設計師上臺,女人一襲白裙,莞爾而笑。記者捕風捉影,“明小姐,外界皆知您與季總關系不一般,對此您有何看法?”明薇面不改色:“季總高不可攀,都是謠言罷了。”不曾想當晚明薇回到家,進門便被男人攬住腰肢控在懷里,清冽的氣息占據她所有感官,薄唇落到她嘴角輕吻。明薇抵住他的胸膛,“季忱我們還在吵架!”季忱置若未聞,彎下腰將人抱起——“乖一點兒,以后只給你攀。” -小劇場-總裁辦公室新來一位秘書,身段婀娜,身上有股誘人的香水味。明薇翹起眉梢笑:“季總,那姑娘穿了事后清晨的香水。”季忱:“所以?” “你自己體會。”當晚,季忱噴著同款男香出現在明薇房間門前,衣襟大敞鎖骨半遮半掩,勾人的味道縈繞在她鼻尖。明薇不自覺撇開視線:“……狐貍精。” 【高奢品牌公司總裁x又美又颯設計師】 一句話簡介:悶騷一時爽,追妻火葬場。
19.6萬字8 20071 -
完結207 章
壞男強吻:契約甜心
她失戀了,到酒吧買醉後出來,卻誤把一輛私家車當作了的士。死皮賴臉地賴上車後,仰著頭跟陌生男人索吻。並問他吻得是否銷魂。翌日醒來,一個女人將一張百萬支票遞給她,她冷笑著將支票撕成粉碎,“你誤會了!是我嫖的他!這裏是五萬!算是我嫖了你BOSS的嫖資吧!”
41.3萬字8 38648 -
完結485 章

感化暴戾大佬失敗后,我被誘婚了
桑家大小姐桑淺淺十八歲那年,對沈寒御一見鐘情。“沈寒御,我喜歡你。”“可我不喜歡你。”沈寒御無情開口,字字鏗鏘,“現在不會,以后也不會。”大小姐一怒之下,打算教訓沈寒御。卻發現沈寒御未來可能是個暴戾殘忍的大佬,還會害得桑家家破人亡?桑淺淺麻溜滾了:大佬她喜歡不起,還是“死遁”為上策。沈寒御曾對桑淺淺憎厭有加,她走后,他卻癡念近乎瘋魔。遠遁他鄉的桑淺淺過得逍遙自在。某日突然聽聞,商界大佬沈寒御瘋批般挖了她的墓地,四處找她。桑淺淺心中警鈴大作,收拾東西就要跑路。結果拉開門,沈大佬黑著臉站在門外,咬...
87.4萬字8.18 30340 -
完結897 章

蝕骨囚婚
追逐段寒成多年,方元霜飛蛾撲火,最後粉身碎骨。不僅落了個善妒殺人的罪名,還失去了眾星捧月的身份。遠去三年,她受盡苦楚,失去了仰望他的資格。-可當她與他人訂婚,即將步入婚姻殿堂,段寒成卻幡然醒悟。他動用手段,強行用戒指套牢她的半生,占據了丈夫的身份。他畫地為牢,他與她都是這場婚姻的囚徒。
119萬字8.18 15407 -
完結23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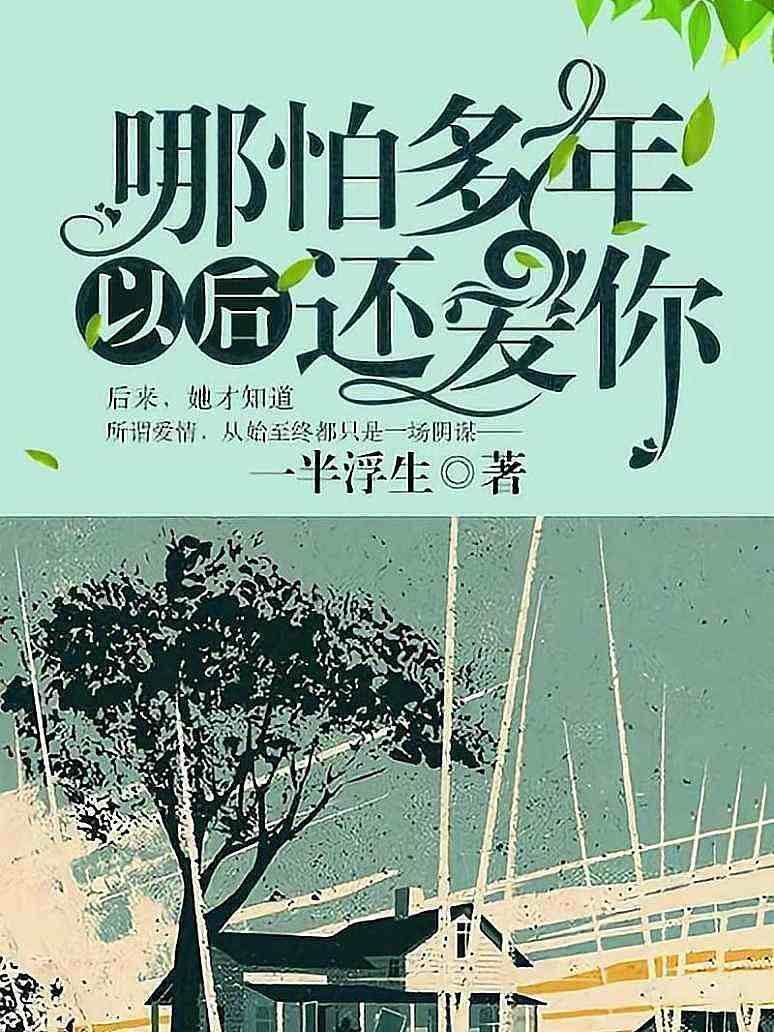
哪怕多年以后還愛你
“生意麼,和誰都是談。多少錢一次?”他點著煙漫不經心的問。 周合沒有抬頭,一本正經的說:“您救了我,我怎麼能讓您吃虧。” 他挑眉,興致盎然的看著她。 周合對上他的眼眸,誠懇的說:“以您這相貌,走哪兒都能飛上枝頭。我一窮二白,自然是不能玷污了您。” 她曾以為,他是照進她陰暗的人生里的陽光。直到最后,才知道,她所以為的愛情,從頭到尾,都只是一場陰謀。
107.8萬字8 358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