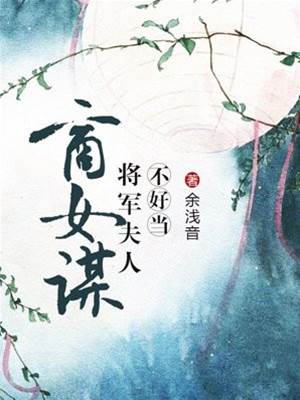《洗鉛華》 第 36 章節
“被捕的刺客著佩劍全都是統一的嗎?”我皺眉開口。
仲溪午的腳步似乎一頓,才開口問:“你怎會有如此疑問?”
我腳步未停,開口:“只是那日見宴席上的黑人,配合很是不當。”
半晌后仲溪午輕笑了一聲,聲音才響了起來:“淺淺,你向來都是遇事變不驚,讓我都止不住佩服。”
這句話太過曖昧,我也不再追問下去,只是開口:“皇上不愿泄不說便是,何必拿這種話……來搪塞我。”
然而右手卻被仲溪午握住,我對上他的眼眸,用力掙了掙,他卻越握越。
“就算此無人你也不能這樣逾矩,你把我當什麼……”我語氣上也帶了幾分惱怒。
“你不是向來都知道嗎?還拿規矩來我。”仲溪午并沒有因我的說辭松手。
左手握圣旨越來越,半晌后我才開口:“皇上這是什麼時候變了目標?”
“沒有變。”
“嗯?”我詫異的看向仲溪午。
只見他目灼灼:“一直都是你。”
聽到這句話我下意識用力回了自己的手,這次仲溪午沒有再用力,我順利的回了手。迎著仲他毫不搖的目,只覺得頭發,我張了張,穩了下緒才說:“那牧遙……”
仲溪午眉頭皺了皺說:“為何你總是會把牧遙扯到我上?”
我低頭看著地上晃的影才開口:“是你說的你看眼神和我不同。”
“當然不同。”仲溪午的聲音低低的響起,“因為喜歡而眼神不同的人一直是你,已經親還惦記的人是你,量尺寸做……服想給的人也是你。從一開始,都只有你。”
手里的圣旨差點拿不穩,只覺得自己心跳聲太響了,響到我耳里全是“砰砰”的回響:“我…我可是……”
Advertisement
晉王妃三個字沒說出來,我就看到了手里的圣旨,聲音戛然而止。
仲溪午似是看了我心思,開口說道:“怕你之前會因為份有負擔,所以現在才來告訴你,不過聰穎如你,又怎麼看不出我的心思呢?還拿牧遙做借口在大殿上婉拒我。”
“既然皇上當時已經聽出了我意思,今日又何必前來……”我覺手里這個圣旨要被我□□爛了,好像聽說過圣旨是賜之,損毀會重罰的。
“因為我放不下。”仲溪午無視我的抵開口,“所以我就還想再來問你一次,親口問你可愿跟我?”
心口有些酸疼,我開口:“皇上是在說笑嗎?你我之間的份,便是到了現在也是不合適的。”
要我做什麼?跟他進宮做妃子嗎?
“或許現在這個時候,這個地點都不適合說這些,可是我還是忍不住了,我只問你愿不愿。若是你心里有半分我,這邊一切都給我,我會讓你明正大的站在我邊。”
仲溪午開口,眼里滿是和的赤誠,完全沒有我最初見他時的試探和戒備。
他右手執燈,向我出左手,白皙又骨節分明的手掌在月下,照的我眼睛生疼:“淺淺,一切都有我,只要你愿意,我的手就在這里。”
仲溪午的話,還有話里的我都清晰明了,可是我能握住這只手嗎?
若我是十幾歲的小姑娘,或者是真正的古代人,我會毫不遲疑的握住,可是兩者我都不是啊。
我現在已經不是做事只憑的年紀了,我和仲溪午之間隔了太多。先不說他和我價值觀相悖的三宮六院,就是我們現在的份也是會有千重阻礙,我終究是嫁過仲夜闌,現在的我能以什麼份宮呢?
Advertisement
仲溪午是喜歡我,可是我不確定長年堆積的后宮生活,能讓他的剩下多。即使是現代社會的一夫一妻制,也是會有很多離婚的,我不敢想在面對后宮日益更新的人,他又能喜歡我多久呢?
迎著仲溪午如同潭水般寧靜溫和的眼眸,我的手越握越,就要將自己手心刺破。
若是被時間消磨殆盡,我又該如何自?我的心思、我愿不愿意,在這重重困難下,都顯得已經沒那麼重要了。我想走向他拉住他,可是這起步太難太難了。
空曠的山崗突然響起一陣倉促的腳步聲,我回頭看到翠竹帶著淚沖我跑過來跪下,心里一跳,就聽說:“小姐……小姐,求你去看看華戎舟吧……他…他……好多……”
聽說出一堆七八糟的話,我努力穩下心神,扶起開口:“好好說話,華戎舟怎麼了?”
然而翠竹支支吾吾半天,哭著也說不完整,我心里越發煩躁,拔就走。
走了幾步才想起來,回頭看到仲溪午還在原地執著燈籠,手已經收了回去,只是看著我,目未曾變過。
深吸了一口氣我才開口:“今日多謝皇上前來送旨意,其他事我只當是沒有聽過,就……不必再提了。”
說完我行了一禮轉就走,不敢再回頭看一眼。
匆忙趕回華府,看到一名大夫從我院子里出來,我拉住了他問道:“大夫,華戎舟如何了?”
那個長著絡腮胡的大夫對我拱了拱手,回道:“回小姐,屋里之人并無大礙,只是傷口二次崩裂了不苦頭,現下服了藥,已經睡了過去。”
傷口二次崩裂?
我暈暈乎乎的看著千芷去送大夫,自己走進了華戎舟的房間。
Advertisement
只見房間甚至簡單,除了一套桌椅和餐再無其他。
走到他床前,看到他躺在床上,雙目閉眉頭鎖,蒼白的面就可以得知他就算是昏睡了去也很難。
我抬手掀起了他的被褥,看到他只穿著子,出□□的上半上,腰間已經包扎好卻滲出點點跡的紗布十分顯眼。
“這是怎麼回事?”我皺眉問向跟過來的翠竹。
那丫頭終于停了哭泣,才開口:“小姐不知道嗎?”
我皺眉,一旁的銀杏見氣氛不對趕開口:“回小姐,華侍衛是那日落崖時的傷,昨日又接了……晉王爺一掌,才使得傷口再次崩裂。”
“落崖?”我眼睛一,心里突然浮上了一個想法。
接下來銀杏就開口證實了我的猜想:“那日華侍衛跟隨小姐落山谷,直到第二日早上才帶著小姐回來,他腰間有一道傷口,大概是掉落時不小心被樹枝劃傷的,他也沒有多說。”
跟隨我跳下山頂?
腦子里響起那日遇見他也是一漉漉,還有他背我時聞到的腥味,我當時還好奇他是怎麼那麼快找到我的,后來卻不曾問過。
只因他穿黑,那天又是晚上,我竟不曾察覺,還任由他一路背著我回來。
這幾日華深之事如同是一個晴天霹靂,我渾渾噩噩也沒再問過他,原來那日他竟是跟著我跳了下去。我是如何回的華府,現在也可想而知,一個傷重之人還拖著我,這幾日也是堅持帶傷跟在我左右。
他說過我向來喜歡忽略他,我還不服氣,現在看來我還真是沒心沒肺。
華戎舟雙目閉,他剛服了藥一時半會也不會醒。我放下了手里的被子,然后依著床沿坐了下來,銀杏見此就拉著翠竹出去了。
Advertisement
這是我第一次這麼認真看這個孩子,一直以來我都把華戎舟還有千芷他們當做是弟弟妹妹一樣的存在,所以從來都是把他們護在后,自己一個人去打拼謀劃。
可是這次卻發現原來會有人隨我一起冒險,我自己跳下來山頂心里有七分把握,那華戎舟隨我一起跳下去時,他心里有幾分把握呢?
忍不住嘆了口氣,這個年在睡中還是眉目皺,往日如花嫣紅的現在是青白的。
昨日他咬牙接了仲夜闌那一掌,才導致傷口二次撕裂,定是痛極了吧,我事后卻還怪他擅作主張。
靜靜坐在床畔,耳邊是華戎舟淺淺的呼吸聲。
這幾日發生的事如同一幕幕在腦海里閃過,我不能再任自己沉湎下去了。因為現在的我,不再只是一個人了,我的一時懦弱逃避,只會給邊之人帶來不幸苦難。
許久之后我才起準備離開,等他醒來再來問他吧,然而剛站起來服卻被扯住。
我回頭看華戎舟還是昏睡模樣,而我的腰帶卻被他在外面的手掌握住,應該是剛才我附給他蓋被子時,腰帶垂到了他手上,才被他下意識的抓住。
我拉了拉腰帶,見他沒有半點松,便又坐了回去,嘗試掰開他的手掌,卻也是沒有作用。他的拳頭越握越,手指甲都快要陷到了里面,像是正在被別人搶走東西。
我只得作罷,放棄了走的念頭,總不能把腰帶解了衫不整的出去吧。
又給他掖了掖被角,就這樣一坐到了天亮。
猜你喜歡
-
完結434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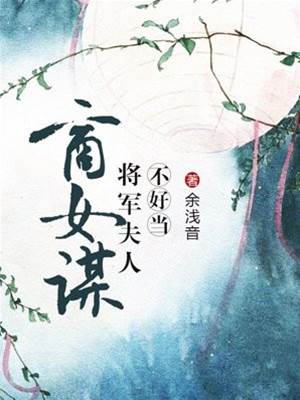
商女謀:將軍夫人不好當
一朝穿越,成為當朝皇商之女,好在爹娘不錯,只是那姨娘庶妹著實討厭,真當本姑娘軟柿子好拿捏?誰知突然皇上賜婚,還白撿了一個將軍夫君。本姑娘就想安安分分過日子不行嗎?高門內院都給我干凈點兒,別使些入不得眼的手段大家都挺累的。本想安穩度日,奈何世…
81.5萬字8 36634 -
完結419 章

鬼醫嫡女寵上天
前世遭遇渣男設計,嫡女沈煙芷竟失身于乞丐有孕,父兄接連戰死,滿門被屠! 重生一世,她腳踩渣男,拳打賤女,帶領全家走上反派權臣之路! 彪悍人生一路開掛,順她者昌,逆她者亡! 鬼醫仙門祖師爺的師父,是她! 最強情報六處的建立者,還是她! 大半個江湖上流傳的大佬們,都是她的門生! 軍師大哥勸她不要跟著反派學,她表示:功高蓋主會被虐殺,但反派權臣能上天。 財迷二哥勸她不要嫁給腹黑男,她表示:放眼皇族,除了他,還有誰配得上我? 護短三哥勸她不要與虎謀皮護,她表示:沒有這只霸王虎,我沈家早就滿門滅絕了。 某腹黑狠辣的攝政王:看來本王要想被沈家接受,全靠媳婦日常替本王洗白了。
83.1萬字8 25926 -
完結827 章

報告將軍夫人今天有點怪
秦蘇蘇死了。 死之前,她看到自己最厭惡的夫君,至死都護著她。 自己最信任的男人,輕蔑的說她:「殘花敗柳。 她一生苦等,不曾讓將軍碰自己一絲一毫,不曾想,卻成了翊王又蠢又好用的一枚棋子。 睜眼醒來,一朝回到剛嫁入將軍府初期,一切都還來得及! 原本是要偷兵書的秦蘇蘇,卻扭頭缺廚房給將軍煮了一碗麵,「好吃嗎? “ 看男人拘謹的點頭,秦蘇蘇抿唇:將軍真帥。 重活一世,秦蘇蘇不求別的,只求將軍順順利利平平安安。 她幫將軍掃小人,幫將軍除奸臣,給將軍煮飯。 上輩子將軍寵她,這輩子換自己寵將軍!
148.1萬字8 60964 -
完結160 章

奪皇權!持天令!傾城嫡女殺瘋了
【虐渣爽文 宅鬥宮鬥 美強慘男主 團寵女主】權勢滔天的國公府嫡女,十年相守助心上人登上帝位,卻在她幫他穩定後宮,坐穩皇位後,以私通罪名打入冷宮。腹中胎兒被生生剖出,與她一道被烈火焚燒而亡。重來一世,她還是國公府萬千寵愛於一身的二小姐,前世欺她、辱她、害她、騙她、殺他之人,全都顫抖起來吧!這昏庸的皇朝,她要攪個天翻地覆。複仇前,前朝太子遺孤裴或:你恨慕容翟,我恨慕容戰,你殺兒子,我殺老子。複仇後,裴或將沈飛鸞抵在牆邊:乖,別髒了你的手,看我打狗。
28.7萬字8 2352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