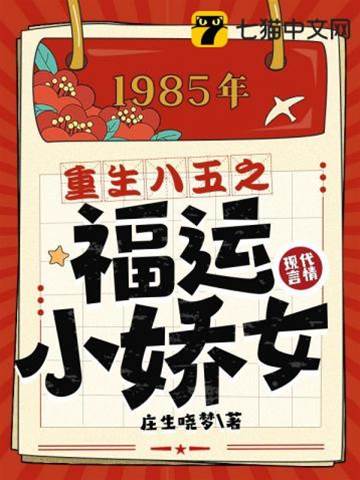《我就喜歡他那樣的》 第39章
霍慈心里往下塌,腦子不糊涂,立刻問:“你們在哪兒呢?”
“我們在軍總,老大剛洗完胃,我陪著在病房里休息呢,”莫星辰其實是在外面打的電話,借口出來倒水,這才有空。
平時就是個大咧咧的格,一遇到這事兒是真的慌神了。腦子里全都是懵的,只想給霍慈打電話。們兩在一塊,霍慈才是主心骨。可是電話都打了十個,那頭都沒人接。這不好意思接通了,眼淚就沒出息的掉下來了。
霍慈一愣,合著北京就剩下軍總這一家醫院了。
不過也顧不得想了,沉聲說:“你先照顧,我馬上就過來。”
莫星辰原本還抱著不在北京的最壞打算,可一聽說要過來,心里頭是真松了一口氣。趕掛了電話,就進去照顧邵宜了。
怎麼也沒想到,這馬上居然是十分鐘。
而且霍慈還是被椅推過來的。
這會邵宜已經醒了,正在打點滴呢。和莫星辰兩人瞧著霍慈一病號服,還是坐著椅來的,神都不對了。
莫星辰又要哭了,帶著哭腔問:“你丫又怎麼了啊?”
原本還指著霍慈給們撐腰呢,可是居然這樣了。
霍慈冷著臉,眉頭蹙:“闌尾炎,剛開完刀。”
白羽在后聽著胡說八道,臉都要氣歪了。可是瞧著躺在床上的姑娘,又實在說不了別的話,干脆就閉了。
對面那兩人倒是都松了一口氣。
病床上的邵宜嘆了一口氣說:“我還讓星辰別給你打電話,就是大驚小怪。”
“都到醫院洗胃了,還大驚小怪?”霍慈挑眉,打眼瞧著,神是真憔悴。
邵宜子平和,但也不是那種書呆子。大學的時候,沒照顧們三個,后來沒了一個,就照顧們兩個。霍慈因為工作累倒,在校醫院掛了一個星期的點滴,在寢室里用爐子給煲粥,誰知買地假冒偽劣的電爐子,把整棟樓的電都被燒壞了。
Advertisement
后來全學校通報批評,連獎學金都不讓評選了。
霍慈為人冷漠,朋友更。大學的這兩個室友,就是最上心的朋友。
邵宜有點兒尷尬,解釋:“你別聽星辰瞎說,我真不是自殺,就是吃了兩顆安眠藥,沒睡著之后,起來喝了點兒酒。我是真忘了吃安眠藥的事兒。”
一旁的莫星辰就差沒跳起來,看著霍慈說:“霍慈你信這話嗎?別說一個醫生了,就是一個沒醫學常識的人,都知道酒和安眠藥不能一塊服用。”
莫星辰眼珠子都紅了,是真嚇著了。
要不是半夜起來上廁所,看見趴在外頭,只怕第二天早上,看見的真是一尸了。
邵宜還是堅決為自己辯解,真是躺在床上實在睡不著起來的。結果看見冰箱的酒,就忘了之前吃過安眠藥的事。
霍慈靠在椅背上,不聲不響地瞧著們兩人說,冷不丁才開口:“那誰能告訴,究竟發生什麼事兒了。”
這話一問,兩個都懨了。
邵宜垂著眼,手背上還打著點滴,安靜躺著。
莫星辰眼睛轉了轉,想說吧,可是又小心地覷了幾眼,床上躺著的邵宜。
“白羽,你先出去等我吧,”霍慈淡淡地說。
白羽也瞧出來,這是有事兒。他應了一聲,就出去了,還順手把門給關上了。也是幸虧隔壁床的人現在不在,估著出去放風或者檢查了。
莫星辰等了半天,見邵宜都不說話。心一橫,干脆說:“還是我來說吧,陳忻劈了。”
陳忻是邵宜男朋友,從大學開始就是同學,談了六七年,快要結婚了。
霍慈來之前,心底已經猜到了大概,可此時聽到,還是冷不丁的腦子一炸。朝著窗邊看了一眼,冷冷地吐了一句:“這傻。”
Advertisement
可不就是傻,一直覺得劈是這世上最沒種,也最吃不力不討好的事。可偏偏還是有人樂此不疲,前赴后繼著。
莫星辰總算是找著知音了,自從知道這事兒之后,就憋著一口氣。當著邵宜的面兒,還不能罵地太狠。
“你知道最過分的是什麼嗎?他居然把咱們班里重新拉了個小群,就沒拉你和我,要不是有其他同學私底下問我,我都不知道這傻要結婚了。”
砰,莫星辰說完,就知道,自己引發了一顆炸彈。
藏不住事兒,原本好不容易憋著沒告訴邵宜,可是看見霍慈在這兒,就跟看見主心骨似得,什麼話都跟倒了出來。
邵宜抬起頭,這次臉上的表不再平靜了,滿臉的不敢相信,滿目瘡痍。看著人多心疼,就有多心疼。
問:“他要結婚了?”
陳忻是上周提的分手,其實早開始,邵宜就察覺到他便冷淡了。但總想著,是工作太忙了,畢竟醫院的工作,每天看那麼多病人,連著幾臺手,還要值班,累是正常的。一直到他提分手,還不敢相信。
他們圣誕的時候,還商量著結婚的事。
莫星辰垂著頭,低聲說:“是咱們班里的劉婷說的,你也知道就是個大。”
“你知道他在哪兒結婚嗎?”霍慈淡淡地問。
臉上沒什麼表,瞧不出來生氣的模樣,就是淡淡的。跟蒙著一層假面一樣,眉梢眼角都是淡的。莫星辰跟認識這麼多年,能不了解,知道這模樣才是最可怕的。
莫星辰小心地問:“霍慈,你想怎麼辦?”
“怎麼辦?”霍慈抬頭看著們兩個,手撥弄耳邊的長發,輕聲說:“好歹也認識這麼多年了,他結婚,我們不去,不是太不盡人意了。”
Advertisement
霍慈瞧著窗外,北京的冬天真冷。
輕聲說:“再過幾天,就要過年了。”
提到過年,莫星辰看著邊這兩人,一個洗胃,一個隔闌尾。委屈地說:“這年末到底是怎麼了,怎麼會這麼多事。”
霍慈懶得搭理的廢話,直直地看著邵宜,問:“邵宜,最重要的是你的想法。”
邵宜沉默地看著。
霍慈說:“現在或許你會很生氣,心底恨他的劈。可你不問清楚,以后慢慢的,你就會想,是不是我哪里做的不夠好,讓他這麼對我。”
久病醫,霍慈曾經因為心理問題,去看過心理醫生。有很多劈的案例,最后被拋棄的方,反而了自怨自艾的那個。們萎靡不振,對失去信任,最后對自己失去信心。
邵宜不是剛強的人,但絕不懦弱,霍慈只希,不要走上這樣的路。
莫星辰還算有點兒手段,搞到了陳忻結婚的地點。報了個酒店的名字,五星級的,就是要預定,也得提前半年。要麼就是這家人有關系隊了,要麼就是半年前就訂了這地方。
莫星辰冷哼了一聲:“倒是人模狗樣的,訂這麼好的地方。”
“陳忻家是縣里的,條件一般,”邵宜輕聲說。
房間里登時沒聲音了,現在連劈的理由都知道了。這種五星級酒店,隨便辦一場婚禮都要幾十萬。要是陳忻家真有這麼多錢,他也不至于之前拖著不結婚了。
這是攀上富貴了。
再說下去也沒意思了,邵宜說困了,見霍慈這模樣,也讓趕回去休息。
莫星辰送到出門,也不敢走遠,就站在門口和霍慈低聲說:“我都問了,陳忻和小三好像是看病時候認識的。”
Advertisement
霍慈一挑眉,冷不丁笑了,還真是小瞧了莫星辰,這都打聽了。
莫星辰生氣地說:“渣男現在滿世界跟別人說,他和邵宜半年前就分手了。只是沒告訴別人而已。他說對小三是一見鐘,覺得遇見對的人了,兩個月就定下來了。我靠,渣男臉皮真是比長城還厚,我認識他這麼多年,都沒瞧出來,真是白瞎了眼。”
這些話,都是莫星辰從同學那里東拼西湊來的。要是陳忻這會兒在跟前,真是恨不得幾個里就扇過去。
霍慈眼神冰冷,上掛著譏諷的笑。
臨走的時候,說:“放心,他蹦達不了幾天。”
**
所謂得來全不費工夫,大概就是指著現在這種況吧。
霍慈睡了一覺,柳如晗就到了。軍總這邊人多,怕有沈方棠的老人,干脆讓白羽打電話給柳如晗,告訴,自己在軍總做了闌尾炎手。
白羽已經打點好護士了,請們千萬別說了。
柳如晗來的時候,還帶了家里的保姆阿姨,保姆手里提著湯,急匆匆地就過來了。
坐下來就心疼地瞧著:“怎麼不提前和媽媽說,媽媽也好來陪陪你。”
“小手而已,”霍慈冷冷淡淡的。
柳如晗也不生氣,親自盛了湯端給,見乖巧地接過去,心底一舒,可轉念又心疼地說:“早說過了,你也該找個知冷知熱的人。”
“行,”霍慈應了一聲,柳如晗開心地連眉都要飛起來,然后淡淡地說:“你給我也找個保姆吧。”
柳如晗噎了下,眨著一雙眸,盯著看。
許久,轉移話題說:“你還記得陸路璐嗎?”
霍慈照舊喝湯。
“就是以前總和沈茜一起玩的那個孩,人家最近都要結婚了,老公居然和你校友,而且我瞧著眼的。你說比你年紀還小呢,都……”
沒念叨完,霍慈就抬頭了,眼神厲地跟冰針一樣,扎到人心里。
“我哪個同學?”
柳如晗還以為生氣了,訕笑說:“也不一定是你同學,估計是同校吧,反正也是b大畢業的。”
“什麼?”
柳如晗略想了下;“好像姓陳,媽媽昨天親自送了請柬到家里來,說了好久,反正滿意這個準婿的。說小伙子模樣長得好,學歷也不錯。”
周圍不孩子都結婚了,柳如晗瞧著霍慈這麼多年,連個正經男朋友都沒找過,心里能不著急。
況且更怕的是,霍慈還沒放下沈隨安。
“陳忻是吧?”霍慈把湯喝完了,隨口說了名字。
柳如晗一頓,恍悟道:“還真是你同學啊。”
“你的請帖呢,正好那天我也要去,到時候我去家里接你一起吧,”霍慈看著,淡淡地說。
柳如晗沒想到能主這麼說,都沒顧得上為什麼問自己要請帖。高興地連連點頭。
為了請帖,霍慈讓白羽送們回去,順便把請帖要了回來。
等拿到請柬,霍慈看著上頭婚紗照新郎新娘的模樣,一聲冷笑,給莫星辰打了電話。
對面剛接通,就問:“莫星辰,要不要跟我去搞事?”
莫星辰怔了下,特傻地反問:“搞什麼事?”
“弄死陳忻那傻。”
猜你喜歡
-
完結1161 章
他養的小可愛太甜了
他是商界數一數二的大人物,眾人皆怕他,隻有少數人知道,沈大佬他……怕老婆! 沈大佬二十八歲以前,對女人嗤之以鼻,認為她們不過是無能,麻煩又虛偽的低等生物。 哪想一朝失策,他被低等生物鑽了空子,心被拐走了。 後來的一次晚宴上,助理遞來不小心摁下擴音的電話,裡麵傳來小女人奶兇的聲音,「壞蛋,你再不早點回家陪我,我就不要你了!」 沈大佬變了臉色,立即起身往外走,並且憤怒的威脅:「林南薰,再敢說不要我試試,真以為我捨不得收拾你?」 一個小時之後,家中臥室,小女人嘟囔著將另外一隻腳也塞進他的懷裡。 「這隻腳也酸。」 沈大佬麵不改色的接過她的腳丫子,一邊伸手揉著,一邊冷哼的問她。 「還敢說不要我?」 她笑了笑,然後乖乖的應了一聲:「敢。」 沈大佬:「……」 多年後,終於有人大著膽子問沈大佬,沈太太如此嬌軟,到底怕她什麼? 「怕她流淚,怕她受傷,更……怕她真不要我了。」正在給孩子換尿布的沈大佬語重心長的
105.2萬字8 127617 -
完結38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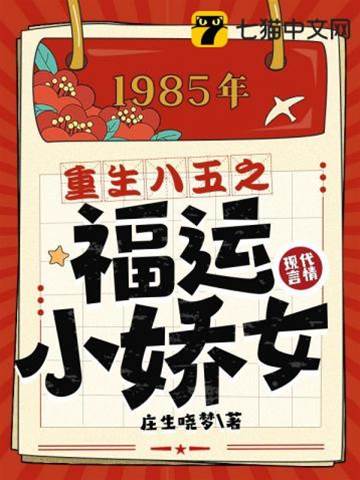
重生八五之福運小嬌女
前世,喬金靈臨死前才知道爸爸死在閨蜜王曉嬌之手! 玉石俱焚,她一朝重生在85年,那年她6歲,還來得及救爸爸...... 這一次,她不再輕信,該打的打,該懟的懟。 福星錦鯉體質,接觸她的人都幸運起來。 而且一個不留神,她就幫著全家走向人生巔峰,當富二代不香嘛? 只是小時候認識的小男孩,長大后老是纏著她。 清泠儒雅的外交官宋益善,指著額頭的疤,輕聲對她說道:“你小時候打的,毀容了,你得負責。 ”
70.5萬字8 21891 -
連載552 章

妻女死祭,渣總在陪白月光孩子慶生
【重生+雙潔+偽禁忌+追妻火葬場】和名義上的小叔宮沉一夜荒唐后,林知意承受了八年的折磨。當她抱著女兒的骨灰自殺時,宮沉卻在為白月光的兒子舉辦盛大的生日宴會。再次睜眼,重活一世的她,決心讓宮沉付出代價!前世,她鄭重解釋,宮沉說她下藥爬床居心叵測,這一世,她就當眾和他劃清界限!前世,白月光剽竊她作品,宮沉說她嫉妒成性,這一世,她就腳踩白月光站上領獎臺!前世,她被誣陷針對,宮沉偏心袒護白月光,這一世,她就狂扇白月光的臉!宮沉總以為林知意會一如既往的深愛他。可當林知意頭也不回離開時,他卻徹底慌了。不可一世的宮沉紅著眼拉住她:“知意,別不要我,帶我一起走好嗎?”
101萬字8.33 184598 -
完結179 章

灼灼浪漫
大雨滂沱的夜晚,奚漫無助地蹲在奚家門口。 一把雨傘遮在她頭頂,沈溫清雋斯文,極盡溫柔地衝她伸出手:“漫漫不哭,三哥來接你回家。” 從此她被沈溫養在身邊,寵若珍寶。所有人都覺得,他們倆感情穩定,遲早結婚。 有次奚漫陪沈溫參加好友的婚禮,宴席上,朋友調侃:“沈溫,你和奚漫打算什麼時候結婚?” 沈溫喝着酒,漫不經心:“別胡說,我把漫漫當妹妹。” 奚漫扯出一抹得體的笑:“大家別誤會,我和三哥是兄妹情。” 她知道,沈溫的前女友要從國外回來了,他們很快會結婚。 宴席沒結束,奚漫中途離開。她默默收拾行李,搬離沈家。 晚上沈溫回家,看着空空蕩蕩的屋子裏再無半點奚漫的痕跡,他的心突然跟着空了。 —— 奚漫搬進了沈溫的死對頭簡灼白家。 簡家門口,她看向眼前桀驁冷痞的男人:“你說過,只要我搬進來,你就幫他做成那筆生意。” 簡灼白舌尖抵了下後槽牙,臉上情緒不明:“就這麼在意他,什麼都願意爲他做?” 奚漫不說話。 沈溫養她七年,這是她爲他做的最後一件事,從此恩怨兩清,互不相欠。 那時的奚漫根本想不到,她會因爲和簡灼白的這場約定,把自己的心完完全全丟在這裏。 —— 兄弟們連着好幾天沒見過簡灼白了,一起去他家裏找他。 客廳沙發上,簡灼白罕見地抵着位美人,他被嫉妒染紅了眼:“沈溫這樣抱過你沒有?” 奚漫輕輕搖頭。 “親過你沒有?” “沒有。”奚漫黏人地勾住他的脖子,“怎麼親,你教教我?” 衆兄弟:“!!!” 這不是沈溫家裏丟了的那隻小白兔嗎?外面沈溫找她都找瘋了,怎麼被灼哥藏在這兒??? ——後來奚漫才知道,她被沈溫從奚家門口接走的那個晚上,簡灼白也去了。 說起那晚,男人自嘲地笑,漆黑瞳底浸滿失意。 他凝神看着窗外的雨,聲音輕得幾乎要聽不見:“可惜,晚了一步。”
30.6萬字8.18 2007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