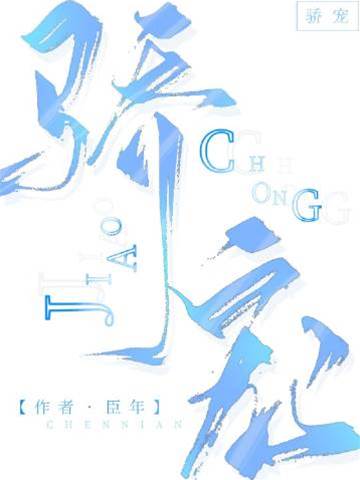《我就喜歡他那樣的》 第28章
啊,怎麼不繼續了?
霍慈怔怔地看他,卷翹的長睫輕輕抖,狹長的眼尾向上彎著,烏黑地眼睛又亮又潤,此時眼神中蒙著一層詫異,帶著無辜,仿佛聽不懂他說的話。
易擇城眼神一下就深了。
火苗從小腹,蹭地一下就竄起來,燒心撓肺,擋都擋不住。.來地是如此急切,他是個男人,但并不重。要不然這麼多年,也不至于邊連個人都沒有。
可這一刻,他無比清楚地覺到.的存在。
然后,一只細的手掌,了上來。隔著一層薄薄地布料。
他知道這雙手有多,握在手掌里像沒有骨頭一樣。只是手指間有些糙,是常年用相機的原因。
從臺穿越進來,將整個房間照地亮,兩人的表只要抬頭都能看地一清二楚。靠在他的上,側偏著頭。從他的角度低頭看下去,的睫在抖,角微微抿著。像是在思考,又像是忍著。
他腦海中閃過無數的畫面,被在車下鮮模糊,看不清臉的霍慈。在浴室里白地幾近明的,還有手房外,抱著他的霍慈。
鮮活的畫面,在這午后猶如一針藥劑,搭在他心頭。
他腦子里有一弦在慢慢拉。
直到,霍慈仰起頭看他,那雙眼睛不像平時那麼冷靜清澈,而是染上了一層。
微張著,想要說什麼時,‘轟’,易擇城腦子里的那弦拉斷了。
易擇城低頭,咬住的。他的手指扣著的臉頰,不輕不重,卻彈不得。漸漸上的力道加重,直到舌頭用力地撬開,裹著的。空氣一下稀薄,鼻息間都是彼此的溫熱氣息,狠狠糾纏。
Advertisement
霍慈被他親地暈頭轉向,沒一會,連呼吸都加重。
才知道,以往自己的那點兒勾引,本什麼都不是。
穿著長,易擇城扣著的腰,從脊背往下,薄下平整,他的手停住。然后微微往后推,熱吻遽然結束,霍慈一臉迷茫地看著他。
他如琥珀般地眸子,此時又深又黑,盯著說:“沒穿,嗯?”
又是這個氣聲,霍慈一下咬著他的下上,惡狠狠地說:“你就是主勾引我的。”
像是被惹地發狂的小野,咬著他的,就毫無章法地開始親。其實霍慈雖然膽大臉皮厚,可那都是在易擇城面前。真到了論真章的時候,就餡了。被親地連呼吸都不過來了,糙糙地撞上來,著一子生地味道。
被易擇城抱了起來,這次又變被在門板上。
“霍慈,不要停,”他低頭在耳垂上了下,霍慈整個人都僵了。
太太,說不出地覺。
的反應功地取悅了面前的男人,然后的薄被堆到腰間。
雪白地長大剌剌地刺激著他的視線。
霍慈咬著,然后一只手直接從邊緣探了進去。兩人同時繃住,手里握著的是炙熱滾燙的,然后那里在手下跳了跳,筆直,堅。
誰都沒說話,呼吸卻早已經不控制地紊了。
霍慈看著他的眼睛,那里不再冰冷,不再淡然,又深又沉,像火在燒。
細的手掌上下著,他悶哼一聲。
是舒服的。
霍慈垂著眼,卻在下一秒又被易擇城抬起了下,兩人的再次糾纏在一起。吻地太深,霍慈不上氣。
“霍慈,你在嗎?”后的門板被拍響,徐斯揚在門外喊。
Advertisement
兩人同時一僵,看著彼此。午后的,又濃又烈。這就像是年的某個暑假,小躲在房間里吃.果,長輩卻突然回到家里。
易擇城抬頭看著后的門,角一,似乎要說話。
霍慈猛地湊上去堵住他的,也不知道為什麼會是這種反應。
“霍慈,我給你拿了點午餐,你要吃點嗎?”徐斯揚又問了一句。
然后另外一個聲音響起,是葉明詩,說:“可能不在吧。”
一門之隔,這種刺激,連易擇城都不了了。霍慈全都在抖,他將抱起來,抵在門上,懸在半空中,全的支撐就是架著彎的雙手。
薄衫堆在腰間,直到他滾燙的東西,抵上來。
“這孩子也真是的,就喜歡跑呢,”徐斯揚老神在在地搖頭。
直到葉明詩問:“學長也不在房里嗎?”
徐斯揚被一提醒,這才恍悟,生氣地說:“你說他們兩會不會跑出去吃去了?”
吃……
他的滾燙就抵在那里,隔著一片早就的.,直到他緩緩開始。咬著,不敢出一聲音。
門外有人,而門里是他和。
葉明詩輕笑,嗔地說:“您別這麼說,學長不是那樣的人。”
然后霍慈抬頭,就看見他正看著。
……
外面徹底安靜了,門板上的撞擊聲漸起。地抱著他的肩膀,整個人息地靠在他上。
易擇城沒有徹底進來。
但霍慈卻渾抖,被碾磨著,著,從小腹升起的一接著一地覺,是從未會的,栗、麻、還有無盡地舒服。
被抱著躺在床上的時候,累地連手指尖都抬不起來。
Advertisement
易擇城下床,給拿了一瓶礦泉水過來。
等喝完之后,他躺在邊,手撥弄了的長發。霍慈安靜地看著他,易擇城想了想,想要開口解釋。
就聽說:“這里不對。”
他們是來工作的,這種地方、這種況都跳了他們的計劃。
依舊濃,房間里的冷氣發著嗡嗡地聲音,霍慈的眼皮重了起來。易擇城沒睡,躺在旁邊,安靜地看著。
的臉頰又小又致,閉著眼時,沒了平日里的冷漠,地不可思議。
**
易擇城回房間的時候,徐斯揚正在打電話,見他回來揮了揮手,很快就掛斷了電話。
他抱怨:“你跑哪兒去了,今天你還罵霍慈跑,我看你自己也不讓人省心。”
易擇城走到桌子旁邊,拿起桌上的煙盒,取出一。等點燃之后,他深深地吸了一口,問:“你怎麼還沒走?”
徐斯揚:“……”
“不是要去塞加爾參加拉力賽的,今天我就讓人給你轉五百萬,”易擇城淡淡地吐了一口氣,神淡然。
徐斯揚來這里,就是為了跟他要錢的。
可是這會易擇城真給他錢了,他又氣地哇哇大,說道:“你就是這麼打發親小舅舅的嗎?”
易擇城瞥他一眼:“不要?”
徐斯揚被他一瞧,沒骨氣了,嗡聲嗡氣地說:“要,是你自己主提價的,不許反悔。”
易擇城走到臺打電話,徐斯揚就跟了出來,問他:“你剛剛到底去哪兒了?我去找霍慈,也不在,你們不會是一起出去的吧?”
聽他提起霍慈的名字,易擇城眸一深,臉上出危險的表。
徐斯揚一瞧見他這表,嚇得都不敢說話了。
晚上,徐斯揚在酒店的餐廳請他們吃飯,雖然相才幾天,不過臨別踐行還是不了的。
Advertisement
霍慈是下來最慢的,穿著一長長,把自己裹地嚴嚴實實。到的時候,就剩下兩個位置,一個徐斯揚旁邊,一個易擇城邊。葉明詩早已經在易擇城的另一邊坐下,正低聲和他說話。
“霍慈,你來了,趕過來坐吧,”徐斯揚拍了拍他旁邊的椅背。
易擇城抬頭看,剛才徐斯揚要坐在他旁邊,被他趕走了。這會他心中不忿,故意喊霍慈。
稚,易擇城心底冷嗤一聲。
直到霍慈施施然地在徐斯揚邊坐下,他高興地給倒了一杯紅酒,笑著說:“雖然我要走了,不過回國之后,咱們可以繼續見啊。”
徐斯揚還故意沖著眨眼,輕笑著說:“你可別忘記我啊。”
“徐斯揚你也太不公平了吧,只對霍慈獻殷勤,”葉明詩在一旁撅嗔。
徐斯揚哼笑了一聲:“誰讓人家霍慈是呢。”
言下之意,就是葉明詩長得不夠。
雖然只是開玩笑,葉明詩登時有點兒生氣,推了旁邊易擇城旁邊手肘說:“學長,你可得說說徐斯揚。”
易擇城原本正在低頭發短信,直到他輕輕點擊了發送。
才抬起頭,看著對面的霍慈,輕聲說了句:“哦。”
哦是什麼意思?
徐斯揚大笑,喊道:“你看,你看,就連我家城城都贊同我的話呢。”
此時霍慈放在桌上的手機響了,是短信來了。
手拿起,解鎖之后,就看見一個從未出現過地名字,頭一次出現在的信息欄里。
易冰山,有他手機之后,就保存地這個名字。
“今晚給我留門。”
猜你喜歡
-
完結96 章
再見及再愛
家道中落,林晞卻仍能幸運嫁入豪門。婚宴之上,昔日戀人顏司明成了她的“舅舅”。新婚之夜,新婚丈夫卻和別的女人在交頸纏綿。身份殊異,她想要離他越遠,他們卻糾纏得越來越近。“你愛他?”他笑,笑容冷厲,突然出手剝開她的浴巾,在她耳朵邊一字一句地說,“林晞,從來沒有人敢這樣欺辱我,你是第一個!”
17.2萬字8.18 20793 -
完結1965 章

盛寵名門佳妻
旁人大婚是進婚房,她和墨靖堯穿著婚服進的是棺材。空間太小,貼的太近,從此墨少習慣了懷裡多隻小寵物。寵物寵物,不寵那就是暴殄天物。於是,墨少決心把這個真理髮揮到極致。她上房,他幫她揭瓦。她說爹不疼媽不愛,他大手一揮,那就換個新爹媽。她說哥哥姐姐欺負她,他直接踩在腳下,我老婆是你們祖宗。小祖宗天天往外跑,墨少滿身飄酸:“我家小妻子膚白貌美,給我盯緊了。”眾吃瓜跟班:“少爺,你眼瞎嗎……”
284.1萬字8 29639 -
完結43 章

我的愛生生不息
雲知新想這輩子就算沒有白耀楠的愛,有一個酷似他的孩子也好。也不枉自己愛了他二十年。來
4.3萬字8 13074 -
完結493 章

甜心玩火:誤惹霸情闊少爺
訂婚宴當天,她竟然被綁架了! 一場綁架,本以為能解除以商業共贏為前提的無愛聯姻,她卻不知自己惹了更大號人物。 他…… 那個綁架她的大BOSS,為什麼看起來那麼眼熟,不會是那晚不小心放縱的對象吧? 完了完了,真是他! 男人逼近,令她無所遁逃,“強上我,這筆賬你要怎麼算?”
90.4萬字8 37776 -
完結77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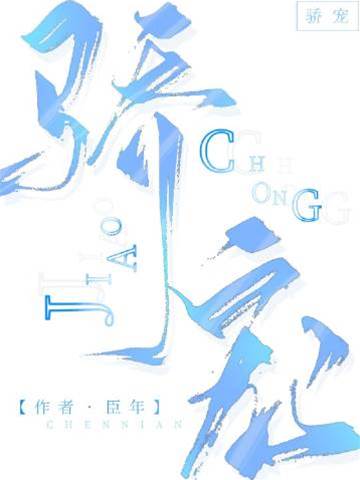
驕寵
作為國家博物館特聘書畫修復師,顧星檀在一次美術展中意外露臉而走紅網絡,她一襲紅裙入鏡,容顏明艷昳麗,慵懶回眸時,神仙美貌顛倒眾生。后來,有媒體采訪到這位神顏女神:擇偶標準是什麼?顧星檀回答:我喜歡桀驁不馴又野又冷小狼狗,最好有紋身,超酷。網…
31.3萬字8 4218 -
完結503 章

沈總別虐了,夫人和新歡約會上熱搜了
結婚三週年紀念日那天,沈澤撂下狠話。 “像你這樣惡毒的女人,根本不配成爲沈太太。” 轉頭就去照顧懷孕的白月光。 三年也沒能暖熱他的心,葉莯心灰意冷,扔下一紙離婚協議,瀟灑離開。 沈澤看着自己的前妻一條又一條的上熱搜,終於忍不住找到她。 將她抵在牆邊,低聲詢問,“當初救我的人是你?” 葉莯嫌棄地推開男人,“沈總讓讓,你擋着我約會了。”
36.8萬字8 336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