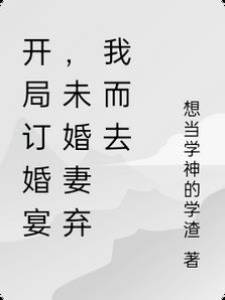《歸路》 第四十二章 尾章 歸路向晨曉(1)
小朋友滿月和半歲時都驗了,一切正常。
兩人的婚禮,定在了路初小朋友一歲半那天。不是不想在周歲,只怪小朋友生在了冬天,太不適合親媽穿婚紗,只好推遲到初夏。
婚禮地點上,歸曉和路炎晨商量要辦兩場。
第一場比較隆重傳統,在男方這里,回到這個鎮子上,第二場就隨便了,主要是請歸曉和路炎晨的同事們吃頓飯就好。歸曉初次到路炎晨家,孟家和秦家做陪著上門,這大兒媳婦雖沒太重視,但也因為“靠山”強大,沒氣。路炎晨說明了不要路爹買房買車,路爹不“掉”就也沒找茬。歸曉家里如何條件,沒人細說過,再加上歸曉父母都在這當口不在京,更是省了麻煩。只有路媽嘀咕了幾句,兩家結親也該先面吃頓飯,被路炎晨妹妹頂回去了。路媽就這麼親生的一兒一,想著老了還要倚仗,也就沒再多過話。
迎親前晚,將姑姑家當作了“娘家”住了一晚,等著第二天迎親。
雨聲陣陣,歸曉跪在床上,挪去窗邊。
看到大顆的雨滴打著玻璃,濺出一個個泛白的水印子。
“這大雨真麻煩,明天要還下著,你那婚鞋就報廢了。”孟小杉靠在棉被堆上,打著哈欠,一手撐頭,一手去翻那張請柬。
全是路炎晨手抄的,正面底下就有:晨曉,照歸路。
翻過來,是發出去前一晚歸曉一張張添上的另一句話:寸寸山河夢,昭昭赤子心。
“我老公特喜歡你這句話,還拿這個說我呢,”孟小杉控訴,“說你才懂路晨,我不懂他……”
“別說請柬了……我張得不行,怎麼辦?”歸曉焦慮癥都犯了。
沒辦過婚禮,窮焦慮。
Advertisement
“張什麼啊,”孟小杉嘆著,將床上收拾干凈,“反正你記得我的話,結婚過去了,你就和路晨踏實住在市區,別常回來。我私下問過路晨,他也是這個意思,他從小在這家就可有可無的,能不回來就不回來,你倆踏實過日子。”
提到這話,歸曉仍舊激:“多虧你和秦楓面子大,了好多麻煩。”
“誰讓你樂意嫁呢,姐姐就盡力給你掃除障礙唄,”孟小杉去看靠墻睡的小娃,“真好看,哎,我要再生個兒子娶你閨……不就姐弟了?你介意嗎?”
“……等你生出來再說吧。”沒影的事……
孟小杉也就說著玩,喜歡二人世界,反正秦楓也是小兒子,家里父母早就抱夠了孫子孫,也不指他們再添新丁,樂得逍遙。
孟小杉看時間晚了,算著五點要起來化妝,趕去客房和伴娘床睡了。
到凌晨一點,歸曉將一個小枕頭放在路初手臂側,離開臥室,穿客廳,去臺,小心翼翼將門鎖打開。
一雨后泥土的氣息撲面襲來。
雨停了。
邁上臺階,反手關門。
小時候,姑姑還有閑心在這里種葡萄和草莓,眼下倒了菜地,不是蔥就是油菜……還沒唏噓一會兒,路炎晨來了電話。歸曉看到他名字還奇怪,今晚不是他和好兄弟聚的時間嗎?接通放在耳邊上:“你不是喝多了吧?”
“沒,沒喝。”
“你不喝他們能放過你嗎?”
“抬頭,看前方。”
歸曉順他的指令,看前方。
就在當初的那個位置,高考后他開車來接自己的那個地方,分毫不差,一輛車再次被停靠在路邊上。車旁有他,還有那若若現的一點。
Advertisement
“你不睡了?”
“好幾個喝多了,把床和沙發都占了。”
“那好吧……反正我也睡不著,”著馬路上的人,“不過也不能過去找你,孟小杉說了,結婚前一晚你不能見我。”
路炎晨好像是笑了聲:“我閨尿布換了嗎?”
“換了。”
“呢?”
“……都一點了你才問,早喝完了,”歸曉嘟囔,“別弄得你是親爸,我是后媽一樣。”
……
“你錢包里有一張卡,”路炎晨吸了幾口煙,慢悠悠地說著,“全清了,以后這卡就給你了。”
“工資卡啊?”
“嗯。”
“都給我?”
“都給你。”
“你不要零花錢?”
“我吃飯不是在基地就在家里,平時也要穿統一制服,單位有班車,沒什麼需要花錢的地方。不用給我留。”
歸曉咬著下笑:“也對。”
全副家當連帶人,從明天開始就真的都歸了。
路炎晨雖然沒這麼說,但如此做了,還做得悄無聲息,徹徹底底,沒半點拖泥帶水,沒任何后路。難怪……他堅持要一歲之后再辦婚禮,原來是早做了這打算,剛好工作了兩年多,債全清了,還夠辦個婚宴。
“好了,待完了,走了。”黑暗中那一點火星的亮也熄了。
“去哪?”
“開車轉轉,你去睡會兒,明天的新娘子,”他笑,末了輕嘆了聲,低低地說,“我真沒想過,還有能娶到你這天。”
聽得心頭了,睫很快就被涌出來的眼淚打了。
“走了,明天來接你。”
他沒再啰嗦,上車,在刺眼的車燈和油門聲中,駛離這里。
次日的婚禮超乎想象的熱鬧,趕火車似的被接親,離開大院,向孟小杉家的酒樓開去。又是迎賓,又是照相,婚禮進行曲都走完了,還沒來得及氣就被人推上去。
Advertisement
觀禮臺上一站,旁邊那個估計這輩子也就穿這麼一回西裝的男人,慣地兩指住領帶結,扯松了些。底下有人起哄:“晨哥,這你就不了了?想解領帶房了啊?”
路炎晨挑眉一笑,瞇了眼去找聲音源頭:“你小子是不是今天不打算回去了?”
人生最得意之時,倒像回到過去,在鎮上哪哪都要被聲“晨哥”的日子。
那人忙擺手:“不敢,晨哥,這可不敢。”
眾人哄笑。
孟小杉一本正經起來:“最后環節了。讓新郎說幾句言,說完,大家該吃吃該喝喝,喝多了樓上包房都騰出來了,隨便睡。”
作勢要將話筒遞給路炎晨,卻又自己收回來:“哦,對,讓我再說兩句。”
證婚人秦楓看不下去,咳嗽了聲:“差不多可以了,要再想當主角,以后我再給你辦一場結婚十周年的。”
又是一陣笑,平時見不著這兩夫妻當面鑼對面鼓的互嗆,今天倒瞧足了。
“……老公我就多說一句,”孟小杉轉臉看路炎晨,“你就說,我夠不夠意思?你媳婦兩年前找我定的菜單,今天我一分錢沒漲給你們的。路晨你說我夠不夠意思?”
路炎晨無奈,將話筒拿過來:“算。”
能在路晨這里討點上便宜,可是孟小杉從小就有的心愿,如此也算是圓夢了,心滿意足下臺。
最后,只留了路炎晨和歸曉在臺上。
路炎晨將話筒舉起:“認識我老婆那年,十三歲,初二,就在中學場北面,小賣鋪門口的楊樹那里。當時我看到第一個念頭就是,”他去看歸曉,說,“這麼好看的姑娘哪里來的?”他從初中就開始混在外頭,鎮上稍微漂亮些的姑娘都是名聲在外,可他沒聽說過“歸曉”這個名字。
Advertisement
好像,和他在平行的兩個世界里,直到那年,歸曉被表妹帶到他面前。
他記住了歸曉。
歸路的歸,晨曉的曉。
……
就這一句開場,真是惜字如金。
底下的也都曉得路炎晨的脾氣,起哄著,讓倆人趕親一個。
歸曉還在細細研究路炎晨的那句話,他臉已經離得很近了。眾目睽睽,歸曉可不好意思,將頭偏了偏,悄聲說:“做個樣子就行吧……”
路炎晨像要來真的。
這麼多人,你不要舌頭啊……算了,可不用熱吻吧……
路炎晨在整個一樓大堂的起哄聲中,右手掌扣在腦后,調整角度,深吻到底。歸曉認命,炸開來的喝彩聲沖撞著一切,仿佛能掀翻堂,震得耳嗡嗡作響。他放開,兩人視線相對著,久久難言。
滿足了眾人的觀賞愿,婚宴順利開席。
歸曉終于得了空坐上主桌,被孟小杉和伴娘催促著吃了兩口熱菜,邊吃邊瞄邊已經將領帶解下來丟到空椅子上的路炎晨。他把兒放到右大上,在小娃的指揮下,轉著玻璃轉盤去夾來,每樣都送到那小里給嘗味道。
“差不多了,路晨,該敬酒了,”孟小杉小聲提點,“伴娘伴郎手里的酒都摻水的,大家心照不宣,你喝點啊,喝一肚子摻水酒也不舒服。讓他們灌死海東算數。”
本來伴娘伴郎是要坐主桌的,可海東和孟小杉的關系終歸特殊,他特地要求自己帶著小朋友改坐了別桌。孟小杉說這話的當口,他正一本正經掏出海王金樽往桌上一拍:“今兒個誰灌晨哥,先過我這關啊。兄弟們可悠著點,晨哥那是婚宴辦完就回市區了,老子可還在這里住著呢,抬頭不見低頭見的,要把我喝出胃出,也不好說不是?”
有人說著不敢,有人說著:“海東,又不是你結婚,怎麼搞得比晨哥還惹不起?”
海東真實地來了句:“路晨結婚,那就是我結婚了。一樣,一樣。”
能有人幫著圓了年的諾言,也是種結局。
猜你喜歡
-
完結264 章

情是回憶如困獸
曾經發誓愛我一生的男人竟然親口對我說: 顧凝,我們離婚吧!”三年婚姻,終究敵不過片刻激情。一場你死我活的爭鬥,傷痕累累後我走出婚姻的網。後來,我遇見師彥澤。站在奶奶的病床前,他拉著我的手: 顧凝,跟我結婚吧,你的債我幫你討回來。”我苦澀的笑: 我隻是個離過婚,一無所有的女人,你幫我討債? 他笑笑點頭,深似寒潭的眸子裏是我看不懂的情緒。 很久以後,我才明白,在他心裏那不過是一場遊戲 .可師彥澤,你知道嗎?那時候,我是真的想和你過一生。
45.2萬字8 19116 -
完結1774 章

荊棘深處
厲墨和唐黎在一起,一直就是玩玩,唐黎知道。唐黎和厲墨在一起,一直就是為錢,厲墨知道。 兩個人各取所需,倒是也相處的和平融洽。只是最后啊,面對他百般維護,是她生了妄心,動了不該有的念頭。 于是便也不怪他,一腳將她踢出局。……青城一場大火,帶走了厲公子的心尖寵。 厲公子從此斷了身邊所有的鶯鶯燕燕。這幾乎成了上流社會閑來無事的嘴邊消遣。 只是沒人知道,那場大火里,唐黎也曾求救般的給他打了電話。那時他的新寵坐在身邊。 他聽見唐黎說:“厲墨,你來看看我吧,最后一次,我以后,都不煩你了。”而他漫不經心的回答, “沒空。”那邊停頓了半晌,終于掛了電話。……這世上,本就不該存在后悔這種東西。 它嚙噬人心,讓一些話,一些人始終定格在你心尖半寸的位置。可其實我啊,只是想見你,天堂或地獄
276.9萬字8 29007 -
連載16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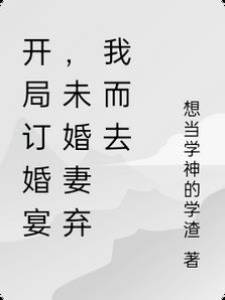
開局訂婚宴,未婚妻棄我而去
微風小說網提供開局訂婚宴,未婚妻棄我而去在線閱讀,開局訂婚宴,未婚妻棄我而去由想當學神的學渣創作,開局訂婚宴,未婚妻棄我而去最新章節及開局訂婚宴,未婚妻棄我而去目錄在線無彈窗閱讀,看開局訂婚宴,未婚妻棄我而去就上微風小說網。
25.2萬字8.18 242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