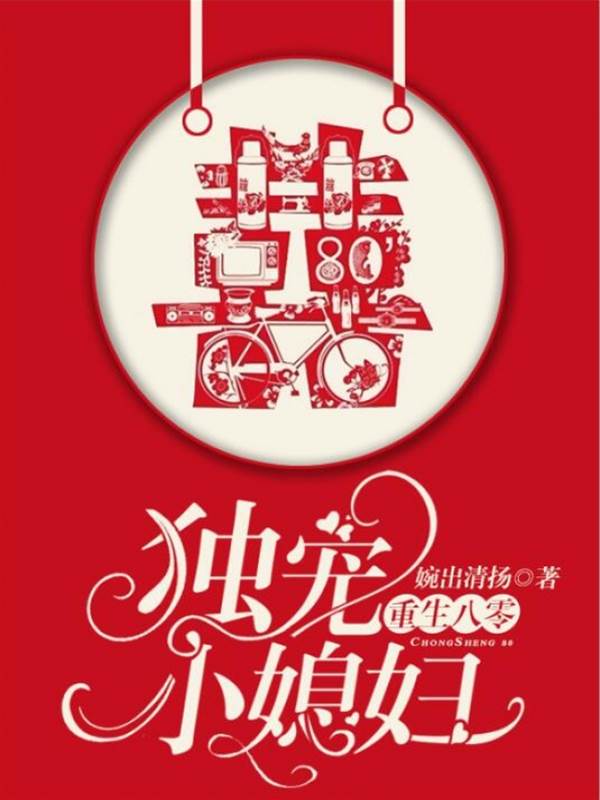《軍爺撩妻之情不自禁》 第505章 大結局(上) (1)
炎珺始料未及自己就一個轉的時間,孩子怎麼就變這模樣了?
一旁的沈三分雙手都是染料,一臉人畜無害的看著,好像力行的告訴老人家:我如果說是弟弟先手的,你會信嗎?
炎珺扶額,該怎麼勸誡小三分同志弟弟是用來疼的呢?
沈四分還有些懵,一張臉,不對,是整個人,除了那雙眼沒有被涂上花花綠綠的外,全上下無一幸免,包括那個——
炎珺一言難盡啊。
沈三分踮了踮腳尖,小鼓了鼓,閃爍著自己那明亮亮的大眼珠子。
炎珺嘆口氣,“你做的?”
沈三分把自己的兩只手藏起來,很努力的搖著頭,裝作聽不懂。
炎珺蹲下子,把他的小手從后給拉了出來,然后攤開他的手掌心,“為什麼要這麼欺負弟弟呢?”
沈三分了自己鼓起的腮幫子,“弟弟要。”
炎珺看向兒床里一臉生無可狀態下的孩子,等等,為什麼從一個不到十天的孩子里看出了生無可四個字?
沈三分很認真的眨著眼,他邁開自己的小碎步跑到了兒床邊,然后抓起沈四分的小手,用著自己匱乏的詞語解釋著,“弟弟要涂,弟弟喜歡,弟弟漂亮。”
炎珺一掌拍在自己的額頭上,“好了好了,不抹了,不涂了。”竟然妄想讓一個不到兩歲的小家伙給自己解釋為什麼要把弟弟弄的滿臉都是,他玩料還會有理由嗎?小孩子心本就是貪玩。
沈四分無辜的嘟了嘟,他抬起手遮了遮自己的小臉,繼續生無可中。
沈三分規規矩矩的站在一旁,臉蛋有些,他手抓了抓。
“小寶別弄自己。”炎珺拿著巾替他了手,“去找你二伯,讓他給你洗一洗。”
Advertisement
沈三分高高的舉著自己的手,一路風馳電擎的爬上了三樓。
“轟轟轟。”震耳聾的音樂聲將整個門板都震得晃了晃。
沈三分站在門口,敲了敲門,好像并沒有人過來給他開門。
他繼續敲了敲,依舊沒有人過來給他開門。
“轟轟轟。”音樂聲再一次震起來。
沈三分趴在地上,過門想要看一看里面。
“弟弟你在干什麼?”沈筱筱學著小三分的模樣也趴在地上。
沈三分努力的想要把自己的小手指進那個隙里。
沈筱筱搞不懂他的意圖,也是同樣把小手進去。
“哐當。”結實的房門從底部開始裂,不過眨眼間,一塊一塊全部碎開。
沈晟易剛剛洗完澡,腰間隨意的搭著一條浴巾,一臉隨心所的坐在沙發上,右手執杯,打算痛飲一杯。
只是酒杯剛到邊,自己的大門就像是破碎的玻璃還有些掉渣的全部碎在了地毯上。
門口還有兩個趴著一不的小孩子正高高的抬著無辜的腦袋仰著雍容華貴的自己。
沈三分從地上爬起來,繼續舉著自己的小手手,“二伯洗洗,二伯洗洗。”
沈晟易看著他手上那燦爛的五六,角忍不住的了,“你就為了讓我給你洗手而毀了我一扇門?”
沈三分翹著,“臟臟,臟臟。”
沈晟易放下酒杯,將小孩子扛在肩上。
沈筱筱趴在桌子上,目灼灼的盯著杯子里那妖艷的紅,出小手輕輕的了杯子,里面的經外力而不由自主的晃了晃。
環顧四周,洗手間方向傳來斷斷續續的流水聲,鼓了鼓自己的,最后輕輕的將酒杯給移了過來。
沈晟易拿著干凈的巾將小家伙得干干凈凈,再心的替他噴了一點花水,滿意的點了點頭,“好了,你可以出去玩了。”
Advertisement
“砰砰砰。”一陣雜的聲音從門外傳來。
沈晟易驀地直,他詫異道,“什麼聲音?”
“轟轟轟。”好像是什麼塌了。
沈晟易心口一滯,急忙推開洗手間的玻璃門,不敢置信的著自己床后面那一無際的藍天白云。
如果他沒有記錯的話,他床后面應該有一堵很結實的墻。
墻呢?他的墻呢?
沈筱筱腦袋有些暈,搖頭晃腦的從床底下爬了出來,臉蛋紅的就像是的櫻桃,還滴著水。
沈晟易見此一幕,回頭看了看桌邊那一杯自己剛剛倒上去的紅酒,不對,不止杯子里的紅酒沒有了,剛開封的那一瓶82年拉菲也只剩下一半了。
誰喝了?
沈晟易僵的扭腦袋,只見自家小公主踩著魔鬼的步伐正興高采烈的朝著他奔跑了過來。
沈筱筱咧開笑的可燦爛了,“二伯,二伯抱抱,二伯抱抱。”
沈晟易一個勁的往后退,拼了命的往后退。
沈筱筱一把抱住他的大,像個小懶貓一樣在他上蹭了蹭。
沈晟易很努力的提著自己的浴巾,他覺得快掉了,快要被小丫頭給扯掉了。
沈筱筱噘著,“二伯抱,二伯抱。”
小丫頭一筋的朝著他上爬,可是爬了兩次都沒有爬上去,最后疲力竭的坐在了地板上,手里還的拽著浴巾一角。
沈晟易本以為放棄了自己,剛一轉準備跑,后背拔涼拔涼的。
沈三分一把捂住自己的眼,又默默的分開了兩手指頭,手指頭的隙正好對著一不掛的親二伯。
沈晟易的視線慢慢下挑。
“沈晟易,你這個臭小子,你在做什麼?”沈一天的咆哮聲從門口傳來。
沈筱筱慢悠悠的抬起頭,腦袋有些暈。
Advertisement
沈一天以著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一把擰住沈晟易的耳朵,強的將他給拽進了洗手間。
沈三分蹲在姐姐面前,大眼珠子明晃晃的看著緋紅的臉。
“嗝。”沈筱筱傻笑著打了一個酒嗝。
沈三分抬起手捧著的臉,“姐姐,姐姐。”
沈筱筱掩噓了噓,“乖寶寶不說話。”
沈三分見著自家姐姐往前爬了爬,兩只手捧著一只瓶子。
沈筱筱一個字一個字的蹦著,“甜,很甜很甜,跟糖似的,甜。”
沈三分聞了聞,有些熏鼻子。
“筱筱喜歡喝。”沈筱筱咕嚕咕嚕的喝了一口。
沈三分看著邊流下來的紅酒,長脖子,“弟弟喝,弟弟喝。”
沈筱筱遞過去,“好喝。”
沈三分張大喝了一口,不是特別甜,還有點苦,他皺了皺眉頭,“不好喝。”
“好喝,好喝。”沈筱筱又說著。
沈一天居高臨下的瞪著穿好了服的二兒子,痛心疾首道,“你怎麼能在孩子們面前做出這種有失大的事?”
“父親您聽我解釋,我可是害者啊。”
沈一天自上而下的審視他一番,“果然一個人寂寞久了心里就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扭曲自卑。”
“……”
“我已經和木家的老爺子商量好了,這個周末你和木小姐好好的聊聊吧。”
沈晟易瞠目,“怎麼又扯到這事上了?”
“你覺得這樣的安排很不妥?”沈一天目犀利的落在他上,“我不管你是愿意還是不愿意,這事毋須商量,你如果非要商量,”沈一天視線下挑,“反正那玩意兒不娶人留著也沒有什麼用,我親自替你廢了。”
沈晟易下意識的扭著腰,夾著。
沈一天雙手叉環繞,“我是在給你說我的決定,不是在和你商量我的決定。”
Advertisement
“哐當。”一聲不容忽視的驚響聲從門外傳來。
沈一天神一凜,一把推開了洗手間大門。
天花板上的燈忽閃忽閃,所有東西好像失去了地心引力浮在半空中,有一陣狂風從破損的墻壁中肆的涌進,吹得滿屋子的東西叮叮當當。
“怎麼回事?”沈一天本想著出洗手間看看況,卻是只走了一步就被退回來,他們的頭頂上空好巧不巧的飄著一只音響,看那積以及重量,砸死他綽綽有余。
沈晟易指著坐在床上抱著酒瓶一個勁傻笑的沈三分,他的旁邊還趟著一個大概已經喝醉的沈筱筱。
沈一天定睛一看,轉過一掌拍在兒子的腦門上,“你給孩子們喝酒?”
沈晟易哭笑不得,“我怎麼可能給他們喝酒,是他們喝了我的酒。”
沈一天進退為難,“現在該怎麼辦?你出去冒死給小寶醒酒。”
沈晟易兩只手拉著洗手間的大門,“父親,您兒子才三十五歲啊,大好的青春剛剛萌芽,您怎麼能讓他在青春年華的時候去送死呢?”
沈一天摳著他的手,“為了大義,我們為軍人在所不辭啊。”
沈晟易轉了一個,扯了扯父親的手,有意的將他推出去,并且大義凜然的說著,“父親,您為我們沈家的一家之主,當真是應該為了沈家拋頭顱灑熱,您去給小寶醒酒吧。”
沈一天心口一,“你這個逆子,你竟然妄圖讓你家垂垂老矣的老父親去臨險境?你這樣做,你的余生會不安的,你會夜夜良心譴責而夜不能寐。”
沈晟易搖頭,“父親您放心,我一定會吃好喝好的。”
沈一天借力使力用著巧勁化解了危機,更加功的將自家兒子給推到了門口,他咬牙關,拼盡全力的想要將他推出去,“兒子啊兒子,養兵千日用兵一時,我好歹養了你幾千日,到時候你為了報恩義無反顧的沖出去了。”
沈晟易雙手撐著門框,“父親,我答應您去見木思捷,我們有話好好說。”
沈一天本打算再說什麼,洗手間的燈管啪的一聲全部碎了。
塵鋪天蓋地的灑了一地,兩人還沒有反應過來,柜子里的吹風機,柜子上面的剃須刀,柜子下面的按,只要是屋子里能通電的東西,一個接一個浮了起來。
沈晟易想往后退,剛退了一步又把自己的腳了回來,他吞了吞口水,小心翼翼的說著,“父親,我有一種即視,我們倆今天要代在這里。”
沈一天回過頭,目繾綣的著自家玉樹臨風的兒子,眼底的溫像塞滿了棉花糖,看著看著就化了。
沈晟易心里莫名的打了一個激靈,為什麼在這個時候他突然想起了一句歌詞:
確認過眼神,我遇上對的人。
沈一天抓住自家兒子的胳膊,一把將他摔了出去。
沈晟易或許到死都會是懵的,他竟然會在某一天被父親當做墊子給推了出去,還是自己的親生父親。
果然啊,三十幾年的那個晚上,自己為什麼要戰勝那幾億的競爭對手來到這個不平等的世界?
炎珺聽著樓上傳來的靜,有些不明就里的抬頭看了看,這兩父子在鬧騰什麼?
“夫人,剛剛醫院來了電話,說是三公子醒過來了。”管家急匆匆的跑上二樓。
炎珺面上一喜,“好好好,我馬上就過去。”
一輛車疾馳在泊油路上,沿途兩側春洋洋灑灑的落在擋風玻璃上。
醫院病房,加安靜的工作著。
靜謐的房間,男人的眼眸有些迷蒙,他的記憶還有些紊,似乎不確定這里是不是花國。
“隊長,您醒了?”慕夕遲本是趴在小桌子上睡了一下會兒,迷迷糊糊中聽見了細微的聲音,他警覺的坐了起來。
沈晟風聞聲轉過頭,眼中的人影從模糊漸漸的清晰。
慕夕遲小跑過去,俯下認認真真的打量一番初醒過來的男人,角微微上揚些許,“您要不要喝點水?”
“小菁呢?”沈晟風的聲音有些干。
慕夕遲轉移著話題,“醫生說過了您燒傷太嚴重,大概需要三次手才能完全痊愈,可是因為您特殊,只有從您自取皮植皮,所以這需要的過程就更長了。”
猜你喜歡
-
完結853 章

他是人間妄想
人間妖精女主VS溫潤腹黑男主 三年後,她重新回到晉城,已經有了顯赫的家世,如膠似漆的愛人和一對可愛的雙胞胎。端著紅酒遊走在宴會裡,她笑靨如花,一轉身,卻被他按在無人的柱子後。他是夜空裡的昏星,是她曾經可望不可即的妄想,現在在她耳邊狠聲說:“你終於回來了!” 她嘴唇被咬破個口子,滿眼是不服輸的桀驁:“尉先生,要我提醒你嗎?我們早就離婚了。”
148.9萬字8 178870 -
完結455 章

成了前任舅舅的掌心寵
“你是我陸齊的女人,我看誰敢娶你!”交往多年的男友,娶了她的妹妹,還想讓她當小三!為了擺脫他,顏西安用五十萬,在網上租了個男人來結婚。卻沒想到,不小心認錯了人,她竟然和陸齊的小舅舅領了 證。他是國內票房口碑雙收的大導演,謝氏財團的唯一繼承人,也是那個惹她生氣後,會在她面前跪搓衣板的男人!有人勸他:“別傻了,她愛的是你的錢!” 謝導:“那為什麼她不愛別人的錢,就愛我謝靖南的錢? 還不是因為喜歡我!”
39.9萬字8 23728 -
完結40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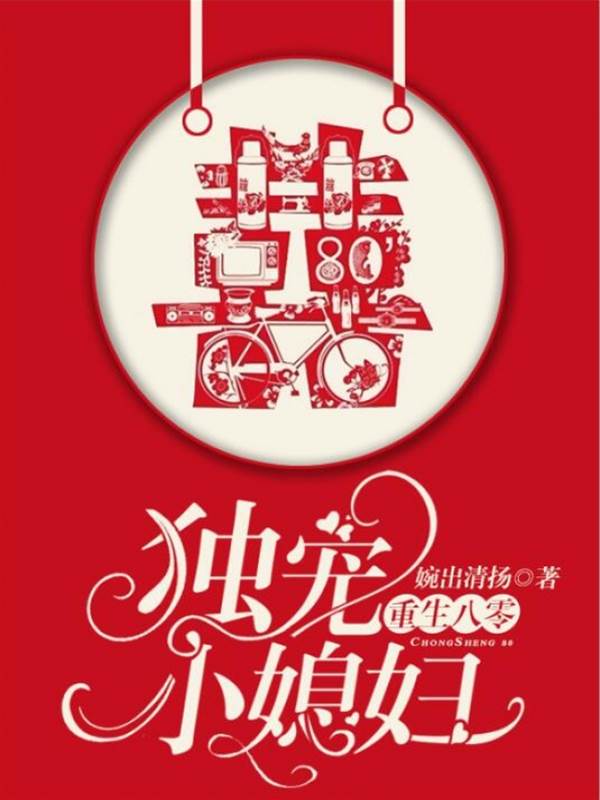
重生八零:獨寵小媳婦
九十年代的霍小文被家里重男輕女的思想逼上絕路, 一睜眼來到了八十年代。 賣給瘸子做童養媳?!丟到南山墳圈子?! 臥槽,霍小文生氣笑了, 這特麼都是什麼鬼! 極品爸爸帶著死老太太上門搗亂? 哈哈,來吧來吧,女子報仇,十年不晚吶,就等著你們上門呢!!!
72萬字8 960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