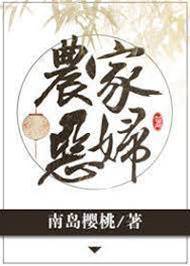《洞房前還有遺言嗎》 第一百一十六章 靈雁歲歲來
不關咱們的事。
隔世后, 可以永遠置事外, 不必再置事中。可以罷手作, 不必再擔起修復作的責任,甚至只要想,可以將作原本一燒了之。擁有前所未有的輕松, 卻也有前所未有的負罪。
這一切都歸于真相的揭。的與神識里,是否已經完全失去秦卿那殘破的靈魂了?一點都不用去承擔秦卿未盡的責任嗎?
回府后, 就浸在月隴西收藏秦卿什的那間房里待了三日。三餐照吃, 覺也睡足, 會聽月隴西講一講邊發生的事。
比如在蕭殷的看顧下,月世德果然就沒能活過來, 眾目睽睽之下被大火燒死,次日就被月氏族里的人抬回扈沽山,籌辦喪禮了;也比如陛下明著沒說,甚至假惺惺地表現了一番對月世德去世的惋惜, 心底卻慘了上道的蕭殷,恨不得未滿國學府三年試用期就直接給他升;更比如蕭殷主承擔監察失職導致月世德喪命的責任,說要幫助徹查長老莫名出現在焚書窟一事,被陛下準允并暗許后順勢以此為借口在刑部站穩腳跟, 卻不急著攬權, 只顧著幫暫被停職的余大人樹威……
不急著扶搖而上,沉得住氣。陛下更看重了。
卿如是聽著這些依舊會笑, 會跟著討論蕭殷接下來的路,沒別的異常。因為那些東西是真的事不關己。其余的時間, 還是更喜歡坐在小板凳上著秦卿的畫像與跡發呆。那是真的關己。
從前多用簪花小楷,如今依舊,可真正的秦卿未月府前,更喜歡在采滄畔用草書。墻上掛著的只有的小楷。
給自己磨了墨,提筆想用草書寫些什麼,卻發現落筆時仍是不自覺地轉用了小楷。寫道:秦卿,你后悔嗎?
Advertisement
現在你那里,崇文先生已經死去了嗎?
停腕須臾,卿如是又在后面跟著寫了一句:你可還會再想念他?那樣一個不堪的人,未曾真正與你推心置腹的師友。
還會。
在心底回答。覺得不夠,又低聲回道,“還會想念的。所以很痛苦。”
“叩叩”兩聲門響,卿如是擱筆不再寫,抬手用指背拭去眼角的晶瑩,開門一看,是月隴西。
“葉老聽說你有喜,帶了禮上門來探。這會兒方與父親聊過,獨自在茶亭吃茶呢。”月隴西示意出門,“去見一見,看看他給你帶的什麼禮罷?”
卿如是頷首,與他后的嬤嬤一道去了。月隴西思忖片刻,抬進到屋子里,緩緩走到桌邊,目落至桌面,拾起那張寫下自語的紙。他看了須臾,將紙折好揣進了懷里,趕著往茶亭去。
興許是國學府的伙食好,葉渠瞧著神矍鑠,遠比他在采滄畔的時候有神采得多。兩人見過禮,待月隴西也到場,卿如是就笑說道,“世子還說讓我來看看葉老為道喜帶的禮,可葉老分明兩手空空,沒見著帶了什麼禮來啊?”
葉渠樂呵一笑,“急什麼,你們且稍等一會。”
此時正是傍晚,夕輝漸盛,天映得周遭昏黃,又從昏黃中迫出一如初日東升般的希。
不知多久,月亮門有幾名小廝的說話聲傳來。卿如是尋聲看去,兩人拿著一幅展開的畫卷正朝這邊小心翼翼地走來,另有兩名小廝在為他們領路。
“喏,來了。”葉渠用下頜指了指。
只見小廝站定在茶亭外,迎著夕將畫立起。霎時間,畫中景被夕染上金黃,霞隨著云海翻滾,鴻雁迎著長風振翅,耳畔傳來參差不齊的雁鳴聲,聲聲互,跟著湖面的點跳躍。群雁歸來。
Advertisement
“聽說你近日郁結在心,難以遣懷。我就想著送你一幅雁歸圖。想想那春去秋來,年復一年。不知道去的那批大雁和來的這批是不是同一批,但總歸是……帶著新的生命回來了。有什麼比為了活下去而來往忙碌更重要的呢?去的就讓它去了罷。”
不知是否人人都似這般,慟然時聽的道理,都像是專程說給自己。似是而非的療著傷,不一定能療好,但總是滿心藉。卿如是亦覺如此,朝葉渠俯一拜,謝過。
他笑,“應該是謝你,”拍了拍月隴西的肩膀,別有深意地嘲道,“讓世子爺未來幾月都實在是可喜可賀。”
話落,月隴西便皮笑不笑地送走了他。臨著踏出門,葉渠了一眼不遠的茶樓,一拍頭,又轉跟他說道,“蕭殷托我幫忙問一聲,是否允他前來拜訪?我讓他要來便來,若你不愿見,大不了被趕出來。所以就讓他在那邊茶樓等著了。你看看要不要讓他進去,我好跟他說一聲。”
這些日接連有人拜訪送禮,葉渠算是來得晚的。前兩日懷有孕的事傳得人盡皆知的地步,的不的都早來過了,卿如是閉門未見而已。今日好容易讓卿如是出門了,多見一人也好。免得轉頭就又回房悶著思考人生。而且……月隴西的眸微深了些。
葉渠哪里曉得他們之間的彎繞,還以為蕭殷做事得罪了月府,只當是幫他們緩和一二罷了。月隴西若是不讓進,他也沒別的轍。
誰知月隴西好說話,大度地點頭許可。且還就站在門口等著。
蕭殷到時見到他,神中出幾分訝然,即刻收斂了,恭順地施禮道,“世子。不知世子為何站在這里等屬下……?”
Advertisement
“倘若我記得沒錯,卿卿對你說過,你的才思與崇文相近,應不遜于他。我想來想去……無論是非黑白,你的心狠手辣,或是聰慧穎悟,還真是這樣,與崇文如出一轍。”月隴西抿,沉了口氣。
人走茶涼,卿如是卻仍舊站在茶亭,觀賞那幅雁歸圖。小廝的胳膊舉酸了,靜默許久后反應過來,示意他們退下。自己杵在原地,眼中空無一。
“咳。”
忽而一聲輕咳,卿如是回過神,將視線劃過去。穿著一白的俊朗青年正站在庭院中向,筆的姿,沉靜的神。唯有耳梢一點紅看得出他的心境。
“你怎麼來了?”卿如是睨著階梯下的他,看著他朝自己走過來。
蕭殷尋了一級矮的,站在下面堪堪能與平視的臺階站定,抬手將一張寫了黑字的白紙遞過去,低聲道,“世子說,你近日心不好。我聽他說了一些,也看過了這張紙上寫的。興許是思考的方式不同罷,我竟覺得你糾結的東西,你所疑不解的崇文,于我來說,都十分簡單。”
卿如是一直低垂著的眼眸微抬,淡淡的點凝聚在眸心,蹙起眉,“嗯?”
蕭殷篤定地點頭。
此時,夕最后一點余暉映在他的眸中,賦予他清澈的眸子以多變的彩,他偏頭道,“聽說秦卿認識崇文,加崇文黨的時候,只是個六歲的小姑娘?……那麼小的孩子就有決心要跟著崇文反帝了嗎?”
卿如是一愣。想肯定地點頭,遲疑一瞬,又搖了頭,不得不承認道,“興許是一時興起。或者什麼都不懂,起初跟著起哄,后來被崇文教導,于是所思所想皆隨他,慢慢陷進去了。”
“我也是這麼想的。秦卿一開始不怕反帝,因為年紀太小本不明白那個組織是反帝的,等能怕的時候,已經被崇文教得以為自己不再怕了。”蕭殷似輕笑了聲,有點嘲諷的語調,“所以,世上沒有那麼多生來便正直無畏與大義凜然,對不對?”
Advertisement
卿如是點頭,“無可否認。”
“那秦卿憑什麼說崇文骯臟不堪呢?因為崇文上說著平權,卻未將人命放在眼里嗎?”蕭殷皺眉,狀似費解,實則清明地道,“那麼秦卿自己加崇文黨時不過意氣用事,未將家人命考慮進去便頭也不回地了死,沒有想過自己反帝也會拉著家人喪命嗎?還是說想過,但執意如此,為了所謂的大義?那麼,何嘗不是上說著平權大義,卻沒有給父母生死的選擇?未將自己家人命放在眼里?”
卿如是啞然。約覺得他說得不對,但細想又找不出哪里錯。的心突突地跳,只能握拳,有些不知所措。
“覺得哪里不對是嗎?你放心,邏輯的確有問題。”蕭殷淺笑了下,“我換了兩者的概念。崇文主要人死,和秦卿的父母被死,自然不同。有思考能力的崇文和六歲的沒有分辨能力的孩提,自然也不同。我這樣對比只是想結合第一個問題說明兩點。既然世上沒有生來便正直無畏的人,那麼此人如何,基本是靠后天養;于是,自六歲起到臨死,一直保持純粹的秦卿,幾乎就是那個骯臟的崇文一手教出來的。”
“這麼說你能明白嗎?秦卿進崇文黨的年紀比誰都小,進得也比誰都早。別的崇文弟子有覺悟要加時已經有自己的判斷能力了,所以才加。而秦卿沒有,與崇文認識時,只是個小姑娘。那時候的崇文也十分年輕罷,卿姑娘你應該比我清楚,初期的崇文在著作中現的是要改變蒼生,教化眾人,那時他還未打響反帝的算盤,背水一戰。”
“所以,他剛認識秦卿的時候,又怎麼可能已經籌劃好了要利用?決定利用,是很多年后的事了。我想,那時候的他只想好好教導秦卿。”
卿如是并未否認,只喃喃道,“那又如何,他終究是利用了秦卿。終究是背負了那麼多條人命。”
“你糾結的是他背負人命這件事本?”蕭殷笑了,帶著看穿一切后的冷然,“我告訴你,月一鳴當年在塞外拿尚未決定死的犯人試驗酷刑;秦卿多次與皇權板時都不慎讓的親人犯了險,最后全靠月一鳴保住,你知道他怎麼保住?不殺秦卿的家人,就要殺別的崇文黨,算來算去,這是不是秦卿背負的人命?如今的月將軍為保襲檀一事不泄出去,亦殺過數名無辜百姓,我們竊。聽時你后來一步,我早就聽得清清楚楚。還有你爹,當年為鎮前朝舊臣用計亦殺了不人。
我相信你知道,聽過之后亦能接。
你糾結的不是人命本,因為這個世道就是這樣,你已經看慣太多,無能為力。你無非是糾結,崇文為何背著秦卿壞事做盡,害被蒙蔽多年,郁郁而終。亦不明白崇文為何在別的弟子面前可以展出渾濁不堪的一面,偏只將秦卿放逐于崇文黨之外。是不拿當自己人?還是從頭到尾對只有利用?”
蕭殷搖頭,不假思索地篤定道,“如果我是崇文,我也必然不會將自己齷齪不堪的黑那面展現給秦卿。”
卿如是眉心微,幾乎無聲地問,“……為什麼?”
蕭殷抿著角,劃開極為清淺小心的一抹笑,他幻想著崇文應該會慣用的語調,語重心長地道,“因為我知道,那樣義無反顧地加崇文黨,愿意跟著一群男人去捍衛道義的六歲小姑娘,值得用最純粹的靈韻栽培。”
“……什麼?”卿如是長睫輕,以為自己聽錯,“你說他不告訴秦卿,是因為……?”
蕭殷溫潤一笑,在黯淡下來的天與華燈的冷映下,竟像是崇文在對說。
他說:“我會想,生來就不該沾染黑,只該理解我記在紙張上的那些東西,而非理解我這個人。
我會教黑白是非,但我不會讓為黑。
我只要這個人來保住我的書,因為眾多崇文弟子中,只有一人能明白我在書中留住的純粹了。
我仍是會讓送死,但我不會告訴我的計劃里必須要有很多人死。那樣就看到了黑。
猜你喜歡
-
完結284 章

末世歸來之全能醫後
驚爆!天下第一醜的國公府嫡女要嫁給天下第一美的殤親王啦,是人性的醜惡,還是世態的炎涼,箇中緣由,敬請期待水草新作《末世歸來之全能醫後》! 華墨兮身為國公府嫡女,卻被繼母和繼妹聯手害死,死後穿越到末世,殺伐十年,竟然再次重生回到死亡前夕! 麵容被毀,聲名被汙,且看精明善變又殺伐果斷的女主,如何利用異能和係統,複仇虐渣,征戰亂世,步步登頂! 【幻想版小劇場】 殤親王一邊咳血一邊說道:“這舞姬跳得不錯,就是有點胖了。” “你長得也不錯,就是要死了。” “冇事,誰還冇有個死的時候呢。” “也是,等你死了,我就把這舞姬燒給你,讓你看個夠。” 【真實版小劇場】 “你可知,知道太多的人,都容易死!”殤親王語氣冷漠的恐嚇道。 華墨兮卻是笑著回道:“美人刀下死,做鬼也風流啊。” “你找死!” “若是我死不成呢,你就娶我?” 【一句話簡介】 又冷又痞的女主從懦弱小可憐搖身一變成為末世迴歸大佬,與俊逸邪肆美強卻並不慘的男主攜手並進,打造頂級盛世!
49.9萬字8 16744 -
完結408 章
誤落龍榻:嫡寵冷妃
年過二十五,竟然還是處女一名,實在是愧對列祖列宗啊! 莫非驅魔龍家的女子注定孤獨終老?幸好,老天終於安排了一個帥哥給她,此男縱橫情場多年,對床第之事甚為純熟,相信會是一個很好的老師,自從相識的那一天起,她便等待著他對她有非分之想。 終於等到了,他邀請她吃飯看電影吃夜宵開房。整個行程裏,她期待的隻有一樣。這一刻終於來臨了,她喜滋滋地洗好澡,穿好浴袍,走出洗澡間正綻開一個魅惑的笑容時,忽然一陣地動山搖,樓塌了。 她從未試過像現在這般痛恨開發商的豆腐渣工程,要塌,也不差這一時三刻啊,起碼,等她完成這人生大
77萬字8 11179 -
完結3613 章

盛世為凰(冷青衫)
他弒血天下,唯獨對她溫柔內斂,寵她一世情深!
528.9萬字8 96664 -
完結157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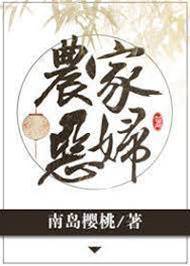
農家惡婦
何娇杏貌若春花,偏是十里八乡出了名的恶女,一把怪力,堪比耕牛。男人家眼馋她的多,有胆去碰的一个没有。 别家姑娘打从十四五岁就有人上门说亲,她单到十八才等来个媒人,说的是河对面程来喜家三儿子——程家兴。 程家兴在周围这片也是名人。 生得一副俊模样,结果好吃懒做,是个闲能上山打鸟下河摸鱼的乡下混混。
48.4萬字8 8137 -
完結314 章

石榴小皇后
世人皆知,當今天子性情暴虐,殺人如麻。 後宮佳麗三千,無一敢近其身。 後宮衆妃:爭寵?不存在的!苟住小命要緊! 皇帝登基五年尚無子嗣,朝臣們都操碎了心。 就在這時,沈太傅家那位癡傻的小孫女阿措,主動撲進了皇帝懷中。 滿朝文武&後宮上下:震驚!!! 後來,沈家阿措升職加薪,搞到皇帝,一朝有孕,坐上皇后寶座,走上人生巔峯。 世人皆贊皇後好命能生,無人知曉,皇帝在夜深人靜之時,刻苦學習《戀愛入門指南》《好男人必備守則》《試論證男人懷孕的可能性》…… 聽說皇后又有喜了,皇帝盯着手裏的書頁直皺眉,“阿措那麼怕疼,怕是又得哭了,要是朕能替她生就好了。” 阿措:其實我真的不是人……
47萬字8 1363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